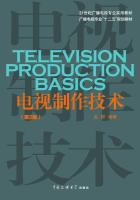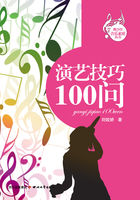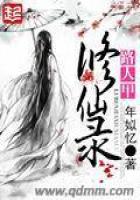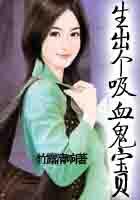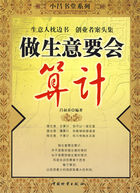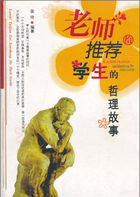角色,原本是戏剧术语,指演员在戏剧舞台上依据剧本或演出要求所扮演的某一特定人物。20世纪20、30年代被引入社会学,又名“社会角色”,“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社会角色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外在表现,是人际关系互动时的行为期望和要求。
社会角色有多种类型,如按角色获得的途径划分,有先赋性角色与自致性角色;按角色规范化的程度划分,有规定性角色与开放性角色;按角色追求的目标划分有功利性角色与表现性角色;按角色扮演的时间久暂划分有永久角色、长期角色与临时角色;按角色承担时的心理状态划分有自觉角色与不自觉角色等等。
滚滚红尘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也没有人能完全独立于红尘之外。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既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又都处在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结点,兼有多种角色身份。例如你、我或者他,在父母面前是子女,在子女面前是父母;面对丈夫是妻子,面对妻子是丈夫;写作时是作者,阅读时是读者;在商场购物成了顾客,乘车外出又成了乘客。在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每个人扮演的都不会是一个角色,而是众多的角色,社会学称之为“角色丛”。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以一定的社会成员的身份与他人进行交往,而这种交往一般以语言为媒介,即进行言语交际,因此作为社会产物的社会角色,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便转化为一定的话语角色。话语角色是指言语交际主体在具体言语交际过程中所认知选定的社会身份。话语角色以社会角色为基础,但不完全等同于社会角色。话语角色是社会角色在具体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它通过言语交际主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交际行为模式外显出来,体现于言语交际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关系位置与相应的特点。“一般说,社会角色是稳定的,而话语角色是短暂的,瞬时的,因语境而变化的,在言语交际中,话语角色可根据语境的需要进行调整,以便使其话语同角色相适应,以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
任何一个个体只要进入言语交际的过程充当交际的主体便会担当一定的话语角色,进入一定的角色关系之中。而交际主体作为社会角色具有多重角色集于一身的特点,是个角色丛,因此,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具有多种潜在的话语角色和角色关系可供选择,然而一般说来,在同一时空点上每个人只能选择一种话语角色,交际双方每次只能以一种角色关系进行对话,这是交际主体“话语角色扮演的必然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话语角色不明或话语角色混乱,影响话语角色的成功扮演”。换言之,作为社会的人,只要进入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面对特定的交际对象,就有一个自身话语角色的选择、确立问题,即话语角色的定位问题。话语角色定位正确与否、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话语的组织与理解,直接影响言语交际的效果,影响交际目的能否达到。
交际双方话语角色定位是受交际目的制约,以自身社会角色为基础,以对方为参照系,经认知、选择而确定的,因此交际主体在进行话语角色定位的同时,交际对象的话语角色、交际双方的话语角色关系也随之明确。当然,不同的话语角色扮演和同一话语角色扮演的不同阶段可能会发生和客观实际不相吻合的情况,这就需要交际主体凭借自己正确的角色认知来调整、修正,并采取与之相应的话语表达方式和话语风格。正确的话语角色定位,为言语交际行为提供了可靠的前提保证与出发点。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只有正确进行角色定位,才能做到彬彬有礼,合意得体,才能取得交际的圆满成功。那么,交际主体如何进行话语角色定位呢?
第一、注意自己的交际动机与交际目的。人们的言语交际起因于一定的交际动机与目的。交际动机与目的往往影响并决定着言语行为的发展方向,对交际主体的话语角色定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选择、确定自己的话语角色首先必须注意自己的交际动机与目的。《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交际动机在于“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家中冬事未办”,需解决“冬事”,其交际目的在于上荣国府寻些“好处”,亦即三十九回从平儿角度叙述的“打抽丰”。历练人情而又能说会道的刘姥姥将自己的话语角色定位在“需要周济的穷亲戚”,并以此制约与贾府上下的言语交际行为,最终满意而去。岑凯伦的小说《只因我寂寞》中有这么一个情节:
沉默而冷漠的惠庄提着菜篮走进来,看见客厅里坐着的人,怔一怔,眉心马上打起结来,很明显地不欢迎范文。
“孙——哎,伯母!”范文叫着。
“范医生来了!”她用冰冷的语气,对范文的一声伯母并不接受。
这里范文与孙惠庄的角色关系有两种:一是医生与患者家属,二是患者的追求者与追求对象的母亲。平时范文称孙惠庄为“孙女士”就是将自己与对方定位于第一种关系。现在改变称呼,称“伯母”,就是定位于第二种关系,而这种定位正是出于交际目的:想拉近与孙惠庄的关系。而孙惠庄沿用医患关系中的职业称呼,将自己与范文定位于患者家属与医生的话语角色关系,也正是出于自己不赞成范文与女儿过深交往的目的。
第二,注意交际场合。言语交际行为总是发生于特定的交际场合。交际场合也制约着交际主体的话语角色定位。交际场合不同,话语角色定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一对父子同在某师机关工作,父亲是师长,儿子则是一位参谋。在机关他们王师长、王参谋的相称,可回到家里他们的称呼变了,“王师长”变成了“爸爸”,“王参谋”变成了“晓东”。这种称呼的变化,其实正是话语角色定位因场合变化而产生的变化。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的话语角色定位如果忽视了交际场合的制约,则有可能出现言语交际的偏差,影响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
第三,注意角色规范在特定情景下所能发挥的实际约束力。一般说来言语交际中所选定的角色,其角色规范的实际约束力越强,言语表达的威力越大,交际效果也就越好。所以应选择角色规范实际约束力强的角色来进行角色定位。
既然具体交际语境下不同角色规范的约束力有强有弱,那么在某些时候交际主体可特别强调自己的某种角色身份,以此来产生某种语言表达的威力。如:
“我今天还有些事要处理。”成浩抖了抖烟灰,淡淡地说,“没时间听你说。”
“阿亮!”杨之刚激动地站起来,“我比你大将近十岁,今天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讲这一番话。我一直佩服你把握艰难世身的本领,以及那种超人的自制力,但……”(莫然《高处不胜寒》)
杨之刚与成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但现在成浩是某司级大公司总经理,杨之刚是总经理助理。二人之间至少有两种角色关系: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现在杨想劝说成放弃和一外省女子的儿女私情,否则成会因此影响美好的前程。为增加劝说的力度,杨有意强调以朋友的身份说话,是朋友之间的推心置腹。
第四,注意与对方的人际关系,对方的社会地位及心理。如前所述,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话语角色定位是受交际的动机、目的制约,以社会角色为基础,以交际对象为参照系统而确立起来的,表达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人际关系、接受主体的社会地位和心理不可避免地影响、制约着具体交际中的话语角色关系。这其中接受主体的社会地位和心理更是影响话语角色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恰当地选择、确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可不注意与对方的人际关系、对方的社会地位及心理。权延赤《巨人的魅力》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离老远,彭德怀便伸出两臂准备握手,确实有些急性子。他敞开喉咙,用他那湖南口音很重的嗓门连珠炮似的嚷:“老毛,我等工夫不小了,怎么才来?骑的什么马呀?你们这些人?”从井冈山到延安,彭德怀始终称呼毛泽东为老毛。随着毛泽东威望日高,延安和各解放区军民都习惯了称呼毛主席,唯独彭德怀仍然保持老习惯,还是叫“老毛”。党的“七大”后,他似乎发现了孤立——全党只剩他一个人把毛泽东叫老毛。于是,他开始改变井冈山时叫习惯了的“老毛”,也用“主席”来称呼毛泽东。只是有时一着急,仍免不了叫出一声两声“老毛”,决无不恭敬的意思,实在共事已久友谊深远的原因。
“好马都给你彭老总了么。”周恩来笑着说。
“嗨,我杀的马也比你们骑的马强哪。”彭德怀握住毛泽东的手,先看马,后看毛泽东,“主席,你可瘦多了!”
这里,彭老总对毛泽东称呼的改变其实就是角色定位的改变。一开始称毛泽东主席为“老毛”,这是从极近的同事关系角度定位。这种定位从彭德怀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来说并无不妥,但与毛泽东主席崇高的声望、地位相联系,就很不恰当了。后改称“主席”,这是从上下级的角色关系来定位,无论从人际关系,还是对方的地位、心理来说都非常得体,而且极富情感。
二、话语角色定位的语言表现形式
1.称呼语
称呼语是话语角色定位最常用、最典型的语言表现形式。汉语的称呼语丰富多彩,有专称、泛称、尊称之分,也有社会称谓和亲属称谓之别。选用何种称呼语来称呼对方既表达了交际主体对交际对象的情感、评价态度,又赋予了自己和交际对象一定的社会地位。换言之,交际主体在称呼对方的同时,也给自己的话语角色进行了定位,并使交际双方的关系具体化、明确化。
2.动词形式
动词反映人或物的运动、发展、变化,表现宇宙的物质运动。一部分动词从言语交际的角度来说还反映了交际者的角色关系,从而表现出交际者的角色身份。如,“我娶了一位好老婆”,“娶”表明了说话者的男性话语角色身份;而“我出嫁了”,“出嫁”昭示出说话人的女性话语角色身份;“我不赡养你们,天地不容啊!”,“赡养”反映出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下对上或晚辈对长辈的角色关系。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之下动词形式也便成了话语角色定位的语言表现形式。
胡范铸在《什么是“修辞的原则”?》一文中举过这么一个例子:“全国人大今天进行了分组讨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小组发言中认为:学习了总理刚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感到深受鼓舞……(报)”他分析说:“如果人大闭幕后,任何一位国民说:‘学习了总理刚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感到深受鼓舞’,在修辞上都没有问题。但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作为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面对刚刚作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所应该作的应该是‘审议’而非‘学习’,即使这位代表平时的职级远远低于总理,但选民推举他作为代表就是要他代表人民去‘审议’的。忽视了自己的角色的转换,必然导致修辞行为的失效”。这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运用了动词“学习”(可能是下意识)就将自己的话语角色定位于下级,从而将自己与总理的话语角色关系定位于下级与上级的关系,但在全国人大分组讨论会的语境下,这种角色定位不恰当,唯有运用“审议”,将自己的话语角色定位于审议者(人大代表),其话语行为才适切有效。
3.口气
口气是有声语言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人们说话时通过声音、气息的调节或语词、句式的运用而流露或显露出来的感情、态度、思想、角色身份的某种情调或倾向”。
说话是人类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交际行为。从信息论角度观照,它其实就是说者与听者的一种信息交流活动。这种信息交流活动主要是理性信息的交流与传递,但也有感情、态度信息的交流与传递。人们在说话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说话方式往往会流露出说者信息传递的某种倾向或者流露出说者对相关人、物、事等的感情、态度的色彩。这种意、情、态的色彩流露就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口气。如“埋怨的口气”、“领导的口气”、“长辈的口气”、“小孩的口气”、“男子汉的口气”等等。口气不总是体现说者与听者的角色关系,但口气常可表现说者与听者的角色关系。因而在特定情景之下,口气也是一种角色定位的语言表现形式。口气和声音、气息紧密相连,复杂多姿,色彩斑斓,交际主体选择什么样的口气和对方说话,往往既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也体现了自身的身份、素养和情感倾向,同时定位了自己与对方的话语角色关系。如:
谷燕山被宣布“停职反省”后的每五天,李国香组长“上楼”来找他做了一次“政策攻心”的谈话。“老谷呀,这几天精神有点紧张吧?唉,你一个老同志,本来我们只有尊敬,请教的份,想不到问题的性质这么严重,县委可能要当作这次运动的一个典型来抓啦!”李国香仍是那么一口清晰悦耳的腔调……
“怎么样?这些天来都有些什么想法?……你看,我只想和你个别谈谈,都没有叫别的工作组员参加……”
谷燕山还是没有为她的诚心所动,只是抬起眼睛来瞟了她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反正我是什么都不会跟你讲。
李国香仿佛摸准了他的对抗情绪,决定抛点材料刺他一下,看他会不会跳起来。于是从口袋里拿出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本,不紧不慢地一页页翻着,然后在某一页上停住,换成一种生硬的、公事公办的口气说:“谷燕山,这里有一笔帐,一个数字,你可以听听!经工作组内查外调核实,自一九六一年下半年以来,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说,芙蓉镇五天一圩,一月六圩,总共一百九十八圩,你每圩卖给本镇女摊贩、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胡玉音六十斤大米,做成米豆腐当商品,共是一万一千八百八十斤大米。这是不是事实?”(古华《芙蓉镇》)
李国香与谷燕山之间的社会角色关系有多种,因而其话语角色关系也就有多种。一开始李国香用和缓柔软的口气与谷燕山交谈,也就是将自己与对方话语角色定位于熟人之间,未能达到交际目的,便改用生硬、公事公办的口气,也就是将自己与对方话语角色关系定位于审问者与被审问者之间,她想以此来提高自己话语的威慑力。
4.语体
语体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中形成的语文体式。它是由于交际的对象、目的、内容、环境关系的不同而产生的言语功能变体。语体的转换往往也体现出交际主体的话语角色转换,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与角色关系,也就是说,语体也具备一定的话语角色功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话语角色的语言表现形式。如:
教授灰白的眉毛微微一扬,拿起沉甸甸的论文说:“两年半时间,写出这样一本论文,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的论文不仅科学水平,而且插图装帧的艺术水平也很高。”
感叹之余,教授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身份,挺正了腰身,恢复了考官的尊严。严肃的答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