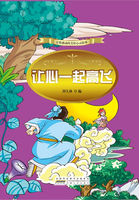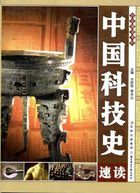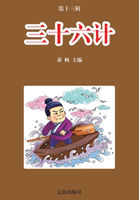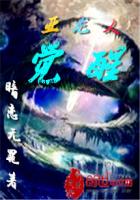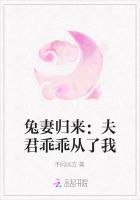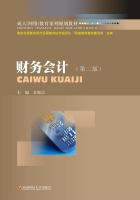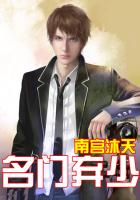[吊带]diào dài(1)围绕在腰部从两侧垂下来吊住长筒袜子的带子。(2)围绕在腿上吊着袜子的带子。
[挂钩]guà gōu(1)用车钩把两节车厢连接起来。(2)比喻相联系:基层供销社直接跟产地。
“吊带”理论上说起来其意义组合有两种可能情形,因而结构关系相应地也有两种可能情形(一为支配式,一为偏正式),但从《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可知“吊带”是偏正式。“挂钩”理论上也有两种意义关系,因而结构关系相应地也有两种可能情形(一为支配式,一为偏正式),但从《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看应为支配式。
根据以上我们所理解的合成词结构类型确立的依据,下面我们讨论两个有关合成词结构类型的实际操作问题:
1.“化石”“积木”的结构关系
初中语文第一册语文知识短文《词的构成》中认为“化石”“积木”这两个合成词为支配式合成词,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从外部语法形式来说,“化石”与“积木”都是“动词性词素+名词性词素”的形式,但不能由此得出它们都是支配式合成词的结论,因为决定合成词结构类型的依据是词素之间的意义组合关系,而不是外部语法形式。如上所述,事实上相同的外部语法形式,却可能分属于不同的结构类型,比如:
(1)卧铺、挂表、刨床、围巾、围网、挂车、滚轮
(2)带头、谈天、达标、挂钩、起草、站岗、围脖
(1)(2)都属于“动词性词素+名词性词素”的形式,但(1)词素之间具有修饰被修饰、限制被限制的关系,词义偏于后一个词素,因而是偏正式合成词,而(2)词素之间具有支配被支配的关系,词素义浑然一体,没有主从,因而是支配式合成词。
从词素之间的意义组合关系来说,“化石”与“积木”都有两种可能的意义关系:
(1)变化成石头化石
(2)(古生物)变化成的石头
(1)堆积木块积木
(2)用来堆积的木块
从这两种意义关系可以推导出“化石”与“积木,的结构方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支配式,一种是偏正式。那么孰是孰非?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我们了解人们创造这两个合成词的理论依据、创造这两个词的目的。
就“化石”一词来说,人们创造这么个合成词是因为认识到有那么一种类似石头的东西,这种类似石头的东西是古代生物的遗体、遗物或者遗迹由于埋藏在地下久远而变成的。可见“化石”的构词理据就是“变化成的石头”,人们用“化石”一词是要反映所认识到的是什么样的对象,而不是反映认识到什么样的对象关系,因此“化石”应该是偏正式而不是支配式。
就“积木”一词来说,人们用它所要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事物(木块),而不是用它来反映人与事物(木块)之间的关系(堆积),因此“积木”也应该是偏正式,而不是支配式。
2.“地球”“雪花”“熊猫”等的结构方式
大家公认汉语有主谓(陈述)、动宾(支配)、联合、偏正和补充五种基本结构关系,表现在复合型合成词里也有这五种基本的结构关系。
就偏正和补充关系来说,它们正处于对立与互补的语义关系网络之中。偏正关系是前偏后正,语义关系偏向后边成分。补充关系则正好相反,是前正后偏,语义关系偏向前边成分。以合成词为例,偏正式的是前边的词素修饰限制后边的词素,语义以后边词素为中心。如“笔谈”,“笔”修饰“谈”,表示“谈”的一种方式,整个词义以“谈”为中心,“笔谈”属于“谈”;“皮鞋”也是如此,“皮鞋”属于“鞋”,“皮”只不过表示一种质料,起修饰限制作用。因而“笔谈”“皮鞋”是偏正式。而“扩大”“延长”等则不然,它们的词素之间是补充说明的关系,后面的词素补充说明前面的词素,在整个词义的构成上,以第一个词素为主,如“扩大”表示一种动作行为,词义以词素“扩”为核心,“大”对“扩”起补充说明作用,表示动作行为的一种结果或趋向。“延长”也以“延”为词义核心,“长”起补充说明作用,因此“扩大”“延长”为补充式。
既然“偏正”与“补充”属于两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其语义构成指向正好相反,那么在合成词结构类型辨识的实际操作中有必要分清二者。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人有时不分二者。举例来说,“地球”“雪花”“熊猫”等合成词很多人都归入偏正式。严格说来这种归类是不妥当的,因为它们的词素意义组合关系是前正后偏,从词义构成上来讲,是以前面的词素为核心,后边的词素对前边的词素起修饰说明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如“地球”的语义理解应是“像球一样的地”,而不是“地(一样的)球”;“雪花”应是“花一样的雪”,而不是“雪(样的)花”;“熊猫”应是“猫一样的熊”,而不是“熊(似的)猫”。显然这正是补充式合成词的特征,而不是偏正式合成词的特征口因此,我们认为“地球”“雪花”“熊猫”应归人补充式,而不应归人偏正式。
像“地球”这种合成词可视为补充式合成词的一个小类。这个小类的特征在于:前一词素表示被修饰被限定的成分,后一词素表示修饰限定成分。此类再举几例如下:
宅院:语义为(带)院的(宅)
烟卷儿:语义为卷儿(状)的烟
钩吻:语义为(唇)吻(状)的钩
泪珠:语义为珠(子)(似的)泪
汗珠:语义为珠(子)(似的)汗
氛围:语义为(包)围(着的气)氛
韭黄:语义为黄(色的)韭(菜)
铁丝:语义为丝(状的)铁
(原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现代汉语词缀研究鸟瞰
汉语没有印欧语言那样丰富发达的形态变化,但是必须承认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也是有一些形态变化的。比如说在构词法方面,虽然主要用词根复合法,但也用词根加词缀的附加法。这附加法就体现了一种形态变化。随着语言的演变、发展,某些成分语意的虚化,现代汉语中有词缀逐渐增多的趋势。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先生就指出过:“中国语似乎有语尾增多的倾向。”
近几十年来,现代汉语的词缀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浏览一些语言学论著,就会发现语言学家们对现代汉语词缀是越找越多,其中不少是否真是词缀很值得检讨一番。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对现代汉语词缀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概括的叙述。
一
词缀,也有人称之为语缀。吕叔湘说:“语缀这个名称也许较好,因为其中有几个不限于构词,也可以加在短语的前边(如第)或后边(如de)。”如果不把可以加在短语前后的那几个成分算作词缀,而称之为助词,那么,“语缀”这个名称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反之,如果把那几个成分包括到词缀中来,也许是“语缀”的名称好一些,因为更具有概括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了词(助词)和词缀的区分问题。由于“语缀”这个术语不仅包括了“不仅是词的,而且是短语的接头接尾成分”,还包括了“那些不安于位的助词”,有一定的杂烩性。因此,有人对它产生疑问:“目前一些语言学家所说的‘语缀’,包含了大小不一的语言单位,人们有理由问:提出‘语缀’这一术语,是否合理和科学?”
二
词缀是定位的不成词的粘着成分,是构词位置固定、意义虚化的词素。
关于词缀的性质特点,人们的看法有一致之处,也有不相同之地。对于词缀构词位置固定以及在构词中经常具有类化作用(如带有后缀“头”“子”的一般是名词,带有后缀“化”的一般是动词)这两点大家看法是一致的。但对词缀“意义虚化”这一点,看法就有分歧了。一般都认为词根意义实在,词缀意义虚化。我们知道,现代汉语的词缀都是由于词根在漫长的语言发展过程中逐渐虚化形成的,那么这“意义虚化”是一点儿词汇意义都不带,还是可以带一点儿?再者,由于,“意义虚化”这个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所以对某些词素,有人认为意义虚化了,是词缀,有人认为意义还没有虚化,应是词根(具体的例子我们底下再谈)。
常敬宇认为词缀“常常附着在词根的前面或后面或嵌在其他语素中间,它只表示附加意义或语法意义,而不表词汇意义,所以词缀是一种不自由语素,或者说是一种虚化的语素”。这就是说,作为词缀意义应该完全虚化,不再带有词汇意义。按照这种看法,现代汉语的词缀是比较少的。常敬字认为:“严格来说,前缀只包括‘阿’‘老’‘第’等,后缀只包括‘子’‘儿’‘头’‘性’‘化’等少数几个,中缀也只有‘里’‘不’‘了’等。”由于现代汉语中“等”既可以表示列举完毕,也可以表示列举未完,所以我们不好说常氏认为现代汉语词缀就这么十一个,但可以推测多也多不到哪儿去。
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认为,有的词缀意义完全虚化,只表示语法意义,有的则兼表词汇意义。前者举例有“老、阿、子、儿、头”,后者举例有“员、者、性、化”。《现代汉语》(增订本)甚至认为“可怜、可笑、反革命、反作用、非法、非常、不法、不良”中的“可、反、非、不”“表示一种比较抽象的词汇意义,位置固定,但一般不表示什么语法意义”,也是一种词缀(前缀)。按照这种观点词缀可以带有词汇意义,那么现代汉语的前缀范围是比较宽泛的。这种观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按此观点,实词素与虚词素、词根与词缀的区分标准就难以掌握了。
词缀的确定涉及词根。一般语法或词汇著作在谈词缀与词根的区别时都说,作为词缀,其意义是虚化的、概括的,一般只表示附加意义或语法意义,而作为词根其意义比较具体、实在,都表示词汇意义。看语意是否虚化应该说是区分词缀与词根的最重要的标准、原则。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结构上来考虑,即词缀的构词位置固定,它是粘着的定位的,词根一般不具备这个特点。
郭良夫认为:“确定一个语素是不是前缀或后缀,一要看它在语意上的虚化程度,二要看它的能产程度,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一个类前缀或一个类后缀,使用的次数多了,使用的范围广了,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前缀或后缀。”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思索。张静根据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划分词根和词缀的四条标准,即:(1)看意义是否实在、具体。意义比较实在、具体的都是词根,意义比较空灵、概括的可能是词缀。(2)看能否单独成词。有些词根可以单独成词,词缀永远不能以它在合成词里的意义单独成词。(3)看构词时位置是否固定。词根用来构词时位置是自由的,可以放在另一词根之前,也可放在另一词根之后;词缀只能放在词根前面(前缀)、后面(后缀),或者放在两个词根中间(中缀)。(4)看能否用作简称。词根往往可以代替全词,词缀一般不能用作简称。“一般说来具有上述四个条件之一的一般都是词根;完全具备四个条件的才是词缀。”
词缀的确定除了存在与词根划界的问题,还有一个与助词划界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对词缀的本质、助词的本质以及词的本质的认识,是很不好解决的。
“们、第、初”一般看作词缀,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看作助词。附着在数词、量词之后表示概数的“来”“把”(如“五里来路”“千把人”),胡裕树看作助词,张静却看作中缀。
“本校”的“本”,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订本)看成指示代词,张静看作前缀。“所”一般看作结构助词,张静认为可划归前缀。
“着、了、过”一般认为是时态助词,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是后缀,如张静认为“了、着、过”只能跟在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动词的完成体、进行体或已行体,不是独立的词,应划归词素(后缀)
再如“的、地、得”一般看作结构助词,但也有看作后缀的,如任学良。
对于词缀和虚词(助词)的区分,一般都没有明确的意见,邵敬敏认为:“一个语素,不仅粘着、定位,而且在组合上是封闭的、可数的,那么,它就属于构词法范踌,是词缀;如果在组合上是开放的、不可数的,那么,它就属于构形法范畴,是语缀,或者按照我国传统的说法,称之为虚词。”
由于语意虚化的程度不同,在典型的前缀、后缀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不太地道的语意没有完全虚化的类前缀和类后缀。严格来讲,现代汉语中典型的、地道的词缀是很少的,类前缀和类后缀,特别是类后缀倒是不太少,如“类、准、超、度、品、率”等等。吕叔湘认为存在类前缀和类后缀是汉语词缀的一个特点。
三
词缀一般分为前缀、后缀、中缀。现代汉语里词缀到底有多少?这无法准确地回答,因为对词缀的性质人们的看法并不十分一致。语言学家们所列举的词缀数目多少不等,甚至悬殊很大,少的十来个(如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多的七八十(如张静《词·词组·句子》),把各家所列的词缀加起来大概有一百二三十个,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是否真是词缀是大可争论的。
1.前缀,又称词头。现代汉语前缀很少。较为典型的有“阿、老、第、初”。这几个词缀一般没有什么争论(胡裕树把“第、初”看作助词),但是把“初恋、初赛、初稿”等中的“初”看作前缀(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的“初”明显有实在的词汇意义。
除了“阿、老、初、第”等外,不少人认为是前缀的,如:非(非正式)、泛(泛神论)、无(无条件)、超(超声波)、反(反革命)、打(打听)等等,它们是否为词缀是有争论的。笔者认为这些不能看作词缀,因为它们还有较为实在的词汇意义,至多只能看作类前缀。比如说“反革命”的“反”,任学良认为是新起的词头(即前缀)(《汉语造词法》),但是很明显这里的“反”有“反对”的意思,不能看作前缀。孙常叙说:“不能把这种有明确的词汇意义的词素当作形态结构的抽象符号来看。”
赵元任把“禁”(禁用、禁看)、“可”(可爱)、“好”(好看、好听)、“难”(难看、难听)等都归入前缀行列。对此常敬宇表示了否定的意见。
2.后缀,又称词尾。后缀比前缀多,较为典型的有“子、儿、头、性、化”等等。对于后缀人们列举的比较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举了。人们列举得多,争论得也就比较多。比如说“儿”几乎都认为是典型的后缀,但是林伦伦著文对此提出疑问,理由是词缀应有一定的语音形式(音节),而“儿”不能自成音节,只是一种卷舌动作而已,因此难以成为后缀。
“员、家”常敬宇认为“都能在词典中查到它们的词汇意义,并不表示虚化的附加意义”,因此是词根,不是词缀。这里实际涉及对词缀性质的理解。
再如“主义”,武占坤、王勤、任学良等都认为是后缀。王力持否定意见,他说:“‘主义’并不是词尾,因为‘主义’可以独立成为意义,和西洋词尾一ism不同。如果我们承认‘主义’是新兴的词尾,那只是从汉语和西洋语言对比所得的结论。”王先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郭良夫提出的“零后缀”概念很是新颖。他说:“有一些多音节的动词,可以表示人的身份或职业,这就成了名词。这种名词就是带有零后缀的,零后缀表示的是‘执事者’。如:领导、编辑、编剧、调度。这种名词有的也可以带上‘者’后缀,如‘领导者、编辑者’。”这种“零后缀”的提出大概是深受印欧语研究中的“零形式”(zero)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