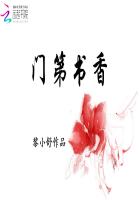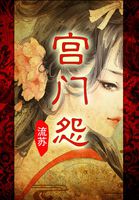消极修辞论
一、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
1.从语辞使用的三境界来看,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曾将语辞的使用分作三个境界:
(甲)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乙)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丙)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
语言运用的这三种境界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你怎样变换术语,其实质你无法改变。这其中表现的境界常用积极修辞,已成共识。糅合的境界要用积极修辞,也要用到其他修辞你无法否认,因为否认该境界也要运用其他修辞,就等于否认有糅合境界与表现境界的区别。那么这“其他修辞”是什么呢?从对立的角度来说只能是消极修辞。表现的境界有修辞,糅合的境界有修辞,记述的境界自然也应该有修辞,因为它们属于“对应题旨情境而来的语文运用”。这样,作为与常用积极修辞的表现境界的对立境界——记述的境界,其常用消极修辞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2.从修辞的本质来看,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
修辞的本质是一种言语行为,一种对语言进行选择、加工的言语行为。人们在一定的情境之下,依据特定的题旨对语言进行选择、加工,其具体目的虽然不同(有的可能是为了追求语言的生动、形象,增添特别的艺术韵味,有的则可能是为了追求语言的精确、简练、明白、晓畅),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即都是通过调适语辞以增强表达效果。因此积极修辞是修辞,消极修辞也是修辞。
对语言进行选择、加工有一个经典的修辞实例。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八,记载了王安石对《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由“到”,而改为“过”、“人”、“满”,最后确定为“绿”字的选择、加工过程。这种选择、加工的言语活动是修辞,下面这类对语言的选择、加工同样也应该是修辞。
唐朝诗人高适,在担任两浙观察使的时候,有一次去台州巡察,路过杭州清风岭。这时,秋意正浓,凉风飕飕。在苍劲的古松上,白鹤扑棱着翅膀,凉冰冰的露水,正好落在他的衣裳上。他观赏着修直挺拔的翠竹,幽雅清静的古刹,观赏着清澈的江水映照着前村的一弯残月,不觉诗兴大作,就挥笔在僧房上题了一首诗:
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湿衣裳。
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角竹房。
高适写好,吟哦几遍就走了。他虽然离开了清风岭,却还要琢磨着诗句,途中经过钱塘江,正好又是月亮西沉的时候,他仔细观察江水,发现月落的时候,江水随潮而退,只剩半江。这时,他联想到自己在清风岭上所看到的月亮,已经西斜,江水应该也只剩下一“半”。当时由于在夜间,又是从山顶远望,所以把“半江水”误为“一江水”。尽管走出百里了,他还是不辞辛劳,特地赶回僧房改诗,到那里一看,诗已经被人改了,正是把“一”字改为“半”字。
“到”、“过”、“人”、“满”改为“绿”与“一”改为“半”都是对语言的选择、加工活动,前者是修辞,后者自然也是修辞,只不过前者属于“使人感受”的积极修辞,后者属于“使人理会”的消极修辞。
3.从言语现象的多面性来看,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
任何言语现象都有多面性,也就是任何言语现象都有语音平面(记录下来有文字平面)、词汇平面、语法平面、逻辑平面和修辞平面,任何言语现象都可以进行语音平面的分析(记录下来的还可进行文字平面的分析)、词汇平面的分析、语法平面的分析、逻辑平面的分析和修辞平面的分析。例如:
秋天的美,美在一分明澈。
有人的眸子像秋,有人的风韵像秋。(罗兰《秋颂》)
这段言语现象可以进行语音平面的分析,如说(或读)的时候有声音的抑扬顿挫问题;可以进行文字平面的分析,如对楷体汉字的形音义的考察、汉字的运用分析;可以进行词汇平面的分析,如语词的理性意义、色彩意义(情感色彩、语体色彩),语词的结构的分析;可以进行语法平面的分析,如词性的分析、句子成分的分析;可以进行逻辑平面的分析,如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分析,对思维对象的断定的分析;也可以进行修辞平面的分析,如句式运用的分析、修辞方式的分析。
我们认为任何言语现象,无论是变异的话语还是常规的话语,是通顺的话语还是不通顺的话语,是生动的话语还是质朴抽象的话语,都存在修辞平面,因为任何言语现象的产生、存在都有一个对应题旨情境的问题,而言语现象与题旨情境的对应与否正是修辞平面的内容。修辞平面显然不等于积极修辞,那些对应于题旨情境的常规的话语,质朴抽象的话语也有修辞的问题,而这不是消极修辞又是什么?我们来对比两个言语现象:
(1)你爱看电影吗?你儿时看过的电影现在还记得吗?
这是黄西毓《全都是好人》一文的开头,两句话构成了一个自然段。这两句话没有上文所举罗兰《秋颂》开头的两句话形象生动,但它毫无疑问存在语音平面、文字平面、词汇平面、语法平面、逻辑平面、修辞平面,可以进行这些平面的分析。就修辞平面的分析来说这两句话是两个设问,它们并不要求读者回答,目的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为下文的展开作铺垫。这两句话适应文章的题旨情境,是较好的修辞。
(2)2001年6月6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上午10时40分,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全体师生和其他院系的学生代表聚集到这里。他们面前的主席台上坐着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还有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等人。
这是曲力秋《特别告别》一文的开头,三个句子,一个自然段。它不如罗兰《秋颂》开头形象生动,独具别致的艺术魅力,也不像黄西毓《全都是好人》的开头连用设问来感染读者,但它依然存在语音平面、文字平面、词汇平面、语法平面、逻辑平面、修辞平面,依然可以进行上述平面的分析。这几句话普通、平常,一片本色,但它对应文章的题旨情境,也有修辞。文章写朱镕基总理来清华大学出席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告别会,在会上发表了真诚的告别演说。因此交待时间、地点、主要及相关人物很有必要。这三句话较好地适应了题旨情境。其中不可否认包含有修辞。然而它不是积极修辞,只能是消极修辞。
4.消极修辞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与角度,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
消极修辞与词汇、语法、逻辑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以往的消极修辞研究缺乏修辞的全面观点,常常只从“要求”和“改错”的角度探讨,角度与方向产生了偏差,很容易使人感到消极修辞“在同语法、词汇、逻辑三家争地盘,或者说从它们三家的‘大锅饭’里分一瓢羹”。因此,“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角度”就成了否认消极修辞的学者们否定消极修辞最有力的根据。如季世昌、费枝美先生说:“从消极修辞的内容来看,把词汇学、语法学、语音学甚至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同修辞混为一谈,没有它独特的角度和内容。”齐沪扬先生在分析陈望道“两大分野”体系的局限时,也指出:“理论体系的外延是模糊不清的。它把自己建立在语法学、词汇学、逻辑学的夹缝之间,从而生出了无数‘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这样的关系表明了修辞和语法、修辞和词汇、修辞和逻辑之间理论上有许多重合之处。”谭永祥先生多次著文,认为消极修辞的内容跟词汇、语法和逻辑等界限不清,消极修辞没有自己的研究内容,从而否认消极修辞是种客观存在。如他在《“修辞的两大分野”献疑》,一文中说:“由于消极修辞的内容实际上都是词汇、语法、逻辑等学科研究的对象,消极修辞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内容的空壳。”
我们认为如果只从“改错”的角度来研究消极修辞,确实不易分清消极修辞与词汇、语法、逻辑之彼此。消极修辞否定论者也正是以此为突破口,否定消极修辞的存在。然而,以消极修辞研究中的偏差为突破口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大的方面来说,词汇、语法(包括语音)是研究语言规律,逻辑研究思维规律,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一样研究使用语言的规律,因此,消极修辞与词汇、语法、逻辑等有联系,但并不相同,更不会消融其中。举例来说,“假设”做为一种语义关系,逻辑学要研究,但逻辑学侧重的是前后之间的真值关系;语法学也要研究,但语法学侧重于句法结构,着重考察的是作为复句的构成成分——分句之间的一种假设与结论的语义关系。逻辑也好,语法也好,对于语言中的假设并不从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角度来研究,而消极修辞正是从功能、结构、方法相统一的角度来研究假设,从方法上概括出作为一种常规表达方法的“假设”的表达模式。姚汉铭先生对作为辞规的“假设”作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他在《假设辞规表示法探索》一文中对现代汉语中表示假设范畴的句子格局进行描写,从方法上对“假设”做出了概括:1.分句表假设;2.紧缩分句表假设;3.谓语表假设;4.主语表假设;5.状语表假设;6.指示代词表假设;7.隐性假设;8.假设在宾语中。
另外,“语音、词汇、语法如果能联系实际,讲点如何运用的问题,也不过各部分讲各部分的,知识是零碎的,是割裂的。而修辞学是研究综合使用语言规律,是研究‘准确的表达’和‘生动的表达’,它是全面地揭示使用语言的规律,如果离开‘准确的表达’,专讲‘生动的表达’,那必然成为‘空中楼阁’”。
从小的方面来说,某些具体言语现象的解释少不了消极修辞。郑文贞先生在《明确对象,加强消极修辞的研究》中作过如下的论述:
消极修辞的要求是使用语言的“起码标准”,但不等于没有“特定的要求”;消极修辞同词汇、语法、语音、逻辑密切相关,但不等于没有它“独特的角度和内容”。1978年高考语文试题改病句第三道题,毛病出在“凌晨早起,深夜晚睡”中的“凌晨”与“早”、“深夜”与“晚”意思重复,要求改为“凌晨起,深夜睡”或“早起晚睡”或“凌晨即起,深夜才睡”。这既不是语法问题,也不是逻辑问题,只能说是修辞问题;但它又不是积极修辞问题,只能说是消极修辞问题。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举过一个例子:“大姐告诉我,‘祖母叫你’。走到祖母房里,母亲和她正在默默相对地坐着。”第二句的“母亲和她”应改为“她和母亲”才对,因为承上一句的意思,着眼点该放在祖母“她”上。原句的问题,同样不是语法问题、逻辑问题,只能说是消极修辞的问题。怎能说消极修辞没有“特定的要求”、“独特的角度和内容”呢?
郑文贞先生提及的两个言语实例有力地说明了消极修辞是一种客观存在,词汇、语法、逻辑等代替不了消极修辞。
我们认为作为研究常规的言语表达的消极修辞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角度。它并非“本身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空壳”。它也并非只是从词汇、语法、逻辑的角度来改病句的“病句修辞学”,其研究内容并不是“词汇、语法、逻辑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十几年来的辞规研究实际已经有力地证明了消极修辞不是词汇、不是语法、不是逻辑,而是实实在在的修辞。那么,消极修辞独特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其研究内容就是常规的语言表达,包括辞规、辞风。其研究角度就是功能、结构、方法的统一,简言之,就是“方法”的角度。
还有的学者曾从专著的缺乏和术语的缺乏角度否定消极修辞的存在。我们认为消极修辞专著的缺乏与术语的缺乏属研究主体的问题,不能因研究主体的问题而否定客体的存在。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不是消极修辞的专著是明显的,华宏仪先生的《汉语消极修辞》虽名之“消极修辞”,但不是好的消极修辞的专著,至少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较理想的消极修辞的专著,然而这只能说明消极修辞的研究有缺陷,或者有重大缺陷,却不能据此推论说消极修辞不存在。我想,就目前而言,只要消极修辞研究同仁们共同努力,较为理想的消极修辞专著是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出现的,因为最近十几年来消极修辞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个案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辞规理论及其研究为较为理想的消极修辞专著的出现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至于消极修辞的术语问题现在已不成问题。十几年来的辞规研究可以说已经解决了或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像“辞规”、“辞风”等术语正是消极修辞的独特用语。其实,只要消极修辞是个客观存在,在研究过程中,人们自然会创造一些适用于研究对象的独特用语,这个问题并不太难解决。
二、消极修辞的研究内容和范围
消极修辞的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的内容是什么?陈望道先生对此有明确的阐述。在《修辞学发凡》中,陈先生认为消极修辞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意思之明通表示法”。它“讨论如何才得把自己的意思明通地表出来”,这方面偏重于内容,修辞时“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说事实常以自然的、社会的关系为常规”,“说理论常以因明、逻辑的关系为常规”。研究消极修辞就要从内容方面研究遵循常规,进行伸缩,以求明通表达的修辞现象。二是“语言文字之平稳使用法”。它“讨论如何才得把自己的思想平稳地传达给别人”,这方面偏重于形式。消极修辞的形式“也受逻辑、文法之类的约束最严紧”。研究消极修辞,还要从形式方面研究遵循逻辑、文法规律,平稳使用语辞的修辞现象。此外,还要研究修辞病例,对此《修辞学发凡》未作明确的阐述,我们体会其中的“零度以下”指的该是这种现象。1964年3月陈望道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消极修辞研究修辞病例:“假如把通顺明白看作‘零点’,那么消极修辞就是研究零点和零点以下的东西,所谓零点以下的东西就是不通的,消极修辞就是要讲究通顺明白。……我在《修辞学发凡》里举了许多古书中不通的例子。如:‘无丝竹管弦之盛’,‘丝竹’是借代音乐,‘管弦’也是借代音乐,这句话等于说‘无音乐音乐之盛’,所以不通。又如‘不得造车马’,‘车’可造,‘马’不可造,这在连贯上也是不通的。因此,修辞学研究病例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之,陈望道先生认为凡采用明通表示法和平稳使用法的零度修辞现象以及零度以下的修辞病例,都是消极修辞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