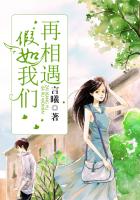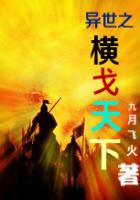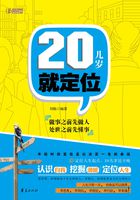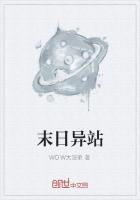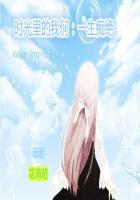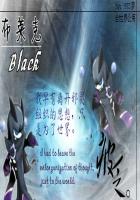不久,我读完了张朴送给我的书,可是心里却有困惑不能解释,我找了个机会决定继续向张朴请教:“老师,南怀瑾在书里说台湾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把传统的东西都丢了不应该,他说了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这未免太抬举传统私塾教育了吧?” “你看到的是师道那一章。不错,我们国家的师道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在不断衰亡,这是不应该啊!” “可是我们国家过去的私塾教育不讲科学,只学习四书五经这显然跟不上时代了啊?”我不无困惑地问。 “谁告诉你我们国家传统的教育不学习科学了?说,谁告诉你的?”张朴一连声地问。 “这,您小时候上私塾不就没学吗?” “你读过易经吗?”张朴打断我的话问。 “没有,我听说易经很深奥。所以……应该不是我这个年纪的人该读的,况且我们老师说女孩子不善于理科……” “屁话,这句话才误人子弟呢!”张朴突然大叫起来。 “你们老师说的女孩子不善理科学习,这都是骗人的鬼话。”我被吓了一跳,“老师,我说错了什么?”张朴表情凌厉,似乎恨不得要把说这句话的人打个半死。好半天,他才摆摆手,示意这不是我的错:“这不怪你,要怪只怪你上学时,教你的那些老师教你的全是假知识和恶知识。” 听了张朴这句话我更无法回答了,我又想起了初见张朴时他说的那番话。“老师,我才疏学浅,您刚才所说的我很疑惑,恳请您赐教。”张朴忽然对着我笑了笑:“你就是这点好,愿意虚心地听我说,换别人早就不耐烦了。” “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呢。” “好,我这么说吧。民国20年,我上私塾时学的内容里就有易,当时我的先生告诉我:易经在中国学问里的地位是:群经之首、百集之冠。” “哦?这么重要?” “对,想研究中国的学问不懂易经是不行的。”听了张朴的话,我突然觉得似乎《史记》的结构跟易经有关。“老师,我突然觉得史记的谋篇布局于易经有某种联系?”我于是问张朴。 “是,12本纪、30世家、70列传……合起来一共一百三十篇。史记里面的内容又互相辉映,本纪为纲,世家、列传是围绕本纪依次排开的星宿,这种谋篇布局正显示了司马迁本人易经上的深厚功底。”张朴说道。 “我从汉书司马迁列传中知道司马迁本人曾经参加过修订太初历,他是个历史学家还能参加历法的修订?我觉得他很有学问。” “这就是你们现在年轻人浅薄的表现。”张朴突然严肃地说。 “哦?为什么?” “过去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过去没有文理分科这种事,我们上私塾那会儿是所有学问一起学,这样就可以奠定一生的学问思想基础。” “哦!” “你们现在分文、理科,文科的不学数学,理科的不学文学,好像彼此有很深的鸿沟似的,不敢越雷池一步。照你们的思维当然不能理解司马迁能修订历法了,这和你们只是把他定义为历史学家一样。” “嗯!”我无法应答张朴的话,我只有乖乖站着听得份儿。 “浅薄了呀!学问的精神都死掉了啊!”张朴一个人边摇头边自言自语。猛然,他一只手握紧了拳头狠狠砸在桌子上。 “老师,依您看,西方的数学体系是否就如中国的易经呢?”虽然见此情形,我还是接着问道。 “不一样,依我看到的情况看,这里面有区别,你去那边拿本书过来。”张朴指了指他书架里面靠窗户一侧的那一排。我走过去,看见有几本包着牛皮纸的书,写着:《西方文化里的数学》、《证明与反驳》、《数学恩仇录》、《数学是什么》……这些数学书居然出现在一位书法教授的家中,张朴的学问还真广啊!我在心里暗暗想。 “你看到了吗?看到了赶紧拿过来。” “全都拿来吗?” “全拿来。” “这些书,全是您在美国时买的吗?” “对!你没看见全是英文版吗?”我翻开一看,可不是嘛,里面全是英语。书的封面写着作者名字,我虽然英语水平不好,但还是可以隐约认出上面写的人名是克拉克。 “这本书的作者是克拉克?” “不错,他是我在美国留学时遇到的一位思想积极的数学教授。” “这些书,恐怕中国还没有吧?” “前几年没有,这几年应该会翻译过来了吧?” “您全看完了吗?”我指了指书说。 “嗯!基本上都看完了。” “哦,那您快说说,您有哪些心得?” “呵呵!你这么急迫地想知道?”张朴笑了。 “张老师,我说句心里话吧,我爱慕学问,从小就是如此。现在我依然怀着当初上学时的那种对学习的迫切渴望,我知道您是位学问深厚的教授,我愿意听您多讲讲学问。”张朴点着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对学问和思想有一种罕见的执着,一种少有的热忱。这在其他学生身上,尤其是在女同学身上是非常罕见的。” “老师,那您就对我多教诲教诲。” “好,说到数学,它是一个有魅力的学问。” “魅力在哪儿?” “数学是西方文化的根基,是理性的结晶,简单地说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学校老师只讲如何解题,不讲别的。” “那是你们老师不懂数学的精神,他只知道解题。所以他教会你们的就只有如何解题,其实数学的魅力不在于你解的那道题,数学的魅力在于它的猜想,也就是设问。” “您是说?哥德巴赫猜想吗?” “数学猜想有很多,哥德巴赫猜想只是其中一个啊,比如费马大定理、希伯尔公式的23个问题等等。但是任何猜想都令研究数学的人兴奋。” “为什么?”我不明白,于是又接着问。“我知道陈景润因为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而名闻世界,可是听说他用了很多方法、费了很多功夫才证明出来。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几年也不出去,这种纯粹的逻辑推理劳动太枯燥了啊!” “那是你认识有误区,数学是个美丽的学科,它是连接现实和想象的桥梁,是可以证明想象的工具。” “老师,我不是太懂您的话。” “哦!这怎么说呢?西方文化一切从理性出发,西方人经历了中世界的愚昧黑暗之后,在通往思想开化的道路上,数学的理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可以什么都不相信,但是他们却相信理性的思维成果—数学的威力。他们认为数学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欺骗他们的,所以理性的思维就渗透进了西方人生活里的各个角落。” 对于张朴的解释,我还是觉得不明白,我依然觉得这个老教授肚子里的学问还真可以说是莫测高深。于是又问“老师,那么数学对西方人的影响是否和易经对东方人的影响一样?” “可以这么说,但是易经较之还要深刻许多。”“ 您说得太宏观了,我真的有点不明白。我们老师只教我们如何做题,教的都是微观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您能从微观角度谈谈数学。”张朴笑而不答,默默地看了我半天,看得我很不自在,使我一时反省自己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 “张老师,可能我问得太多了。您是教书法的,我问的这些问题也许对您来说不好回答是吧?”张朴摇了摇头,“让我先问你一句,你从微观学习了数学,可是在你的思想意识里你认为自己学明白数学了吗?” “没,我只是学会做题了……” “我当然知道你会做题了,可是在你的思想里有没有数学的清晰形象呢?” “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明白,是吗?你们老师教你学了半天数学,可是你们学到最后却连数学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们这不是越学越迷茫了吗?” 张朴的话我又一时答不上来,我大学里学的是中文,数学我早就不学了,可是即使是我不学了,我印象里也感觉没有学明白数学。张朴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不是太深刻了,他似乎更应该去问数学系的学生。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是说您的问题问得有点深,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很想全部告诉你,可是你的基础太浅了,数学本来就是属于思想领域的,抽象的很,基础浅了又怎么听得懂?” “老师,您是在怪我吗?” “不,我是对你怀着殷切的希望。话说的重了,你是不是会往心里去?” “不!不!不会!老师。因为买字帖的事,您都那样骂我了我都没往心里去,这次怎么会呢?我是恨自己没出息。” “别这么说,孩子。你是个要强、聪明、努力的好孩子,假以时日你是一定会出人头地的。不过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话,任何学问,都是思想在前,学问体系在后,思想是学习学问的旗标。要不然啊,你会越学越迷茫的。”张朴拍着我的肩头说。 我半懂不懂地点头称是,离开了张朴老师家。可是在回去的路上我却还在咀嚼着张朴的话,数学是证明想象的工具?还有最后这句:“一切学问都是思想在前而学问体系在后,思想是学习学问的旗标。”可是我越琢磨却越觉得,照这样我们现在的学生中没有几个有思想的人啊。
同类推荐
二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刊于明代崇祯年间。每集40篇,共80篇,故实有拟话本78篇。作品多是取材于古往今来的一些新鲜有趣的轶事,敷演成文,以迎合市民的需要,同时也寓有劝惩之意。二拍部分作品反映了明代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等篇,通过对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和他们海外冒险理想的描写,反映了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市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部分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如《李将军错认舅》歌颂了坚贞的爱情,《满少卿饥附饱飏》批判了忘恩负义、富贵易妻的丑行,提出了在爱情婚姻中男女平等的要求。
热门推荐
时光里的我们:一生痴绝
风吹起如花般破碎的流年,而你的笑容模糊又清晰,成为我命途中最美的点缀,若有、若无,如梦、如幻,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后来,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那年。过去的那些琐碎,拼凑出了青春,痛过,爱过,恨过,笑过,幸福过。悲凉的青春里,信念敌不过流年。终究破碎一地,无法挽回。每每念及,那尖锐的碎片划开我的伤疤,旧时的疼痛让我清醒。流年里那些山盟海誓都已如烟般消散,岁月里当初说好一起闯天下的人已在人海中失散。透过浅浅的微光,看到时光里,曾经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