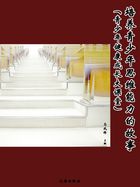孟小伟去世后的第二天,我们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这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搅乱了我们家里贫困但又平静的生活,也把我的爸爸拖到了万劫不复的可怕深渊。
我其实应该憎恨这两个人的,真的,如果他们当初没有出现,我和我的姐姐就不会失去这一切:乐观可亲的爸爸,饭桌上简朴但是其乐融融的一日三餐,余香的白色婚纱,余朵的明星梦,还有我将来要读的大学……可是回想八月里发生的事情,我始终都觉得那就是一团迷雾,雾气浓重,白茫茫一片,我们大家都被裹挟在当中,看不清来路,也见不到结果。
我的爸爸,他就是在雾中跟我们走散了,他离开了我们大家,不声不响地、一意孤行地,而且是无法回头地,走向了一条偏僻而又危险的小路。
说到底,我们家里的人都是善良的人。丁老师上语文课的时候讲解说,“善良”是个褒义词,可我觉得“褒”并不能说明一切都好,因为我在一本书中读道: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的两面性。“善良”也是这样,当你满怀同情和怜悯,努力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灾难已经埋伏在你的身边,虎视眈眈地盯住了你,时时刻刻都能张开大嘴把你吞进去。
到我们家里来的这两个人,一个五十岁,身架眉眼跟我爸爸有点像,可他有病,还病得不轻,佝偻着腰,穿得很破烂,脸瘦得像丝瓜瓤,肤色灰暗得像烧成焦黑的炭。另一个二十五岁,矮胖,皮肤也黑,却是油光铮亮的黑,鼻尖总是汪着一层油,额头上脸颊上长满黄豆大的粉刺,没事的时候他总爱拿两个一块钱的硬币去挤它们,挤破了,流血,然后结疤,脱了疤后,一颗一颗红得很神气。
我爸爸指点我们叫人:五十岁的这个是他嫡亲的堂叔,我们该叫他“爷”,二大爷;年轻的这个,二大爷的儿子,小名狗伢,算我爸的堂弟,我们得叫他“狗叔”。不,不能这么叫,我爸说,这么叫太不严肃,干脆简单点,省去名字,就叫个“叔”吧。
二大爷和叔,都是从爸爸老家来的。二大爷得了病,咳嗽,咯血,还喘不来气,乡下医院只会挂抗生素,别的不会治,没法子想,投奔在大城市打工的我爸爸来了。
“真是没法子想。”二大爷上气不接下气地诉苦,“一大家子人,孙子外孙子都有几个了,个个都是土里刨食的命。这年头,种田能种出什么名堂呢?糊嘴都不够。老老小小都指着我的手艺弄几个零花钱呢,我可真是不能死。我死不得啊,有亮……”
有亮是我爸的名字。这名字我听起来很陌生。我们天使街的邻居都喊他“老余”,没人知道他叫“余有亮”。
我二大爷有什么能挣钱的手艺呢?就是扎纸人纸马纸车纸房子什么的。我爸爸解释说,农村人死了,送葬要烧这些纸扎的东西,不烧的话,就是后人不尽孝。这些车呀房子呀什么的老人生前一样没有沾到边,死了还不叫他带到阴间享受一下子,太枉为一世了。所以二大爷的手艺在农村能挣钱。
也怪二大爷的儿女都太笨,没学成他的手艺,弄得他生个病还怕家里人断了零花钱。
我爸是个很讲义气、很要面子的人,别说他的堂叔堂弟投奔他而来,就是老家村里沾不上多少边的亲戚邻居来,他也不会回绝了人家,或者一顿饭就把人家打发走。
当天晚上,我妈指挥我的两个姐姐,把家里狭小的空间重新做了一番布局:余香和余朵让出她们外屋的双人床,在里屋我的小床上挤挤睡;二大爷和叔睡在余香、余朵的床上;我在外屋饭桌下铺张小草席,打地铺。
余朵对这个安排十分不乐意,因为我的那张小床只有一米宽,一个人睡觉还过得去,这样的盛夏天气,要让她跟余香两个人汗淋淋地滚在一起,前胸贴后背地睡,真不是好受的。可是当着家里客人的面,余朵又不好明明白白说她不乐意,只能拐弯抹角地挑唆我:“余宝,你要小心点噢,别让老鼠半夜咬了你的鼻子噢。”
我一点儿不反对睡地铺,所以我回答她:“老鼠才不会咬男孩,男孩肉结实,又不香。”
“那你要当心蟑螂,蟑螂会爬到你嘴巴里撒尿的。”
“我把嘴巴闭紧了睡觉。”
“还有蚊子呢!你不挂蚊帐,蚊子能把你咬成烂香瓜。”
“有蚊香啊,头前一盘,脚后跟一盘,看蚊子敢来?”
“哎哟,余宝,你个蠢货!”她恨恨地骂我。
我一点儿不生气,身子一矮,腰一弓,哧溜钻进了饭桌下。我的草席恰好卡在桌子的四条腿之间,头顶上的桌肚像蒙古人露营的帐篷,既安逸又新鲜。我对自己的一席之地满意极了,左翻翻,又滚滚,怎么都稀罕不够。
我爸爸接连起了两个大早,替二大爷排队挂号。
为什么挂号还要排队呢?因为二大爷想看省人民医院的专家门诊。
我们天使医院的号最好挂,走到窗口交上钱就行。离我们家不太远的那个市立医院门诊的号也好挂,顶多排上十个八个人的队。唯独省人民医院的专家号,想要挂上一个,比上天摘星星还要难。想想看,专家们都老啦,一天最多看上十几二十个病人吧,可是从全省还有外省慕名而来的病人该有多少啊,不排队的话,专家的门槛不得天天挤坏几道啊。
我爸爸头天是早晨六点钟赶到医院的。挂号窗口打开前,先有人用纸条发了号,我爸的号头是五十六。可他一打听,贴在窗口的告示是“限挂二十人”。差得太远了,没办法,回家吧。
第二天爸爸再早起,五点钟到医院。明明排在前二十名,等他挤到窗口,穿白大褂的小姑娘把头伸出来:“没号了,明天再来吧。”我爸爸急得跺脚:二十个号呢,怎么只挂十个人就没了呢?号头流到哪儿去了呢?
还没等我爸想明白事,有个染黄头发的小伙子就过来,把我爸扯出医院门,挤眉弄眼问他,家里人着急看病啊?想不想买张高价号啊?我爸信口问一句:高价号多少钱?那人一伸巴掌:五百块。我爸爸哼都没哼一声,扭头走了。他才不会白花这个冤枉钱。五点钟挂不到三点来,三点不行干脆排通宵,不信医院跟黄牛党窜得那么好。
号挂不上,狗叔一点儿不急,反正有吃有住,饿了有人端饭,闷了上街闲逛,生病的老爷子还有我爸我妈伺候着,比老家日子好过得多。
可我的两个姐姐不干了,因为这两个陌生人一来,家里的秩序全都被他们弄乱了。
首先一个,狗叔太能吃。那不是一般的能吃,是我们在整条天使街的邻居中都没有见到过的能吃。狗叔的嘴巴里连接的好像不是喉咙和胃,而是一根直通通的比茶杯还要粗的塑料管,任何食物到了他的嘴边上,彻底一倒,哗啦啦地就下去了,顺滑得不打一点儿磕巴。你比如说,头天他们来,晚饭来不及仔细准备,我妈就做了一大锅肉丝青菜面。用的是头号钢精锅。我妈讲礼数,端锅上桌的时候就嘱咐我们,客人先吃,吃完了我们再吃。哪里能想到,一大锅肉丝面,除了先盛给二大爷的那一碗,余下的居然全被狗叔倒进了肚子。一大锅啊,盛到碗里,十碗八碗总要有的啊,狗叔的肚子是什么肚子,真叫我们开了眼界。
狗叔吃得多,三顿饭就要做得多。在我们家里,买菜做饭基本是余香的活儿,如果说之前她做五个人的饭,现在起码要做十个人的饭,多出了双倍的活儿。而且我爸这个人待客不抠门,饭桌上两荤两素是必需的。余香一大早要拽着我和余朵上菜市场买菜,三个人吭哧吭哧把菜篮子背回家,接下来的活儿就是择菜,洗菜,切菜,淘米,一大锅一大锅地做熟。到饭菜端上桌,狗叔根本不懂客气也不懂谦让,屁股还没在凳子上坐稳呢,风卷残叶似的,荤的素的一股脑儿下了肚。
余香的好手艺来不及被欣赏,眨眼间没了踪影,弄得她好恼火,愤愤道:“明天买鱼回来烧,买小猫鱼,刺儿多,卡死他!”
可是小猫鱼根本卡不死狗叔,人家连骨头带鱼,咔咔一嚼,下去了,咽得眼睛都不眨。
余香用劲拿眼睛瞪他,鼻孔里呼哧呼哧扇气。我爸那边还笑眯眯地劝客:“吃饱啊,吃饱啊,哥这儿鱼翅海参管不起,粗茶淡饭还是管够的。”
狗叔本来都要丢下筷子了,听我爸这一说,干脆又盛一碗饭,把剩下的鱼汤倒进去,搅一搅,三口两口,扒拉进了肚。
余朵一个劲儿地遗憾,城里这几天怎么不举办吃包子喝啤酒的大赛呢?如果把狗叔弄过去,冠军肯定是稳拿啊。
狗叔吃得多,放屁也多,想必是城里饭菜比乡下油腻得多,不那么好消化。晚上我跟他睡一个屋,只听见床上“噗噗”地响,满屋弥漫着冲鼻的臭屁味。我头前一盘蚊香,脚后跟一盘蚊香,烟雾滚滚,盘旋缭绕,还是压不下狗叔的屁臭。半夜里我拎着草席爬起来,推开里屋的门,在我爸妈和余香、余朵的两张床之间将就着睡下来。结果余香摸黑上厕所,一脚踩在我的胳膊上,她吓得哇哇大叫,以为踩着了一条滑腻腻的粗蟒蛇。我也跟着大叫,因为我的胳膊几乎要被她踩成骨折,疼得要命。我妈赶紧拉亮灯,看见我们两个人惊慌失措的狼狈样,问明原委,又好笑,又心疼。可她不敢多话,因为来的是我爸的亲戚。
跟狗叔一比,我二大爷吃得倒是少,少得就像猫吃食。你看他端起饭碗那副难以下咽的样子,就觉得人活到这份上真没劲,世界上就没有一件值得让人高兴和愉悦的事。
我爸劝他:“二叔你还是要多吃,吃饱饭食才能抗病。”
二大爷愁眉苦脸:“我也想啊,可我喉咙里打坝,咽不下去啊。”
我不明白他的话。人的喉咙里怎么可能“打坝”呢?又没有土块又没有水泥,拿什么打上去呢?
我同情二大爷的病,可我实在不喜欢每天面对他那张老丝瓜瓤一样焦苦的脸。你跟这样的一个人待在一屋时,心里会恐慌,也会绝望,就好像有一座珠穆朗玛峰这样的山头压在你心上似的,让你喘不上气,透不进阳光。
还有,我和余香、余朵都腻歪他往破花盆里吐的那些痰。一开始他直接就把痰吐到地上,那更恶心。我们家里虽说是水泥地,可我妈每天把拿拖把擦得干干净净,他这么一张口就往地上吐,实在太过分,连我爸都忍不住皱眉头。可我爸又说,农村人就是这习惯,因为脚底下踩的都是泥巴地,天生适合吐痰这件事,二大爷都已经吐了几十年,你叫他现在改,憋着,也不容易。我妈不甘心,试着从阳台上找了个破花盆,往里面放些沙土,拿到二大爷床边,告诉他这是痰盂,专门吐痰用的,有痰吐到痰盂里面去。谁知道这样一来,二大爷仗着有了吐痰的家伙,从此全没了顾忌,就好像一下子完全敞开了喉咙一样,日日夜夜咳个没完没了,也吐个没完没了。他吐出来的痰不是白色的,也不是黄色的,是花花绿绿有红有紫的,看起来怪异得瘆人。而且那痰还散发着一股怪味,腥,腐臭,把红头苍蝇都招得一拨一拨往家里飞。我妈心里很害怕,不知道二大爷得的是什么病,担心我们几个小孩会被传染,但是又不好说,更不能赶客人走,她要真说一个“走”字,我爸肯定会跟她拼命。
总之,那两天我妈真是焦心死了,她说她出门干活儿都走神,擦地把水桶碰翻了,擦桌子把人家温董家的一只花瓶打得粉碎。她说,还好那花瓶是景德镇买来的新货,温太太人又好,没有叫她赔。如果是古董,那才惨,把我们全家五口人全卖了都抵不上一只瓶的钱。
我爸第三回去医院,下一个大决心,半夜两点起床,三点不到,打着哈欠站到了挂号窗口前。居然还有两个人比他更早,一打听,是安徽人,前一天晚上赶过来,通宵没睡。我爸回家跟我们感叹说,农村人请名医看个病,真是不容易啊,就冲这份辛苦劲,天王老子都要掉眼泪。
呼吸内科的专家号自然是拿到了。三点钟排队还拿不到的话,黄牛票贩子们都该杀。
我爸拿到号头心花怒放,急急忙忙挤车回家,又急急忙忙带上二大爷和狗叔挤车返医院。其实他打个电话给我们,我和余香、余朵都能做这事,可他就是不放心,生怕大城市的居民时时处处都会欺负农村来的人。
二大爷在医院受到了很细致的问诊,抽了血,拍了胸片,做了CT,还有奇奇怪怪的我爸爸都说不上名字来的化验和检查。他们父子两个带在身上的大几千块钱就这么飞快地一点儿响声都没有地花出去了。狗叔每次解开裤腰带拿钱出来时手都发抖,他被惊吓得不轻,不明白那些铮光闪亮的机器为什么一靠近人身子就会把钱吸走。他抱怨说,那个老大夫看着那么祥和贵气,实际上心特狠,可着劲儿让人做检查,肺上有毛病就查肺吧,干吗要查血呢,查肝呢,查脑袋查屁股呢?真是杀人不眨眼睛哦。
狗叔一抱怨,我爸心里就不好受,因为专家号是他挂来的,检查费用这么昂贵,这里面有点不明不白的意思:为什么偏选了这个专家啊?是不是跟专家串通好了要来坑我二大爷的钱的啊?哎哟,总之好人做不得。
然后,我爸为了心里能够过得去,接下来的检查费用,他就抢在狗叔前面掏钱,还一个劲儿地声称:“我刷卡,我刷卡。”
刷卡的钱就不是钱了吗?偏我二大爷和狗叔还真信,真以为看不见的钱就是可以白花的钱,花多少不心疼。
一圈检查做完,根本没等到最后结果出来,老专家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爸:“病人肯定是肺癌。农村人过来一趟不容易,就别耽误了,赶紧办手续,住院治疗吧。”
我爸带着二大爷他们到住院部,交押金。癌症病人的住院押金,起点就是三万块。开票的小姑娘说,这还只是手术费,后期要化疗的话,费用会更高。
三个人刹那间变成三块花岗石,硬戳戳地立在住院部的门廊里。谁有三万块钱?狗叔的裤腰里肯定翻不出,我爸的银行卡上同样刷不出。
二大爷焦苦着一张脸,呼哧呼哧喘一阵,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别再操心了,回吧。人得了这个病,治也是白治,何苦借钱背债给自己找绝路。”
“不行。”我爸说,“你是我叔,你投奔了我,是看得起我,你要是就这么回,老家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我。”
“不会,你都已经替我们刷过卡了,我爸他领情。只可惜你的卡不是财神爷的聚宝盆,不能够刷一回涨一回。”狗叔啧嘴。
“回!狗伢子,赶紧买车票去。”二大爷红头赤脸,态度坚决。
“不能回!叔,你这是打我的脸。”我爸伸开手臂阻拦。
“有亮,你是孝顺孩子,可你不是阔佬,耗不起这绝症,叔得认命。”
“叔啊!叔,你们容我半天,我想想办法行不行?”
话说到这儿,我爸已经是恳请,是乞求了,我二大爷就是再坚决,也不能不顺着我爸的意思了。
这样,我爸把二大爷和狗叔两个人留在医院里,让他们找个长椅坐着,等他回家筹钱,再过来送他们入病房。
我爸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妈、余香、余朵、我,我们全家人都在,并且齐刷刷地坐在饭桌前,似乎等待着我爸走过来对我们宣布某一个重大决定。
“哈哈,人聚这么齐,给我开欢迎会呀?”我爸故意说句笑话,要把沉重的气氛搅得轻松点。
我爸没成功,因为谁也没有笑。
之前我妈就嘀咕过,二大爷的病恐怕不是什么简单的病,他那脸色,他咳嗽吐痰的模样,多吓人啊,这一进大医院的门,不把家里淘个倾家荡产都不作数。
二大爷进城治病,总共带了多少钱呢?昨天狗叔脱了外衣进厕所冲澡,余朵偷摸了他裤腰里的那个布兜,告诉我妈说,只有这么厚的一叠钱——她用拇指和食指比画了半厘米的一个高度——最多五千块。
余朵偷看人家钱,这样的行为很可耻。可余朵就是这么鬼精的一个人:什么事情都爱打听,什么事情都想插手。
我妈听了直叹气。她知道,这钱在农村已经是一个大数目。她说在她们贵州,老家人到卫生所里看个病,花两三百块钱都心疼。老家人不知道大医院里花几十万上百万看病是什么样的概念,不敢想,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带上五千块出门,这在二大爷家,已经算是放手一搏的意思了。
也因此,从昨天开始,我妈在心里就做好了应对难关的准备。她还偷偷嘱咐我们三个小孩子,爸爸如果想花钱,就让他花,毕竟二大爷是来投奔我爸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爸爸的老家人在背后戳他的小指头。
道理都明白,真正落实到钱的问题上,谁都没有辙。
我妈忍不住老话重提:“要是我那张银行卡……”
她想说的还是我爸去ATM机上取钱被骗的事。她耿耿于怀。那是整整一万块钱。
我大姐余香慌忙扯我妈衣服,不让她说。
“是哦是哦,一万块钱,其实也顶不了什么大用场。我听温太太说,她家老爷子中风住院时,那种重症病房,一天就得花一万。”我妈连说带比画的,给自己打圆场。
“一天一万,一天一万……”我爸嘀咕,“从前住皇宫都花不了这么多钱。这不是治病,这是杀人。”
我看见余朵的嘴皮子一个劲地动,她肯定很想说句话。我用眼睛死死地盯她,让她别说。在这样的事情上,小孩子最好别插嘴,不然就是讨骂。余朵把脸皮都涨得发红,不过她还是忍住了没开口。
我爸妈小声讨论着能够从谁那儿借到钱。爸爸的工友同事,天使街的街坊邻居,妈妈的贵州老乡……算来算去,真有钱的一个没有。没钱的呢,借上三百五百,仨瓜俩枣也顶不了大用——医院里不是说了嘛,手术押金三万块,后期化疗什么的还得往里填,填多少暂时没有数。
我妈妈算着算着伤心起来,叹气说:“像我们这种人家,三个人挣钱,两个人念书,平常过日子看看还行,真碰上事情,才晓得破船经不得风雨。”
我爸两眼发红地瞪她:“那怎么办?让我叔走,回老家等死?”
我妈很委屈:“我说过这话了吗?我不就是埋怨自己不中用吗?我挣不了大钱,帮不了你的大忙!”她说着哭起来。
我爸就吼她:“烦不烦啊?你烦不烦啊?动不动就晓得哭,哭有屁用!”
他起身,大步冲出家门,等我追出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得不见了踪影。
我妈擦擦眼泪,起身到厨房,察看她做好了盛在盘子里的几个菜:炒豇豆,毛豆米烧茄子,麻婆豆腐。她后悔说:“你爸半夜出门去挂号,到现在米水还没粘牙呢,我该让他先吃饭再说事的。”她忍不住地走到阳台上往外面看,“不会饿晕在哪儿吧?天热,心里再急……唉!”
我们三个小孩陪着我妈,吃完了这顿说不清是中饭还是晚饭的饭。我们语文书上有一个词,叫作“味同嚼蜡”,丁老师讲得口干舌燥也没让我们明白“蜡”嚼在嘴里是个什么滋味,可我现在无师自通,把这个词的意思领会得彻底。
我爸最终还是弄到了钱,把二大爷送进了病房。护工自然不用再请,狗叔是现成的,租张塑料躺椅,就在病房里安营扎寨了。缺点是饭量太大,每次打饭都要了再要,把那个送饭阿姨磨叽得发火。阿姨恨恨地用饭勺嘣嘣嘣敲狗叔的头号塑料饭盒:“没见过你这样的吃货,你比牛还能吃!”
狗叔呢,任她数落,绝不还嘴,该多要时照样多要。好在其他病人们饭量普遍小,相互间扯一扯匀一匀,打饭阿姨不见得有多吃亏。
我爸到底是从哪儿弄到这笔住院费,是借的,还是怎么的,他死活不肯说,怎么问都不说。
“挣钱是男人的事,花钱是女人的事,你管这么多干吗?”他这么回答我妈忧心忡忡的话。
我妈私下跟我们嘀咕,她别的不怕,就怕我爸借高利贷,再就是帮人贩毒。借了高利贷,一辈子就算是被恶魔缠住了,想要脱身难上加难。帮人贩毒呢,那更吓人,逮着了是死罪。可是普天之下,还有什么钱比这两样钱来得更快更容易呢?
“阿弥陀佛,”我妈两眼望天,虔诚无比,“菩萨老儿你要保佑他,别让他犯浑,别让他走黑道,千万千万不能啊!”
除此之外呢,我妈干活儿更勤快,伺候我爸更小心。只要我爸在家,她总是两眼不离他的身,有时候还发愣,眼珠子胶死了似的,半天转不动。我知道,我妈这样的神情,是在琢磨他,也是在怜惜他。她不敢对我爸做的事情说长道短,但是这不代表她心里没意见,没想法。她是用她的关心体贴,委婉地表达她的担忧焦虑。
我妈心里的意思,爸爸看懂了没有呢?明白没有呢?我不知道。我觉得玄。因为爸爸仍然不肯在钱的来源上透露一个字。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二大爷开过刀,割去癌细胞,再做上一两次化疗,出院回老家,我爸的责任就算尽到了,他也不必接二连三地冒险求财了。往下二大爷还能活多久,那是二大爷的寿数,我爸左右不了。可没想到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怪异,它就是不肯往人圈好的方向走,它非要跟人拗着拧着对峙着不可。
二大爷的术前体检单出来,主刀医生拿着单子很严肃地通知我爸,肺癌暂时不能动,因为心电图显示老人家有冠心病引起的心肌梗死,情况还挺严重,全麻手术有风险。
“那么,那么怎……怎……怎么办?”我爸当然就发了蒙,基本上语无伦次。
医生指了一条路:“最保险的方法,先解决心脏问题,微创手术,放支架。”
“什么叫支架?”我爸当时的脑子里,联想到的肯定是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
“支架嘛,扩充血管,能让心脏正常搏动的器械。”医生有点好笑地看一眼我爸,“你不懂没关系啦,你只要知道放支架可以治病就行。”
当然当然,我爸不需要知道心脏里面放支架有什么用,可他必须知道的是放一个支架要付多少钱。
了解的结果,价格高低不等。进口支架,一个就是几万。国产的,少过一万也不可能。而且二大爷的心脏已经在苟延残喘,放一个支架没用,放两个才算勉强。
这个打击太过猛烈也太过突然,我爸和狗叔,堂兄弟两个人,面对面,大眼瞪小眼,沮丧得直想狠抽自己嘴巴子。
“我什么人啊!”狗叔伤心动肺地呜咽着,“我怎么就让我爸病成这样啊!我怎么做儿子的啊!”
我爸一点儿都没有责怪他。农村人就是这样,要么不病,一病就是大病,因为他们特能忍,小伤小痛轻易不肯捧着钱往医院送。我爸安慰狗叔说,事到如此,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治就治个彻底吧,钱的事情他再去想办法。
这边我爸回家,还没为钱想到办法呢,那边医院就给他打了电话,说病人已经放弃治疗,自行出院了,让我爸去住院部结账。我爸掉头赶往医院,果然人去床空。同病房的老头儿说,二大爷听说了自己的情况,死活不肯再治了,说治也白治,白花儿孙的钱,他死了在阴间也不得安稳。
我爸爸心里悲伤,深一脚浅一脚,迷迷瞪瞪地回了家。到家也不说什么话,倒头往床上一睡,似乎睡眠能够为他疗伤。我妈试探说:“要么你回去一趟,再把他们爷儿俩接过来?”我爸不说行,也不说不行,闭着眼睛装没听见。
可是睡到半夜里,我爸突然从床上挺身而起,黑暗中声音无比清晰地说:“余宝他妈,我想到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爸絮絮叨叨说给我妈听:他小时候上学,家里穷,早饭就是一碗玉米糁儿粥,到学校撒泡尿就头晕眼花了。那时候二叔身强力壮,有手艺,挣得到零用钱,日子还算过得去,知道他上学挨着饿,就每天给他准备一个发面饼,他上学路过二叔家,拿了就走,一路香香地吃到学校。
“就这么大,”我爸用拇指和食指圈了一个茶杯口大小的圈,“又没油又没糖,铁锅里炕出来的,可我吃着真香,真顶饿。”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一年三百六十天,凡上学的日子,都能吃到二叔家的一个饼。吃好几年呢,算算有多少个?这账要放到今天算,利滚利的,我该还我二叔多少钱?”
他是在问我妈。我妈没答话。她心软,肯定被我爸款款说出来的这件事情惊着了。然后我妈就摸索着起身,去厨房给我爸做早饭,催他吃了赶快回老家,接人,治病。
我爸从乡下回来后告诉我们,开始二大爷打死不答应,他说他这身子就是块千孔百疮的破抹布,手指头一捅一个洞,再一捅还是个洞,补不起来了,也犯不上再补了。我爸劝他不动,拉着堂弟堂妹们齐刷刷在他面前跪一排,连哭带求,这才把他弄上车,直接拖进医院。
放支架的钱,自然还归我爸筹措。我爸从哪儿筹到手的呢?谜底同样不对我们揭开。
可我分明已经在爸爸身上看到了危险。我看到恐怖就像天花中的电火花,噼噼啪啪地响,红红绿绿地闪烁。我看到包裹在爸爸周围的巨大的阴影,它们时而像恐龙,时而像海浪,时而又像一大排悬挂的利剑,直通通地对着我爸刺过来。
我是鬼眼男孩,我的预感总是能应验。
可我不知道如何保护我爸爸。我能预知危险,却不能排除险情,这是我时常活在恐惧中的原因。
有一回我在家里的阳台上,看到一辆破旧的桑塔纳远远跟着我爸。我爸走,车就缓缓地走,我爸回头,车就不动,车里的人跟我爸直接对视。可惜距离有点远,我看不清坐在车中的到底是什么人。那车一直跟到我爸进了院子,上楼之后,才忽地掉头,加速开走。
是威胁我爸爸吗?还是在警告他什么?
我爸爸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偷偷问余朵:“姐,你知不知道咱爸借了好多钱?”
余朵先说:“不知道啊。”想想又说,“肯定的啦。”然后再问,“他管谁借了?”
“温董。”我告诉她。
她瞪着眼珠不相信:“怎么可能!温董是老板,咱爸是打工仔,打工仔哪敢向老板借钱?不怕炒鱿鱼?”
过了一会儿,她冷静下来,若有所思看着我的脸:“恐怕我得相信你,鬼眼男孩哎。”
我说:“姐,我害怕。”
她摸摸我的手:“真是的呢,手冰凉。”
我们面对面地沉默。
余朵到底是个心思活泼的人,闷了一小会儿后,她的眉眼又活泛起来,数落我:“你个蠢货,没见过你这么胆小的男孩儿,比兔子胆还小。借钱怕什么?是借啊,不是抢啊。”
“不好。”我说。
“滚蛋!你怕什么怕?”余朵骂我,“怕还不上啊?大不了我初中毕业打工挣钱去。再不行的话,你念完初中也去找份工。我再有一年就毕业了。你上完初中要几年?”她掐掐指头:“四年。四年很快的,眼皮子底下的事情。想想看,我们家里五个人都挣钱的话,那是什么光景?钞票哗哗地往家里流呢,数都数不赢,嗬!”
她笑眯眯地,脸颊上红扑扑的,简直就有点陶醉。
我只能轻轻叹一口气。
就是这样,没人能够理解我心里的忧患,永远都没有人。我看到的事情太多,知道的秘密也太多,这便注定了我的一辈子是孤独的。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个替温董朋友顶罪的倒霉透顶的司机,自首之后很快判下来了,有期徒刑三年。我爸说,如果他们当时就停车报案的话,也许都不用坐牢,缓刑就可以了。但是也难说,因为开车的胖子那晚明显是喝多了酒,如果现场报案,交警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很容易判断出来谁是驾车人,那样的话,醉酒驾车,惩罚会加重。
关键是,喝醉了酒还敢开保时捷的那个胖子,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温董为了保护他,把自己的司机都贴进去了,可见这人对温董至关重要。这是我爸小声说给我妈的话,被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爸一定要去探一回监。其实论起来,他跟那个倒霉的司机一点儿都不熟,虽说是一个公司的人,可一个开大货,一个开老板座驾,天上地下哪儿都挨不着哪儿。我爸执意要去,只能说,他在这件事情上良心有愧,要去求个安宁。
爸爸给那个司机带去了一千块钱,让他买烟抽。自己抽,也打点同监房的犯人们抽。爸爸说,这是监狱里的潜规则,新犯人都得打点老犯人,不然要挨欺负。
我很惊讶我爸有这么大的气魄,出手就能掏一千块。从前,我们管他多要十块钱都是难上加难的事。
这让我心里更害怕。改变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是好事,也许不是好事。改变就意味着你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熟悉的那一切统统都没有了,你沿着这条崭新的道路走,前面是天堂还是地狱呢?不好说。
总之,我们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而我用来想事的脑袋瓜子太小,我真恨我没有早一点儿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