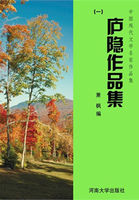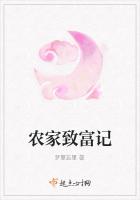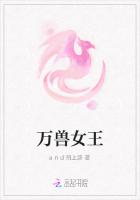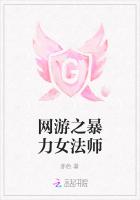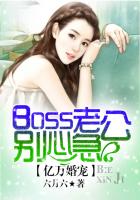二○○四年四月在北京召开的“身体写作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症候”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
日常生活里有尊严,身体里也有精神
文学是一种灵魂的叙事,但在论到“灵魂”之前,似乎有必要先辨析“身体”一词。作为一个哲学命题,灵魂和身体的二元对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但随着现代哲学的发展,这样的对立已被更复杂的思想分析所代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在灵魂和身体之间,除了简单的对立,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彼此纠结、互相转化的未明区域。灵魂和身体并不是分割的,身体也不是灵魂天生的敌人,相反,身体作为一个伦理命题,日益引起思想界、文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在前些年喧嚣一时的“身体写作”中,“身体”因为有效地反抗了一种玄学化、知识化和灵魂虚化的陈旧写作,进而成了这一阶段文学革命的主角。到二○○○年诗歌界出现“下半身写作”,“身体”作为“肉体乌托邦”的代名词,更是被推到了写作的极致——关于身体在文学写作中的诸多争论,都源于这种极致写作对现存文学秩序的“冒犯”。
然而,并不能因为“身体”一词在写作界被赋予了极端色彩,就可忽视它的革命价值。“身体”一词,近年有被妖魔化的趋向,好像一讲到身体,指的就是性,就是欲望,就是个人的宣泄。“身体”一词,近年有被妖魔化的趋向,好像一讲到身体,指的就是性,就是欲望,就是个人的宣泄。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身体和肉体是不同的。肉体主要指的是身体的生理性的一面,也是最低的、最基础的一面;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身体还有伦理、灵魂、精神和创造性的一面。身体的伦理性和身体的生理性应该是辨证的关系,只有这二者的统一才称得上是完整的身体,否则它就仅仅是个肉体——而肉体不能构成写作的基础。
身体的伦理性(或者说身体性的灵魂)是真确存在的,我甚至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物质化,而灵魂需要被身体实现出来;没有身体这个通道,灵魂就是抽象的,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只讲灵魂不讲身体的思想一旦支配了一个人的写作,这种写作就很容易走向玄学——玄学写作看起来高深莫测,其实里面空无一物。灵魂不该是抽象的,因为即便是最抽象的哲学和神学,也大都不否认身体存在的重要性。比如《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话很多人都熟悉,可一章十四节很多人就不一定注意了,这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人查过原文,发现“真理”和“实际”是同一个词。很多人读到“太初有道”,以为是神话,可没读到“道成了肉身”,“道”被实现了,“道”成了实际,成了可以在肉身里面实现的一种事物,它不再是那个抽象的“道”了。圣经如果只讲那个抽象的“道”,那个在天空中运行和人没有关系的“道”,那我们不读也罢,但它还讲了“道成肉身”的故事,这就在神性和人性之间建立起了一个通道,把神圣的“道”和人在地上的生活结合起来了,最抽象的和最具体的融合在了一起。写作难道不也是一种“道成肉身”的过程?不过它的“道”只是作家个人的思想,而圣经的“道”是神的“道”而已。“道”不同,但目的都是要在肉身里实现,要获得一个身体的现场。
现在很多人一讲到精神、灵魂、理想,以为就要反对身体,从而把身体和灵魂对立起来。其实,最有力量的灵魂、最有价值的精神都是从身体里生长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连耶稣都不例外。圣经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并非一直生活在天上,而是来到地上做拿撒勒人,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半,“道”在他身上被彰显于日常生活中,“道”有他的身体作载体,才能被人认识。他既是在传道,也是在活道,在他那里,道和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的道一点也不抽象,因为他的道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生活现场。他说人要爱父母,要爱人如己,不能恨人,不能杀人,等等,这些道,都以他自身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经验,耶稣的灵魂就会缺乏说服力。连耶稣尚且需要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一般的作家怎能越过身体直接飞翔?其实,不仅圣经注重“道”和肉身的关系,中国思想家在讲“道”之时,也同样注重“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现和彰显。朱熹在《集注》里说:
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
——“道”固然有超越“日用事物”的时候,但“道”也遍存于“日用事物”之中,正如王阳明的诗句所言:“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别诸生》)正因为强调思想、灵魂不能完全脱离日常,《老子》四章才有“和其光,同其尘”一说,《庄子·天下篇》才说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假如连道家哲学都对世间、日常不离不弃,文学又怎能离开身体、现世而写人记事?
就像日常生活里面也有尊严一样,身体里面也有精神。这是常识。许多时候,我们将写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当成庸常而没有尊严的代名词,这是误读。如果尊严不能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起来,那么,这种尊严就不是真正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应该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同样,精神如果无法通过日常生活、通过身体传达出来,这种精神的真实性就很可疑。精神如果无法通过日常生活、通过身体传达出来,这种精神的真实性就很可疑。因此,我反对用一种貌似高尚的精神来贬斥身体、践踏身体、把身体驱逐到一个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体写作,就是要把身体从黑暗的地方解救出来,让身体与精神具有同样的出场机会。
存在着一种虚假的身体写作
身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当然有物质性(生理性)的一面,但物质很可能是我们了解精神的必由通道。文学虽为精神事务,但并不等于说文学由此就可脱离身体这一物质外壳而独自存在——任何的精神、灵魂和思想,都必须有一个物质的外壳来展现它,没有这个通道,写作就会演变成为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或者变成语言的修辞术。强调身体在写作中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作家写作时个人的在场。“身体”是个人在场的标志之一。一个人的写作,如果没有对存在、对他所体验的生活的身体性参与,他的写作很可能是凌空蹈虚的,这和意识形态管制下的“假大空”写作并无不同。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真正伟大的写作都是身体写作,都是写作者的身体在场的写作。身体是不可复制的,而文化具有某种公共性。为文化而写作的作家,常常显得个性模糊;而面对自己的身体,忠诚于自己的身体感觉,并对身体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语言处理的作家,反而有可能成为好作家,因为他们有能力将身体语言化,使语言具有他身体的形状。比如,读李白的诗,可以感觉到李白这个人是豪放的、飘逸的,有一种神采飞扬的身体印象;读杜甫的诗,你会觉得这个人比较沉着、忧伤,身体前进的步伐感觉是缓慢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语言留给读者的印象,它是另一种真实。伟大的文学总能让人通过它的语言,看到作者的身体——读这样的作品,你会觉得是在和一个具体的人对话,而不是在和一种空泛的思想打交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阅读感受,当你喜欢读一个作家的文字,时间久了,你还会喜欢上这个人,你会去寻找这个人的照片,去读他的传记,了解他身体活动的历史,渴望知道他的爱情故事,甚至会想去他的故居看一看。会有这种愿望,就因为他的作品把他的身体带到了你的面前,你渴望了解这个人更多的方面,才会萌生看他的故居和遗物的想法。现在很多作家在写作上的失败,就在于他们不承认写作是有身体性的,或者,他们意识到了这种身体性,但没有面对自己身体的勇气,没有把身体在语言中实现出来的能力。他们意识到了这种身体性,但没有面对自己身体的勇气,没有把身体在语言中实现出来的能力。比如,一些明明是脆弱、无能的人,却经常在作品里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刚强、充满力量的人(相反,卡夫卡就真实地面对了自己的脆弱和无能,他承认,“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这种虚假性就会构成对写作的致命伤害。
写作的虚假性,许多时候正是源于写作者对身体的遮蔽。
身体从一方面说,是个人的身体——物质性的身体;从另一方面说,许多的人也构成了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肉身,如约翰·奥尼尔在《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一书中所说:
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
这话说得特别好,对我很有启发意义。这种肉身状态,正是写作需要用力的地方。今天,很多人的写作之所以显得苍白无力,就在于他的写作几乎不跟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发生关系,他的写作,总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或某个超验的思想结论里进行,凌空高蹈,停留于纯粹的幻想,看不到任何来自身体的消息。真正的写作必须面对身体,面对存在的每一个细节,面对这个社会的肉身状态,留下个人活动的痕迹,这是写作的基础性部分;如果在写作中看不到这一面,就会落入单一的大而空的务虚之中,像过去那种政治抒情诗一样。
其实,不仅写作事关身体,一切的社会事务都和身体有关,连政治也不例外——没有身体的政治,肯定是不会尊重人性、尊重生命的。没有身体的政治向往的是远方,为了远方的某个超验的理想,它可以不惜牺牲许多现实中的生命;强调政治的身体性,就是要避免政治只在空中飞翔,而无视千万哀痛的灵魂在大地上游荡。只有从身体出发的政治,才有可能是人性的政治。历史已经一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政治开始限制身体的自由,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思想专制和生命迫害,因为政治要飞向那个虚无的远方,它是决不允许身体束缚它的。身体是当下的朋友,远方的敌人。忽视当下性、只顾远方的政治和写作,对人类是一种灾难;人连藏身之处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幸福和理想?死魂灵的写作就是一直在空中飞翔,永远落不到大地上,不能魂归“我”这个身体,最多只是现有文化和思想的转述,这种写作显然是被别的思想作用了,接受的也是别的思想命令,哪怕这种思想很高尚,符合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于写作者的身体而言,也是死的,虚假的。一些作家在政治运动期间写了不少“假大空”的作品,为何现在不愿再谈及?因为事过境迁,他发现那些东西不能代表真实的“我”了——由此可见,当时那个真实的“我”是被有意遮蔽起来的。包括诗歌界一度极为推崇的海子,他在长诗和诗学随笔中,经常使用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神学的一些思想词汇,可他并未在自己的身体中找到和这些神学思想相契合的点。在“王在深秋”、“我的人民坐在水边”这些空泛的诗句中,你看不到海子那个柔弱的、多愁善感的身体,你感觉不到他的身体是如何存在于“王在深秋”这样的诗句里的。我不否认海子是有才华的,但他的写作没有足够尊重自己的身体,反而用一种高蹈的方式蔑视了身体的存在,并亲手结束了自己的身体——从他惨烈的自杀悲剧中,你可看出他是多么厌恶自己的身体,多么想脱离身体的束缚而独自在空中飞翔。他的诗歌,很少有身体的在场感,很少有那些和个人的身体密切相连的细节,看不到多少现世经验,你只能看到他张狂的灵魂在希腊上空、在神学殿堂里漫无边际地飞翔,这种灵魂最终因为失去了它最主要的基础——身体——而显得过于空洞。
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除了海子这种观念写作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虚假的身体写作——它使用的是公共的身体,这看起来是在书写身体,其实这样的身体已经没有多少个人的色彩,只不过是在转述一些身体的公论而已。比如,小说写作中的那些私生活,有多少不是照着现有的消费口味所设计?诗歌写作中的个人经验,又有多少出自诗人自身的深切体验?现在市场上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个人写作”,就是因为这些“个人写作”都有着鲜明的公共价值的烙印。真正的“个人”其实一直处于隐匿之中,很多的“个人”只是经验、表象的不同,支配这些“个人”的依然是某种思想的总体性,并无多少精神的个性可言。它的直接后果是缩减了文学的精神空间,也使写作变得日益表浅化。
要反抗这样一种公共写作,没有身体的揭竿而起是无法成功的。但是,身体在今天的写作中被简化、被过度使用后,也面临着再度被公共化的危险。身体在今天的写作中被简化、被过度使用后,也面临着再度被公共化的危险。如果说,上次的公共化是专断的思想,那么,这次的公共化则是性和欲望。它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不能说,一个人大量写到了性和欲望的场景,这个人就是在进行身体写作;身体一旦被公共化,即便作家写了再多身体性的细节,它也不再是身体写作,因为这样的写作用的不再是个人的身体,而是公共身体,它在骨子里其实还是观念写作,因为在他笔下的性和欲望,只是一种社会公论,一种与自己的个人经验无关的类型化表达。很多人甚至看到书写性和欲望的作品好卖,便按照这个社会的总体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写作,这是写作的复制,已经和那个真实的身体无关。
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
钱穆曾经指出,晚清的衰落,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照此说法,现在的写作困境,也在于写作成了纸上的写作——最有活力、最有个性的部分被遮蔽了,千人一面。千人一面的写作肯定是观念写作,而不会是身体写作。这样的观念写作,就是为了某个意识形态的总体要求,或者为了一种所谓的抽象精神,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写,集体戴上文化面具(如罗兰·巴特所说,现在的写作都戴上了文化的面具)——这面具要遮蔽的首先就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跳。这种文化面具既可能来自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书面的阅读经验;阅读中的文化面具,与意识形态的文化面具是一个意思。反抗这种写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回到身体,回到有体温的写作现场。
为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文学的语言革命之后,到二十世纪末,身体会成为另一次文学革命的主角。语言和身体,前者指向的是“怎么写”,后面指向的是“写什么”——比如“下半身写作”,不就是一次“写什么”的革命么?好像“怎么写”的可能性已经穷尽了,再次的革命,只能诉诸身体,造道德的反。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半身”的出现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作为一种诗歌的行为艺术,把诗歌从“怎么写”再次转回到“写什么”,这里面其实蕴含着新一代写作者很深的文学焦虑和精神焦虑。
但我也注意到了,当身体写作成为一种时髦,当肉体乌托邦被一度神圣化,“身体”很快就在当代文学中泛滥成灾。真正的身体遭遇到了被简化、被践踏的命运。简化的意思就是把身体等同于肉体、欲望和性,结果就把身体写作偷偷地转换成了肉体写作。这种对身体的迷信很容易走向肉体乌托邦。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写作者,普遍以为肉体就是一切,以为肉体可以决断一切,把身体的生理性强调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学身体学》(收入我的《先锋就是自由》一书,山东文艺出版社二○○四年版),里面说:
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当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一种我称之为身体暴力的写作美学悄悄地在新一代笔下建立了起来,它说出的其实是写作者在想象力上的贫乏——他牢牢地被身体中的欲望细节所控制,最终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他牢牢地被身体中的欲望细节所控制,最终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肉体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力,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肉体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权力,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
虽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这是特里·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但是,一旦肉体本身也成了一种权力时,它同样可怕。因此,我更愿意用一个新的说法来代替“身体写作”这一称谓——“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说“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强调的是两个要素,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语言。“身体”说的是作家作为一个存在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身体所感知、接触和遇见的每一件事,都跟他的写作有关,唯有如此,他的写作才是一种在场的写作;“语言史”的意思是说离开了身体的独特经验,语言的创造性就无从谈起;照样,离开了语言的创造性,身体的经验也不会获得有价值的出场空间。二者在写作中应该是同构在一起的。仅仅从经验层面上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太大的,比如吃饭、睡觉和性,等等,都差不多,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文学产生,就在于写作者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用创造性的语言来描述、发现和想象存在,并重新建构事实和经验的边界,使其焕发出新的光辉——遗憾的是,这样的创造性写作,在当代是越来越少了。
一百年前,尼采曾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声称:“要以身体为准绳。……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我相信当下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接受了这样的劝告——“以身体为准绳”,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写作者热衷于将身体改写成一种肉体的欲望叙事。美国的罗伯特·惠特曼在评价其剧作时就说:“我希望我的作品成为有关肉体经验的故事。”这种肉体经验的故事,欲望的故事,在中国作家笔下,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写作主题。消费这样的欲望故事,不仅成了这个时代的身体伦理,也成了这个时代的话语伦理。这种伦理的核心内容是欢乐。美国的萨利·贝恩斯在《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一书中说:
当身体变得欢乐时,由文雅举止的条规建构而成的身体会里外翻转——通过强调食物、消化、排泄和生殖上下翻转,通过强调低级层次(性和排泄)超越高级层次(头脑及其所暗示的一切)。而且,十分重要的是,这欢乐、奇异的身体向个人自足的现代后文艺复兴世界中的“新身体教规”挑战,新教规的身体是封闭、隐蔽、心理化及单个的身体。而这个欢乐、奇异的身体则是一个集体的和历史的整体。
萨利·贝恩斯显然忽视了身体在欢乐化的过程中所蕴含的危险因素,那就是身体沉溺在自我欲望中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这其实是对身体尊严的严重伤害。身体被政治所奴役和被消费所奴役,其结果是一样的,它都是使人从人本身的价值构想中坠落,最终走向它的反面。以前那个政治化的社会,在身体问题上,坚持的是道德身体优先的原则,抵制一切个人对身体的关怀,把身体变成了一个政治符号;现在这个消费社会,在身体的问题上,则坚持欲望身体优先的原则,放纵一些肉体的经验和要求,最终是把身体变成了一个商业符号。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这话一点没错。无论是政治奴役身体的时代,还是商品奴役身体的时代,它说出的都是人类灵魂的某种贫乏和无力。
重新建构身体维度的渴求,就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了。应该把身体当做一个整体来规划。它可以是开放的,但应该拒绝被外在事物所操控;它是自由的,但这自由不能被滥用;它是有情欲的,但它也超越情欲。最重要的是,它是独立的,但它也生活在一个广阔的身体世界里:自己有身体,别人也有身体;推而广之,政治是一个身体,社会也是一个身体。政治身体被滥用,会导致强权和压迫;社会身体被滥用,会导致灾难和动乱;个人的身体被滥用,势必也将失去身体的价值和光辉。只有将个人身体的独立性同构在别人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里,这个身体才有可能获得精神性的平衡。只有将个人身体的独立性同构在别人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里,这个身体才有可能获得精神性的平衡。换句话说,生理性的身体必须和语言性的身体、精神性的身体统一在一起,身体的伦理才会是健全的。——我相信,关于身体伦理的这一思索,对于文学叙事中的身体表达,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