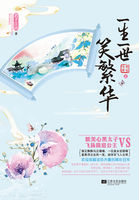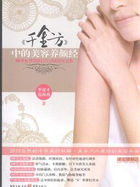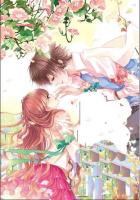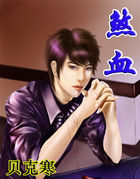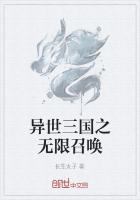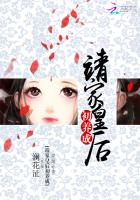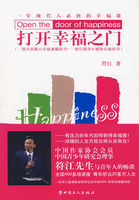剿灭群妖后,麻姑得以清闲,到东岳泰山拜谒碧霞元君,商榷道经。不期与奉师父王重阳之命,前来泰山探望道仙的丘处机相遇,同为昆嵛山道人在他山相会,倍感亲切,说话间二人游览至一泰山巨石前。麻姑拍拍巨石,说:“若能将这块泰山石搬到圣经山,必将壮我圣经山之威。”
“我道高足吕尚,号姜子牙在助周灭纣后,受上天之命分封有功诸神,没有给自己留神位,只做被周朝皇帝册封的齐王,玉皇大帝觉得有亏姜子牙,便在泰山颁诏: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并御笔亲题:‘泰山石敢当’,赐予姜太公,亲喻:此字刻于任何石头上,都能镇妖避邪。于是,连泰山之石也有了神威,仙姑想必早已见过天下建房者普遍在房山头上方垒一块刻有‘泰山石敢当’的石块,籍以镇宅,若将这块泰山石搬到昆嵛山,必振我道场之威。”年轻气盛的丘处机勒勒腰带,搪口便说:“仙姑先行一步,待小徒将这块泰山石搬回昆嵛山,放在圣经山上。”
麻姑吃惊地看了看丘处机,觉得这小道知道的还真不少呢,又觉得好笑:这小道竟敢夸下海口,太不自量了,便说:“那就有劳你了。我回圣经山等你。”说完,径直下山。心想:先行回圣经山,将此事告知他师父王重阳,就等着看笑话吧。
麻姑走后,丘处机挽了挽袖子,敦敦实实地站好骑马式,运足气,双手欲抱起泰山石,可是抱不过来,便双手抄着泰山石下部空隙,“嗨!”的一声吼,运起气来,然而,泰山石却纹丝不动,他那里知道泰山石非同一般,不是凭力气可以随意搬走的。丘处机站稳弓字步,用肩膀抵着泰山石费尽吃奶之力扛去,根本撼不动。他找来铁撬垫上支点用力撬动,可是泰山石就像扎了根一样,根本撬不动。他知道自己说大话,栽跟头了。麻姑肯定回到圣经山就把自己夸海口的事告知师父了,急得搓手跺脚,额头汗珠飞溅。拖着哭腔仰天嚷道:“我有何颜面再见师父?”
“小伙子,你在干什么呢?”企图晃动泰山石的丘处机扭头望见一位道士身背宝剑,手执长缨,笑眯眯地望着自己,他知道自己一脸的无奈,已经将自己的处境告诉了这位气宇不凡的道士,没有隐瞒的必要了,说:“大师,我与麻姑同游至此,麻姑说若能将此泰山石搬到圣经山,必壮圣经山之威,年轻毛嫩的我,一时心血来潮,忘记了师父再三告诫出家人不打诳语的教导,信口夸下我把它搬回圣经山,如今我撼它不动,更别说搬走了。”丘处机一脸的懊悔可怜相。
道士拍拍丘处机的肩膀,说:“你忘记了《太上老子道德经》所说:‘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年轻人,敢搬泰山之石壮圣经山之威,有志气。好啊!莫愁,贫道来帮你。”说着,将手中长缨一甩,泰山石竟晃了晃,变小了。丘处机看得真切,惊得口张目呆,连忙跪下仰问:“大师法力无边,小道有幸见识,敢问大师尊姓大名?”
道士捋着三髯美须说:“你我是同道人,吾乃吕洞宾是也。”
丘处机听罢,连忙“嗵!嗵!嗵!”叩了三个响头,五体投地地说:“啊!原来是吕祖,小道有眼不识泰山,还请仙师原谅。”
吕洞宾连忙上前扶起丘处机,说:“快快起来,你师父王重阳还在圣经山等你呢。你闭着眼睛,抱紧泰山石,快快回去吧。”
丘处机谢过吕洞宾,遵照吕洞宾的吩咐,紧紧抱住泰山石,吕洞宾将长缨一甩,大喝一声:“去也!”立即一道火线“嗖”地出现在空中,泰山石霍地向昆嵛山方向飞去。丘处机只觉得身轻如烟,两耳生风,飘飘然飞在空中。
麻姑正在与王重阳戏说丘处机泰山之行,突然,“轰通”一声巨响,让人感到地动山摇,二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块巨石已经从云端落在圣经山巅之上,在溅起的泥尘中迅速变大,丘处机屹然站立在巨石旁,麻姑与王重阳不约而同喊道:“飞来石也!”
丘处机满面欣喜地跑到王重阳和麻姑面前,跪拜之后,将巧遇吕洞宾,幸得仙祖相助的经过告知,王重阳朝着蓬莱方向作揖感谢吕洞宾的帮忙,对麻姑说:“小徒的仙缘不浅啊。没给为师丢人现眼。”
麻姑说:“你的高足,日后必有作为。”
三人望着巍巍屹立于圣经山巅的泰山石,相视开心地笑了。
自此,来圣经山的人无不对纹理有别于昆嵛山的泰山石叹为观止,纷纷猜测,演绎出多个版本的传奇故事。
圣经山前的西于村,有个于姓小伙子,父亲早逝,与瘫痪在炕的母亲相依为命地苦度一贫如洗的日子,家穷,穷得连个名字也没有,村人呼他于娃,他也就答应着。
于娃自小好学,常常在搂草、挖菜时,拼命干,挤出时间到麻姑观去听麻姑讲经说道,也许天生有缘,于娃悟性极高,对麻姑所讲的道经铭记在心,心领神会,小小年纪好道成癖,宁肯饿着肚子也要在人家做功德时去奉献一点香火,村人们戏称他“道痴”。
麻姑对于娃向道的挚诚,学道的勤奋,悟道的深切,极为赏识。常常特意给于娃以点拨,使他早日学成。
于娃到了论婚嫁娶的年龄,村人为他叹息不已:“可惜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家贫如洗,又被瘫痪在炕的老母亲拖累,没有一个媒人登门提亲。”
于娃却坦然置之,他说:“丘处机道长在潘溪穴居,吃饭向人乞讨,穿衣只披一件勒丝草蓑衣,人称‘蓑衣先生’,莫非还有个媳妇不成?”村人掩口而笑,越发叫他道痴了:“你一个穷乡僻野的凡人俗子,怎么能跟仙人相提并论?”
一天,于娃正在山坡砍柴,突然,一个身着道袍的人立在面前,气宇非凡,双目深邃地看着他,于娃一愣,崇尚道教的他马上施礼,道:”师傅在上,弟子在此有礼了。”
“我不曾收你为徒,还是免礼吧。”道士嬉笑着说:“听说你自比丘长春?”丘处机的号为长春子。
于娃听到道士直呼邱神仙的名讳,觉得此道士非同一般,便诚惶诚恐地跪下,说“我哪敢以贱比贵,不过以神仙作榜样,聊以自慰而已。”
“说的好,敢于相比,就是有志气。”道士说:“道家说宇宙间可分为九种人,最上为神人、大神人、真人、其次为仙人、大道人、圣人、最下为贤人、凡民、奴婢。不知你想做那种人?”
于娃不加思索,开口便说:“仙人不敢奢想,贤人不敢自封,不想当奴婢,做个凡民便知足矣。”
道士仰天而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万德基于孝。‘守其母,没身不殆。’仙人不过是主风雨,善变化而已;人人皆可成仙,成仙之路在于学道积德。”
“师傅莫不是邱神仙?”道士一番告诫。使于娃恍然大悟,对《太上老子道德经》释说得如此精辟,肯定是丘处机道长来到面前。
“丘处机是也。”道士说完,一甩长缨,飘然而去。
于娃得到丘处机点化,越发清心寡欲厉修苦行,笑对邻居的讥讽,无微不至地伺奉老母。多次受到麻姑夸赞,道行渐深。
一天,于娃在从麻姑观回来的路旁砍柴,突然,从路上走来一位苗条女子,长得凤眼柳眉,粉面桃腮,樱唇微启,娥娜多姿,走得飘飘然。于娃刚要回避,娇艳女子却带着一股迷人的香气细步飘到面前,微开红唇,露出两行整齐皎白的雪齿,对着于娃嫣然一笑,抛过来一瞥多情的秋波。
于娃紧皱眉头,转向一旁,对娇艳女子不肖一顾,向道已久的于娃清醒地意识到:在这荒山僻野,这妖艳女子从何而来?必是妖孽变化,企图坏我道性。于是收心敛性,正色道:“我乃向道之人,与女色无缘,请姑娘让开,莫误了我砍柴的功夫。”说着抡起斧子,一道寒光在娇艳女子面前一闪,“喀嚓”一声,一截枯树杈随着寒光落地,娇艳女子一愣,说:“你这位小哥,年纪轻轻向道入迷,清苦终生,岂不愚昧?”
“向道之人,以苦为乐,以诚为真,以德为本,洞明寰宇,大彻大悟,何谈愚昧?”于娃冷冷一笑说道。
娇艳女子听得于娃一番妙语真言,大为震惊。原来它是躲在悬崖石窟窿里修炼千年的蝙蝠精,见于娃一心向道,大器将成,深怕阻了它的魔路,便以美色迷惑,动摇其心志,以误其途,没料想到于娃夙愿根深蒂固,不为所动,且已悟出真道,道魔不能同世两立,将来必是它的心头之患,恼羞成怒,刚要发作,望见麻姑踏步而来,便在“喀嚓!喀嚓!”的砍柴声中,旋即隐身离去。
麻姑见于娃执着砍柴,目不旁贷,没有近前打扰,含笑返回。
丘处机闻知于娃受其点化后,更添道缘,理辩蝙蝠精,不受其惑,甚喜,又在梦中应缘授他《东华真经》一部,让他日夜诵读,促其早日修成正果。
于娃的道缘愈深,蝙蝠精愈是惊恐。
在雷鸣电闪,风雨交加的夏夜,于娃正在家中修炼,隐约听到呼唤声,循声望去,只见雨雾中的圣经山七彩之光闪烁。于娃一下子被吸引了,看着看着便有飘飘腾空之感,迷迷朦朦飞将起来。他刚要乘风而去,突然,从云中闪现出娇艳女子,得意地娇声怪气嚷道:“还是飘飘欲仙好吧?免受病母拖累。”
蝙蝠精本是沾沾自喜地挖苦于娃,不想倒唤起于娃悟觉,他身子一沉,着脚在地,急忙跑回草屋背起母亲向圣经山奔去。
蝙蝠精一看于娃不肯舍弃病母,这将使他修道告成,便施展魔法,将一块巨石滚下山,直冲于娃滚去。奔跑在山坡的于娃见巨石滚来,躲避不及,急忙将老母掩在身下保护起来。
恰在此时,空中一声炸雷,将滚动的巨石劈为两瓣,一瓣依山屹立,成为无字碑,一瓣平卧路边,犹如平展宽敞的石榻。
突如其来的炸雷将蝙蝠精惊楞了,它看到麻姑怒气冲冲而来,知道不妙,麻姑的毙妖簪确实令妖怪们胆寒,叹道:“昆嵛山虽然有悬崖峭壁,窟窿洞穴,却没有我辈的栖身之地,人们视我与近亲老鼠同类,见了便喊‘打!’哀哉!”仓忙化作一缕青烟,逃之夭夭。
麻姑来到石榻前,见于娃母子被雷声震昏,轻甩手中长缨,将二人托上石榻,片刻之间,母子便苏醒过来,于娃扶母亲从石榻上下来,母亲瘫痪的躯体竟然行动自如,于娃也觉得浑身轻松,二人望着石榻惊叹不已。
原来,于娃道缘所致,蝙蝠精对他的险恶用心,尽在麻姑视线之内,麻姑见蝙蝠精要用血光之灾陷于娃于不孝,阻于娃道缘,使其前功尽弃。便用铁拐李传授的掌手雷将巨石劈为两半,使其不能滚动,母子二人幸免灾难。
于娃和母亲望着石榻前含笑面对的麻姑,不知道说什么好,跪下便拜。麻姑将二人扶起,说“是你们的善行得到善报,我只是替天行道。”
母子二人深深感激麻姑的救命之恩,从此,母子昄依道家,因得道成仙的于娃曾卧于石榻,人们便把石榻称为“卧仙石”。
有人问于娃的母亲瘫痪多年竟瘉的原因,她欣喜地告诉乡亲:“自从在卧仙石上躺过,下来后,病就好了。”
乡亲中有病的纷纷到卧仙石去将病体躺在卧仙石上,还挺灵的,但也有人躺过几次,仍身病如故,无奈,去问麻姑,麻姑说:“病在自身,恶为病根,善有善待,恶有恶待,恶行不改,身病不瘉。”
那些恶病缠身,不堪其苦的人思想自己的曾经,惭愧之至,痛改前非,再去卧仙石,一躺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