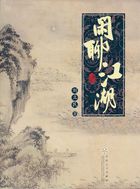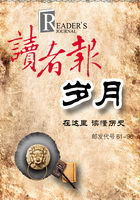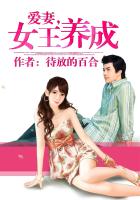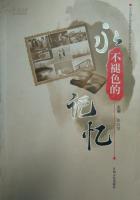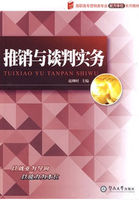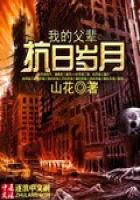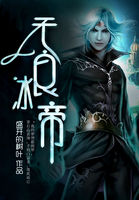老家邻里有个远房三舅娘,她的一生就是一个‘苦’字。小时候听父母讲,三舅娘娘家在清末民初中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有钱棺木商人家,她是家八姊妹中最小的一个独身女。由于天生丽质聪颖,从小就很受父母哥嫂的疼爱。八岁那年,父亲把她送到了县城一个有名的私塾读书,一直念完当时的初中课程,此后她便萌发了完成高等学业,将来当一名教书先生的理想。父亲也本想将她送到50华里外的成都省城里继续完成她的学业,但在母亲和长辈们的反对下,父亲放弃了。因在那个年代她已属于谈婚姻嫁的年龄。17岁那年,无论她以绝食抗争,还是苦苦哀求,母亲都无动于衷,最终这个满怀梦想、才貌出众、亭亭玉立年轻的女子,经父母作主,嫁进了我们侧面大院,拥有百亩产业,一个远亲大户人家的三舅为妻。
三舅娘中高个,在那个时期,她应算左右乡邻中,有着较高文化的女知识分子了。她不仅仅漂亮善言会道、抄写算帐,还绣得一手栩栩如生的花鸟、草木、人物细绢图。尤其她编织的;已经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川西棕编’鞋、帽等各种小工艺品,更是小巧玲珑,微妙微俏,很受商家和邻里的喜爱,并以高于她人的价格卖出。可就是那个门当户对封建的包办婚姻,从此让她走上了迷茫、痛苦的不归之路。
远亲三舅家境富裕,加上父母从小对他管教不严,少年时候就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轮到该上学年龄,父母多次送他读书,他多次逃学,直至周边老师不接受他为止。这个三舅其性格孤僻横暴,在姊妹和乡邻面前,常常耍横称霸。随着53年土地改革工私合营,三舅娘娘家和她丈夫家,大部分产业归新中国人民政府所有,加上耕种经营不善,双方家庭相继败落。原来靠出租百亩农田,过着安闲富裕生活三舅他们这个大家庭,便解体分家,各立门户。在倡导勤俭节约,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时期,对这个长期养成好吃懒做的三舅来说,根本无法适应。不管是春播种、夏栽插、秋收割,只要三舅娘叫他下地里干活,他略不顺心,不是朝三舅娘哦破口大骂,就是拳脚相加,当我记事后,常常目睹这样的事情发生。为躲避丈夫的暴力,三舅娘还不时地带着小孩跑到我父母面前求助,相关部门也多次出面调解,但是效果甚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包括所有的家务活一并落在三舅娘身上。她慢慢变得憔悴疲惫,甚至木讷起来。以前那笔直的身躯,被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压力,变成了与她现实年龄极不相符的驼背老人。
三舅娘膝下有两女两儿。大儿子在58年出麻疹时,因无钱治疗夭折。大女儿智力偏低,未曾上过学。在人民公社和3年自然灾害粮食特别紧张、靠争工分养活一家人时期,由于这个家庭成份不好,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救济,全家人一天以两餐汤米粥维持生计。记得在文革初期的一天凌晨,三舅娘带着10岁的大女儿出早工时,把小女儿叫醒做早饭,当她和大女儿收工回家,看到小女儿坐在炉灶旁,抱住弟弟偷偷地哭泣时询问,才知道小女儿刚做好的饭,就被父亲吃个精光。小女儿上前拉住父亲的衣角说:“爸爸给妈妈和我们留一点吧”那知道这个已不成人性的父亲,却把小女儿推倒在地。三舅娘听说后,就去房间里找到又上床睡觉的丈夫理论,谁知道惹恼他,便起床对她拳打脚踢,我父母闻讯后跑过去才得以劝息,之后我母亲把他们四口人叫到我家吃了早饭。
在村邻有‘三爷’之称;由于很少下地干活,养得又白又胖的这个三舅,又歪又恶故,村子里的人都叫他‘三爷’。他的无聊和粗暴多次逼迫三舅娘带着三个孩子一起跳河自尽被邻里搭救。无奈之下,她只有盼着儿女们快快长大,她唯一的念头就是把后半生寄托在这小儿子身上。三舅在一次与村邻争执时,因突发脑溢血去世。随着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两个女儿逐渐长大成人,相继出嫁,家庭生活慢慢得到改善。三舅娘对小儿子管教甚严,所以儿子少言勤快。农闲就到城里打工,对母亲还孝敬。不久经人介绍,取了一个远乡女子为妻。儿媳到是一个勤快治家人,这样儿子基本常年在外打工,婆媳在家耕种养植,一个三口之家过着较为舒心的日子。
两年后,家里添了一个小孙子,婆婆视为掌上明珠。随着年龄的变老和多年劳累,她已积劳成疾,对农田和家里的体力活已经力不从心。那平常对婆婆还算过得去的儿媳,突然变得可恶多端。有病不带婆婆去医院,娘家来客人不许婆婆上桌吃饭,凡是吃鸡鸭鱼肉前,就迫使婆婆到女儿家去。家里做饭、喂猪、洗衣裤一律由婆婆一个人承担。孙子满意5岁那年,硬要逼迫分家,让婆婆一个人过日子。儿子看到母亲年已70有余,又多病,坚持不分。儿媳就以离婚要挟,一个没有骨气和没有良知的儿子和媳妇就这样,把这个可怜的老人分住在,紧挨在着他们宽敞,有四间两层楼房下的竹林栓狗、养猪旁的一间潮湿、睡觉、做饭、拉撒为一体的茅草屋里,邻里看到都心酸呀。
因年老多病体弱,在一个秋雨绵绵的早晨,她起床做饭,由于地面潮湿不慎滑倒,将其左脚腿部摔断倒在地上。由于儿子在外地打工,她痛苦地连续呼唤儿媳和孙子数次,恳请儿媳妇和孙子把她扶起送到医院去治疗。可那个可恶的儿媳妇就是不以理睬,在邻居们闻讯赶来时指责儿媳时,儿媳才叫孙子把婆婆用三轮车送到医院。未等婆婆痊愈,怕花费过多的医疗费用,就叫婆婆出医,从此三舅娘就只有靠着两根木杖,艰苦地过着她一个人寂寞痛苦的生活。村委会看到该情况,经过数次做工作,在迫于邻里乡亲的强烈压力之下,儿媳才勉强将婆婆接到一起吃住。没过两年,眼看孙子到成家的年龄,儿媳怕这个残废多病婆婆妨碍儿子婚姻大事,趁丈夫外出打工不在家,又将婆婆送到那间茅草屋中。一年四季,风去雨来,酷暑寒冬,她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各种痛苦,生活不到两年,这个向来和痛苦抗衡数十年,苦难迭起的苦命三舅娘,在儿子不在家的一天,不明不白地悬梁自尽了……
茅草屋没了,低沉痛苦的呻呤声没了。浮现在眼前只是一个蹒跚,撑着拐杖的老媪在雨中,孤独地徘徊在竹林茅草屋旁的朦胧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