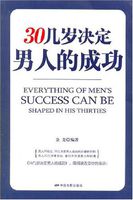人到临死反省一生的时候,常常会感到这样一种缺憾,正像一个苦于口喝的人走到泉水边上,却发现一条狗,一只羊或一头猪已把水弄脏了的时候所感到的那样——无奈、放弃。
地下共三层。靠地面的上边一层,里面像博物馆一样摆放着各种陈列物,什么远年间的“分家单、卖地契……”发黄了的纸张,上面写着一些奇哩古怪的名字;什么缠足女人用的木底模儿、男人穿的毡疙瘩;什么四耳棉帽头、揑脸儿牛皮勒死靰鞡;什么……嗨!虽说P先生活了八十多岁,这里陈列的许许多多物件都是他未曾见过的。往下第二层里面陈列的全是古画。虽说他对这门艺术一窍不通,但对现代画与古代画还是分得出来的。他站立在一排画幅前,画幅下面写着唐寅作。当他由记忆中正在去寻找这个名字时,耳边突然传来从前那个自我的催促声,“看这个干嘛?都是些无名之作。没意思!没意思!”紧接他就回应了句说,“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唐伯虎的真迹?”他说这话时并未有觉得出来——有多像他曾经熟悉的老G的声音啊!声如其人,有股自以为师的清高意味儿。然而他像闻声(竟管这声音出自他自己口中)便尊从的朝四下里慢步走去……可是在整个二层寻找个遍,也没见到一幅画是写着唐伯虎所作。噢?他像很沮丧的跟从前那个自我叨咕,“竟是一些无名之辈……真个没意思!没意思!”尔后回了一下头,像在寻求响应,然而身后空空,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便出了二层房间,又走上阶梯朝下层步去……
当到了下面第三层,刚一迈出阶梯口,就觉得里面阴森森的叫人毛骨悚然,他有点害怕了。当他慌慌然回转过身去,正欲踏向朝上去的阶梯时,由三层房间里面送出来“嘿嘿……”一阵怪笑声。
是田三浪!他在这儿?如果说这下面的一层就是地狱,凭着他生前处处占便宜之本事,死后绝不会做这种选择的。现在田三浪能发出来嘲弄他的这种怪笑声,想必一定是他觉得很得意的一处所在。P先生没再犹豫地回过身走了进去——这是这座地下建筑最底层——由上往下属第三层。里面阴森森的,有些黑暗。像一间极其简陋办公室,中间并列摆着两张掉角破桌和断腿缺梁的两把破凳,碎纸片满地,角落里堆着一摊垃圾……啊!这里的一切,P先生都觉得十分眼熟。就像十年****时期政府机关砸滥后的红卫兵总部,或某个新成立的战斗队临时使用的场所,仰或就是无聊闲扯一类的地方吧?不!在人们心里积淀下的——阴间就是阳间的映象,这里正是什么时候P先生曾同田三浪、老G等人在一起时的那间办公室。日月循环,人生伦回,现在P先生重新又回到这里来,不免心中泛滥了。只觉波涛涌动,一股股……他不知那是往昔之寒酸?还是温故之暖?
如果说这里也有主人的话,可就是田三浪了,至少他本人是这么认为的。在这里他可为所欲为——无论什么人在场他都不掩饰那张丑陋嘴巴,多么难出口的污言秽语都能随意由里面淌出来。正因为如此,才赢得上边赞誉:他是最深入实际之人。譬如说起教育科长跟女教员那档子事儿,他对每个细节、每个微小动作都能讲得惟妙惟肖,就像人家两人做那种事而他站一旁侍候来着似的。
他往往在说这类事时,还很为得意。好像真的侍候过人家那种事,事发后做事者受到了处分,而他这位一旁侍候的人非但未受任何株连,还大饱了一场眼福……这可真是个大便宜!据他本人讲,他跟那个乡下闺女确立婚姻关系时,那闺女看中他的就是这一点——不吃亏!
然而小C坐进了这间极简陋办公室的时候,他却感到了浑身的不自在,甚至还有些酸溜溜的醋意。小C是一个很柔弱的娇小女人,或许他是妒忌小C也能走进这样高雅地方;或许他认为小C根本就不配跟他坐同一个办公室;或许他是……然而小C的到来,让他发挥出了最大潜能,充分展示出他的聪明才智。
其实,同坐一个办公室也是各有各的作用,谁也代替不了谁的。譬如他在讲述教育科长怎样舔那女教员羞处的时候,小C坐在断腿凳上就是一个很忠实的听众。有说者就必有听者,这是分工上的不同。如果没有小C这个娇小女人在场,他在讲这类龌龊事儿时就显得平平淡淡,正像他自己说的,“光是些老爷们儿能听出个啥意思来?”而有小C在场,不仅使他讲的有滋有味儿,似乎也给人间频添了几分斑烂的色彩。
P先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小C告诉他的。她说,“田三浪老师尽说些低级下流话儿,叫人家坐在一边听着都不好意思了!”她把田三浪那天说教育科长的事告诉给P先生后,接着就问,“你说那教育科长他……他咋还舔呢?”她的问题把P先生给弄的左、右都不能……无法作答。后来又有一次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小C问P先生“什么是?”P先生满脸通红,什么都没说。然而无声胜有声,小C心里明白了,两个问题似乎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当然她还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个新的问题等待他回答——就像这样,无声的……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
P先生对这个柔弱、娇小的女人,感到单纯的像个孩子般可爱。心想,都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性的知识怎这么差?于是他买了本书送给她,她感激涕零,有了这本书,便可顶半个田三浪,等他再讲某某人那类事儿时,她就可以叫他住嘴,说他讲的那些不附合科学,有书本为证……可是她却没那么做。书本上的是理论,田三浪讲的是实践,书本上写的与田三浪讲的不一样时她就单独去问P先生。这样,她每一次从P先生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种满意回答;而是精神上一种不可或缺的补益。一天,另一位女孩见办公室没有旁人就偷着告诉P先生,“有人说你跟小C不清楚呢!”P先生既没震惊,也没恐慌,他不仅对这话不怎么在意,并反映出他好像很乐于接受的样子。当时他没言语什么,只是勉强的笑了一下。
那女孩儿似乎看出来,这种谣传他像早都听说过了似的。于是就又体贴的告诉说:“这话是田三浪说的。他说小C跟着你……”如果这时P先生去找田三浪打架,那女孩儿一定会站在P先生一边,仗义执言。他却没有。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什么话都没有听说过似的……不过他很感动不已,就像一双纤秀的手指抚弄起他心中的琴弦——不禁奏出美妙、浑圆的音韵。这音韵一直都萦绕耳边……他仿佛有种幸福感,暖融融的。
自此,他无论立着、坐着,仰或走在路上……都在想着那女孩告诉给他的话。“有人说你跟小C不清楚呢!是田三浪说的,他说小C跟着你……”哈!他的心里面尤如大海的波涛,然而却不是由风暴所起;是自身的热力才使心潮涌动,上、下翻卷的。晚上他坐在书房里,没开灯,一个人默默地品尝那言传为他所带来的那种欣喜。这是怎样的一种欣喜啊?说不清楚,只是人生百味中一种奇妙感受才让他如此激动,如此心跳,如此血液沸腾,如此的……啊!他方才发现——他已经爱上她了。
P先生这时看到田三浪和小C就在这座地下建筑的最底层里,他们相对坐在紧挨一起的两张掉角桌子的各一边。小C好像在解释着什么,田三浪屁股下面一把断腿凳子,左歪右扭,稳坐自如。一会儿他两手托着后脑勺,身向后仰,眼望天棚,就像小C的话是透过上边地面的缝隙——一点点淌进底层里面来的;一会儿他又身子前倾,伏到桌面上,用笔在一张废纸上划拉起什么来……只听屁股下断腿凳子“咔咔!”直响。而小C就不这么自如了。为避免坐的断腿凳子冷丁倒下去,或为了能坐的牢靠一点,她总是那么小心异异的。她把两只胳膊伏在桌面上,两手摆弄一根秃头铅笔,翻过来掉过去……这种无意识动作好像在掩饰她内心里的什么,是掩饰她有意识说出的每句话吗?她的小脸蛋儿红朴朴的……
P先生每次跟她拥抱时,好像都有种罪恶感,可是当她每次扑向P先生怀里时,都会娇柔不已,感叹连连,“唉!都多长时间没在一起了……”每次拥抱她都搂的那么紧,亲吻时都那么投入,那么狂热、忘形;那么的……噢?她跟田三浪像是在说P先生什么。是说什么呢?P先生看到的,是她的每句话里好象都裹挟着一股灰色气流。话儿一出口就立即爆开了,——灰色飘向P先生眼前;而她自己则罩进了一层纯净透明的气体里。P先生的目光冷丁惊矍地一闪,凝滞住了。“怎么?他话里的意思是……说我死皮赖脸的缠着她!”P先生不禁冲向桌前。田三浪离去了,刚才他坐的桌面上丢下来他划拉过的那张废纸。P先生拾起来,拿到手上看了看,上面随意写下刚才小C说过的那句话——“人家烦侮他,他还不知道呢?”
啊!P先生受了伤似的——心里一阵剧烈疼痛。他这才感到,小C并不像他想象那么单纯、柔弱、可怜,她是这般无情、狠毒啊!“从此一刀两断!”他痛下决心,不由一双脑怒的目光朝小C射去!然而小C刚才坐的断腿凳上是空的,桌面摆放着两个头盖骨。他又朝四周看了看,四周壁架上完全是白花花的人的骨骼。有完整的,有零散的;有的头、身两离,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已成为化石……啊!原来这是一层地下墓穴。怎这么多尸骨?或许这是什么时候的一种群葬?对!正是群葬。活着为同事;死后做鬼邻……这倒也不失为一件温暖人心的事情。这不?在一个角落的壁架,他见一具尸骨有点像老区;在相邻的个壁架上,他见塌陷了的头盖骨后,便一眼就确认下来这是他那位做领导的朋友BU;紧挨着的另一个壁架上,尸骨已经脱落了,不过在剩下的零乱核骨中,他发现一块三寸多长的尾骨,不由让他泛起了幽思……“怎么?是她……她也葬在这儿?”P先生知道,除了早年机关里那位老姑娘外,别人身上是不会多出这样一块骨头的。那时机关里人都叫她猪尾巴根儿,据说她由娘肚子里刚一坐胎就坐到了尾巴上。《百年孤独》(1)中说:这是近亲成婚的产物。不知道她的父母是不是近亲成婚?总之,她一出生就注定成为众人眼里的异类。她由小到大,无论走到哪儿,人们第一眼目光所关注的不是她那张脸蛋儿,而是屁股。人们好像都知道:藏在裤裆里的屁股后长的个猪尾巴。尽管隔着裤裆谁都没有看到,但谁都觉得恶心。于是她就成了男人嫌弃;女人厌恶,人见人躲的一个怪物。活着时,她有情无处投放;有爱不敢表白,她只好孤守老姑娘真操,终老一生……死后,她这才追随起生前之所爱,来到BU领导身边。BU领导生前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她是他亲自到人才市场挑选来的。如果说BU领导生前没有跟她亲热过,显然不是因为她长了个猪尾巴;而是由于他天生的正人君子,既使他把头伸到她胯下想亲吻一下猪尾巴根儿,也会一本正经地怪她说:“噢?你怎么把裤裆贴到了我嘴上!”自此她就把尾巴紧紧夹起来了。但她明白了他的用意,活着他要面子,死后再去追他!听说那边他刚咽气不久,这边她已经人事不省了。于是她就追他,追呀追……直至她追得粉身碎骨,葬到了他身边。这时,他们两人大概如愿以偿了吧?生前愿望,死后达成,一个美丽的梦。然而下一个壁架上的尸骨残核,却让P先生有些寒心。
这是两具尸骨交叉在一起被塞进壁架里的。就像罪孽深重的两个囚徒圈在同一个牢笼里。其中一个没了脑袋,只剩个秃溜溜脖子连着白骨架在壁架里弯成个弓型。弓背往下耷拉起半拉胯骨,就在胯骨耷拉的裂痕上,P先生确认出这具无头尸骨是田三浪的。因为P先生清楚,那胯骨是他上小姨子炕时,让姨妹夫给踢裂的。要不是他们共同的朋友老区和老G出面作证——说是场误会,这胯骨早就被踢掉了。末了只踢出一道裂缝儿,好在没有断开,并无大碍。现在看来,是胯骨上那道缝隙迸裂开了。可是为何会耷拉着,没有掉下来呢?噢,原来在两胯之间有个脑袋,那半拉胯骨,是让连在脑袋上的胫骨支着的。P先生看了看,发现那脑袋一边的腮骨上有一条指印……啊!怎么?是老郭。P先生心里明白:这是个有啥说啥从来都不掩饰自己什么的直性子。可是不知是什么人背后造谣中伤说他是“掏耙!”P先生听了后,就像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一样,简直就天掉下的屎盆子落在老郭的头上。他本打算找老G说说心中愤懑,可是发现老G不仅兴灾乐祸,并且跟人一块起哄……这样,本来是件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却更增加了许多真实的成分。因为大家都知道,老G跟老郭是无话不说、无事不晓的多年朋友。
“老郭的这事是真的了,连老G都这么说呢!”
“老G说了,是有那回事。”
……
最后就老郭自己也怀疑起自己来,“呃,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有一天,他实在无法忍受外面那些污言秽语、鄙视目光时,不知怎么便有意无意的向儿媳表示起他的忏悔……结果让儿媳给挠了个满脸大开花。由于儿媳下手狠了些,便在腮骨上留下来现在看到的指印。
唉!老郭啊,老郭……活着时你是老G手上的一件器皿,盛过他所用之美味后,又被他用来拉屎拉尿;死后你又甘愿胯下之辱,用你的胫骨支撑起人家的屁股,才使那断裂的半拉胯骨没有掉下来。世界上,也不知有多少忠诚、老实厚道者玩弄在小人鼓掌之中,然而他们却是朋友。P先生不觉心里蒙上一层阴云,他不忍再看下去了,于是他急忙回身跑向了阶梯口。当他慌慌然沿着阶梯爬出地面时,早有一位美丽女子等在了进、出口那儿。她身穿黑色旗袍,头挂白绫。身材颀长,而又柔弱、娇小;像似“新寡”而又不是“新寡”,一张红朴朴脸蛋儿上,透着温顺、贤良而忧郁的美。噢?小C!她是小C?顿时他忘记了小C给他的伤害,忘记了心里伤口的疼痛,忘记了……他敞开胸怀,朝那美丽女子扑去。不料他扑了个空,差点儿掉下床去。
醒来后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思想里丢失的不是小C。怎么会是她呢?她即然给他那么大伤害。那么刚才的这位美丽女子是谁呢?他不由“吧嗒!吧嗒!”嘴,像是要品味出刚才梦境里一种什么情趣儿。
注:(1)哥伦比恶作家马尔克斯所作长篇小说《百年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