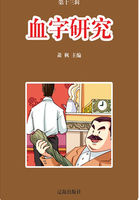十六年前,苏叔良来过这个地方,江西的一个古镇,那时正是春水缭绕,杨柳依依,十六年后,再次重游故地,前尘往事恍如一梦,苏叔良苦笑,自己的半生又何尝不是大梦一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古人说,洲,是水中的陆地,所以我给我们的女儿起名叫做伊洲。伊洲,伊洲,夏草,你可知这么些年,我带着咱们的女儿是怎么过的吗?她和你的眉眼是如此的相像,一颦一笑,都是你的影子,我不忍看,伊洲在我的忽视和冷淡中竟已长这么大了。
这许多年,我一直生活在你的阴影里,渴望有一天一睁开眼能回到那天,如果真的能回到那天,我一定不会放你走。夏草,你可知道我想你?我像个正常人一样结婚,赚钱,养家,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早已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我为谁而生,又为谁而死,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火车在“隆隆”的行进中,穿越千山万水,一路驶进这座江西古镇。多少年,这座古城如一位阅尽人间风雨的老人,见证岁月变迁,如今还是当年模样,只是当年的人事已不再。苏叔良从火车上下来,沿着记忆中的街道一路走来 ,走到当年分别的地方,这座浮桥还像从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静静地卧伏在清澈宁静的水面上,桥边蜿蜒而下的台阶上,有妇女在洗床单,说笑着。
苏叔良找到约定好的地方。那是停靠在岸边的一条小小渔船,踏上船,船家热情地沏上茶,便忙自己的事情去。不一会,船身一晃,有轻微的交谈声传来,苏叔良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他艰难地抬起眼睛,看着眼前人。
夏草,是你吗?
十六年了,苏叔良第一次流下眼泪。她还是从前的样子,光阴似乎已将她遗忘,就连那双眼睛里单纯的忧伤都未曾改变。夏草,你是我的夏草吗?
“你,好吗?”俩人几乎同时问出这句俗不可耐的话,随即又都苦笑,好与不好又能怎样?
“叔良,我不该叫你来的。”夏草踟蹰再三,“我已经辜负了你,却最终还是辜负了他。”夏草抬头浅笑,小鹿一样的杏核眼里沉静如水,眼神还似当年,只是多了些许苍凉。“夏草,不要这样说,我,只要你好过。”苏叔良攥着手里的茶杯,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缓,心却在被刀子一下一下地切割。
“其实,在你抱走孩子后的三四年,我已经记起了从前。”夏草缓慢地说完,苏叔良却无异在心里炸响一个旱天雷。他惊讶地猛然抬头,疑心自己听错:“夏草,你刚才说什么?”夏草的手指绞着长发的发梢,似乎下了很大决心才抬起头,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叔良,在你走后的三四年,我记起来了。”苏叔良起身抓住她的手几乎是绝望地喊:“你说什么?你记起来了?你现在知道我是谁吗?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找我?为什么不告诉我……”
夏草瘦弱的身体在他身前无助地摇晃:“叔良,不要孩子气,那时,你已有家。”“可我心里却只有你”,苏叔良把脸埋在夏草的掌心,声音哀切,“我每一天都在祈求奇迹出现,我每天祈祷让你回忆起来,哪怕只有一点点关于我的记忆。我不信你就这么把我忘了。这十六年,我每一晚都在做着想你的梦,夏草,你知道吗,我是多么爱你……”
夏草咬着嘴唇,把脸贴在他的头发上,这是她曾经的爱人苏叔良啊,他们曾经是多么相爱。“叔良,不要这样,我只是希望我们三个人都好过。我……是不是很自私?”“夏草,你知道的,我只要你……”夏草轻轻推开他,坐回对面的座位,抿一口茶,这茶可真苦,若与此时的心情相比不知又如何。
“叔良,安然瞒着我联系你,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我的时间不多了。”“不,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我要带你去最好的医院,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再次离开我的!”苏叔良绝望地泪流满面,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奇迹。夏草摇摇头,浅笑:“看,你又孩子气了。我最多只有一个月时间了,我希望你好好陪陪我,我可不想把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医院里。”“好,好,我答应你,你说什么我都答应……”苏叔良感觉在那一天就已经流完了此生所有的眼泪。
一个多月后,夏草从苏叔良和谢安然的生命中永远消失了,同曾经那段最浪漫的错误永远地道声再见。苏叔良按照夏草的交代将她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在火车站,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苏叔良木然回头,周梓晴牵过他的手,温柔笑道:“回家吧。”
这已是离开家的第四十八天,苏叔良和周梓晴回到家,苏伊州惊讶得不敢相认,一个多月,苏叔良满脸胡茬,竟然长了那么多白头发,他一下子苍老了这么多!
苏叔良指着怀里的骨灰坛,轻轻吩咐:“给你妈妈跪下。”“我妈妈?她……死了?”巨大的震惊让苏伊州瞬间丧失了思维能力,徒然跪在地上,不知如何去想,也不知如何去问。十六年来谁都不能提的妈妈突然出现在眼前,竟然是她的骨灰,苏伊州不久前才从徐若之那里知道了从前父母之间的那段纠缠,现在这样一个突兀的现实摆着眼前,她根本还没有能力消化。
苏叔良掏出一对黄澄澄的金镯子递给苏伊州:“这是你妈妈的嫁妆,是她们家女孩出嫁代代相传的陪嫁,你妈妈让我交给你。”苏伊州接过这两只纤巧古朴的金镯子,套在手腕上仔细打量。镯子上面用简单的线条錾刻了一只展翅的凤凰,旁边是一株盛开的牡丹,空白处祥云缭绕,图案煞是古意盎然。这是妈妈戴过的,苏伊州心里的感觉好新奇,妈妈,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为什么不见我?还有你,一声不吭就走了,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苏伊州的思维逐渐清晰,一股巨大的委屈蔓延全身,不禁冲苏叔良大喊。“对不起,我……”犹豫半晌,苏叔良抬头看着苏伊州,认真地说:“对不起,我决定去见你妈妈时,她还有一个月时间,我不想最后一个月里,你和你妈妈都伤心。既然从来未见,不如不见。”
苏伊州定定地看着苏叔良的眼睛,轻轻地摇头:“你太自私了,你凭什么就做了我的决定?那是我的妈妈,十六年前她生下我还抱过我的!可是我永远都见不到了!你想一个人拥有她,你是个自私的男人!”苏叔良心里猛然一震,没错,苏伊州一语道出了他的真心,他的确是个自私的男人,想独自拥有爱了一辈子的女人,这生命的最后,他要陪她走,谁都不许插手。可这有错吗?夏草,那是他用尽生命去爱的女人啊……
自从苏叔良从江西回来后,益发地沉默寡言,有时候周梓晴问他好几遍问题他都听不见,他似乎陷入了一个与外人隔绝的状态。这种状态太危险了。周梓晴生怕他做什么傻事,整天在家守着他,店里的事暂时让周子墨帮着打理。几天后,恰逢苏叔良的生日快到了,周梓晴和苏伊州、周子墨商量着要给苏叔良办生日,家里已经好久没有笑声了。
农历六月二十这天,一过中午,三人就开始忙碌,择菜洗菜,刮鱼鳞,切肉,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一股久违的家的温暖洋溢着,三人都特别高兴,感觉似乎回到了从前。苏叔良照例是早早起床独自去离家不远的公墓陪夏草说话,日薄西山才想起回家,一天只吃一顿饭,饭量还少的可怜,这些天来日日如此。在这个传统保守的城镇,他的所作所为成了大街小巷流言蜚语中痴情男子的最佳代表。
苏伊州却不以为然,妈妈是走了,难过是自然,哭过后眼泪一擦,日子照例还是要过下去的,难道就要这样伤心到天荒地老吗?活着的人不是更重要?苏伊州替周梓晴不值,就这样一个结婚十六年来一心想着别的女人的男人,有什么可以值得眷恋的?不如怜取眼前人,苏叔良却不晓得这个道理,苏伊州暗叹,每一个痴情男子的背后总是有一个痴情的怨妇在委屈成全的吧。从来浪漫的背后是伤痕累累。
快到七点,苏叔良终于回家,周梓晴兴冲冲地拉他入座,两个孩子把饭菜摆上餐桌,点起蜡烛,让苏叔良许愿。苏叔良显然不明白做这些所谓何事,有些木讷地问:“这是要做什么?”长时间的寡言和独处,苏叔良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说话很慢,眼睛里透着百无聊赖。
“叔良,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来,快许个愿吧。”苏叔良看着蜡烛上闪烁的火苗,良久没动,苏伊州碰碰他的胳膊:“爸爸,快点许愿吧,大家都等着你呢。”苏叔良好像才回过神,轻轻道:“夏草,我只要你。”
周梓晴的笑容瞬间在脸上凝固,苏伊州心里的火腾地蹿起来,站起来指着苏叔良发作:“妈妈走了,我也很难过,可是你悼念亡妻也该有个限度吧,大家好心好意地为你庆祝生日,你就说这样一句话?你就知道你伤心难过,别人看见你这样就不难过吗?店里的生意你不管,家也不想回,你什么都撒手不管了,你还是个男人吗!苏叔良,死了的人就是死了,可是还有活着的人呢!你太过分了!”
“伊洲!”周梓晴拉住苏伊州按她坐下,苏伊州兀自悲愤不已,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周子墨一直没做声,安静地坐在他的椅子上。周梓晴沉默半晌,抬头浅笑,冲苏叔良端起酒杯:“叔良,我敬你一杯,生日快乐!”一仰头,杯中白酒一饮而尽。
苏叔良却好似没看见一样,木然转身就要走,“你不能走!”周梓晴抓住他的手腕,指甲几乎掐进他的肉里,“苏叔良,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她仰着头,声音颤抖,苏叔良回脸看了她一眼,便欲推开她的手,淡淡道:“你又何必再问。”“我不甘心!苏叔良,我不甘心!这十六年来,你心里有她,我不在乎,可是她现在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放不下她?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我的一点点位置吗?”
周梓晴肝肠寸断地质问让苏叔良黯然,他抬手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脸上赫然现出五根手指印,“爸!”苏伊州惊叫,苏叔良看着周梓晴泪流满面的脸,声音很轻,但却无比恳切:“梓晴,是我辜负了你,对不起。”“不!我要的不是对不起!你明知道的!十六年前我跟你回家乡的时候你就知道的!我的一生全葬送在你手上了,苏叔良,我好恨你,我恨你!”随着周梓晴哀哀欲绝的哭喊,她猛然抓起桌上切蛋糕的水果刀朝自己胸口捅去。
“不要!”苏叔良两手去夺,锋利的刀刃几乎将手指切断。周子墨忙扑上去夺她手里的刀,三人争夺间,桌上的饭菜都被碰到地上,周梓晴一跤滑到,刀子本来已经在苏叔良的手里,被她的力道一带,也朝下跌去,刀尖正插进周梓晴的胸口……
苏伊州现在还能清晰无比地记起那柄利刃刺进肌肤的声音,向着吊灯喷溅而出的鲜血带着温度落到脸上的惊恐,蛋糕上白色的奶油花蕾瞬间变成鲜艳欲滴的红,那样的夺目,让她在很多个午夜里尖叫着醒来再也无法入眠。
送到医院时,医生摇了摇头,连抢救都不必了,人当时就死亡了。白布盖上了她的脸,周子墨眼中的仇恨让苏伊州打了个寒颤。警察很快来调查取证,作为目击证人,周子墨和苏伊州都被带到了警局。反反复复的笔录让苏伊州濒临崩溃的边缘。
“当天晚上,他们是怎么发生冲突的?”“他们婚后感情怎么样?”“类似的情况还发生过吗?什么时候?”……苏伊州机械地回答,她不知道人都死了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一遍遍的回答带来的疲倦让心里的悲伤一点点地被挤走,到最后,苏伊州惊讶地发现,从自己嘴里说出的话是那么虚无缥缈,就像这些无比熟悉的名字,苏叔良,周梓晴,周子墨,夏草,都好像那么遥远,就像跟自己半点关系都没有。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警察推门进来跟录口供的同事一番耳语,随后走过来对苏伊州宣布:“你可以走了。”“什么意思?”苏伊州心下一阵茫然,追上去问:“什么叫我可以走了?我爸爸呢?”有个女警似乎心有不忍,悄悄对苏伊州说:“苏叔良和周子墨的口供一致,是苏叔良和周梓晴发生争吵,拿起水果刀刺死了周梓晴。你爸爸……杀了人。”“不!不是这样!他骗人!刀子不是他拿的,他是误杀,刀子不是他拿的!周子墨,你这是报复!爸爸!爸爸……”
苏伊州的强烈反应是所以人意料之中的事,大家都一脸的同情和理解,这让苏伊州更加愤怒,“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听我说话,我没有撒谎,这是一场骗局,我爸爸反正是不想活了,有人还要在他背后捅一刀。周子墨,你这个小人!我恨你……”随着一阵酥麻的痛楚,苏伊州渐渐什么也不知道了。被临时找来打镇定剂的女法医摇摇头叹道:“这孩子也真可怜,一下子就成孤儿了。”
苏叔良被一审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这也许在别人眼中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他们会说,丧心病狂的杀妻凶手终于伏法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苏伊州听着法官陈数整件案件情节时,如同那晚的惨剧在眼前重新上演,一些从来没有的情节被加在苏叔阳的头上,苏伊州目瞪口呆地望着站在被告席上的苏叔良,他微微低着头,眼神很平静,甚至可以称得上祥和,不知道在想什么,对这些莫名奇妙的指控完全不在意,一副认罪的姿态。
苏伊州绝望地冲苏叔良大喊:“苏叔良,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要认罪?你明明不是故意的!你是被冤枉的……”法警将疯狂的苏伊州拖出了庭外,苏伊州在心里恨得牙痒痒,恨不能冲进去将那个小人撕碎。宣判完毕,周子墨走出来,苏伊州扑上去拽住他:“周子墨,你给我说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周子墨推开她,无惊亦无喜,淡淡地说:“苏伊州,你成孤儿了,可我唯一的亲人也没了。这笔帐怎么算?”苏伊州一时无言以对。“我们注定只能做陌路了。苏伊州,再见,不,是永远不见。”
苏伊州怔怔地听完他最后一个字,心里反而平静下来,僵硬的脸上挤出一个笑容,褪下左手腕上的串珠递到周子墨眼前:“好,这样的结局是你们都想要的。还给你。再见,不,是再也不见。”苏伊州转身离开,那串剔透的黄色串珠被周子墨随手抛在身后,像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苏叔良放弃上诉,接下来就是等待枪决。等待行刑的日子漫长又残忍,每一分每一秒都折磨着苏伊州的神经,有时候她甚至宁愿那一天马上到来,一切都尘埃落定也就痛快了,可是心里却撕心裂肺地难受,就像身体的某一部分也被抽走,连呼吸都疼。
苏叔良被枪决前后的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在苏伊州的记忆里成了一片禁区,如同没入百慕大的沉船,很多细节都不知所踪,苏伊州再也想不起那天关于苏叔良的只言片语,只记得他给了自己一张纸条,上面是工整简短的几行字:
伊洲,我的女儿,爸爸走了,剩下的路你要自己走下去,要勇敢。我这一生只为了你妈妈。这样的结局未必不是圆满。对不起。
从那一天,苏伊州似乎变了一个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再让她感觉为难和害怕。她变得沉默寡言,却又坚不可摧,生活已经把自己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还能怎样?最差不过如此,悲剧的尽头已无悲痛可言。
去火葬场领回苏叔良的骨灰安葬好,苏伊州擦干眼泪,马上开始着手面对最现实的问题。店里已经乱成一团,那晚惨剧发生后,周子墨便再也没去过店里,店里的工作人员无人管理,这段时间以来基本没有开工,混乱程度可想而知。
苏伊州先找出酒店的账簿,发现最后这几个月的账目极度混乱,出多进少,还有好几笔海鲜食材的账目没清,记帐凭证与帐本根本符不起来,询问店里的人,都是一问三不知,却都急着追问工资怎么结。
苏伊州冷笑:“我爸爸死了,我可还活得清清楚楚的,你们的工资自然是要结的,我不会拖欠谁一分钱。谁能告诉我,最后这几个月,到底谁在管帐?”大家相互看了一眼,都在心里暗叹这丫头不好惹,纷纷将真实情况说出来。
原来,自从周子墨来苏家后,苏叔良就授意让他学着管帐,还让原先的会计在一旁教他,这近三年来的账目几乎都是周子墨做的。苏伊州心里一凉,知道情形不妙,确实地查了一下,才发现实际情况更糟,店里的保险柜几乎是空的,流动资金只有几百块钱,而且周子墨走后,原先的会计也不知所踪,显然俩人肯定有猫腻。
苏伊州不想再去找周子墨,这个人这辈子也不愿再见到了,无论他吞了多少,只当是替周梓晴善后。至于员工的工资,苏伊州承诺,一周之内把工资结清,目前要做的就是把店转让出去,苏伊州不想也没经验接手这个烂摊子,再说,她还不想辍学。
打发员工走后,第二天,苏伊州就贴出了转让启示,由于是加盟店,地段还不错,而且多年来形成了固定的客源,所以有意的还不在少数。苏伊州谈了几个,有一个双方价格还比较满意,于是速战速决,当天钱货两清。
那位四十多岁的商人看着眼前这个远远比实际年龄成熟的女孩,也不禁赞叹不已。苏伊州心下不以为然,在苦难面前,也不见得非要哭天抢地,残酷的现实更能在几天之间把人变得坚不可摧。钱到手后,发完员工的工资,结完货款,还有近十四万结余,苏伊州当即把钱存到银行。
然而回家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能找到家里的存折,苏叔良根本没有存款!或者是存款在周梓晴名下,而现在存折都不知所踪。这不奇怪,周子墨想做的话一定能做到的。苏伊州已经决定在钱上让步,就不再去追究周子墨。
然而,事情还没结尾。苏叔良下葬后,周梓晴老家忽然来了一大群多年不联系的远亲,苏伊州简直怀疑从前的周梓晴姐弟俩根本不是孤儿,而是生在四世同堂的大杂院。他们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听来听去不过是要钱,总之就是,周家的女孩不能枉死,补偿是一定要的。
苏伊州不禁笑自己天真,以为死者为大,对周子墨让步,到此为止,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在客厅里狠狠地砸了一个茶杯,瓷器的脆响让这群人终归于暂时闭上了嘴巴。“既然大家撕破了脸,我不妨直说。我手里只有十四万,你们要是全要,杀了我也一分没有。我只能给你们一半,你们看着办吧。”一干人面面相觑,管事的终于发话:“好,就这么办!”
苏伊州本来买下一块墓地要为苏叔良和周梓晴合葬的,但是周梓晴那伙远房亲戚死活不答应,非要把骨灰带回老家安葬,为此,又要去三万块的安葬费。苏伊州在心里冷笑,没想到周子墨倒是很会算计,指使了这么一大帮子人来难为自己就是为了她手里的这几万块钱。
送周梓晴骨灰回老家那天,周家人要求苏伊州披麻戴孝跪送,苏伊州没有任何异议,该受的磨难谁也替代不了。她自己找来丧服穿戴停当,反而周家来争气的娘家人一下子丧失了战斗的乐趣。那条槐荫街,多少个晨昏在这街上走过,从来没觉得它有这么漫长,十里长街,一步一跪,一身孝服的苏伊州白衣胜雪,毫无表情地将这荒诞的仪式进行到底。
那一天,似乎全世界的人都来围观,苏伊州看不见,也听不见,奇怪的是,她想起了很小的时候,苏叔良牵着她的手走在这条街上,带她去电影院看电影,路边有卖棉花糖的,苏叔良还给她买了一只,那天看的什么电影,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那棉花糖的滋味真甜……
跪到了火车站,刚下火车的人不明所以,看西洋景似的纷纷打探事情始末,版本辈出。周家人施施然登上南去的火车,苏伊州扶着路边的路灯站了好几次才艰难地直起身来。
“苏伊州!苏伊州——”方少阳从人群里一路狂奔,那么多人,就像永远也过不去。满头大汗的他终于站定在苏伊州面前,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你……”看到心爱的女孩憔悴至此,膝盖上早已破烂不堪,血肉模糊,方少阳禁不住嚎啕大哭。他被关在家里的这几天,竟发生了这么多事,件件触目惊心,让他如何不痛。“方少阳,我都这样了,还值得你喜欢吗?”苏伊州只轻轻吐出这一句就疲惫不堪地晕倒了。
这一觉,足足睡了两天。醒来,正好是半夜,窗外漫天的星星闪闪烁烁,月光清凉如水,方少阳在身边早已睡熟,这个以死相逼从家里跳窗而逃的少年,用自己的倔强守护着心爱的女孩。苏伊州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光洁的额头,挺阔的鼻梁,柔软的唇,这个倔强的人啊,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放手,认定了就要一条道走到黑,碰到头破血流也不知回头。
方少阳感觉到她的抚摸,猛然睁开眼睛,惊喜地看着她:“你终于醒了。真好!”苏伊州一伸手够到他脖子里的吊牌,里面是那张初一时的照片,那时的苏伊州是那么的稚嫩,在镜头前略带羞赧地笑着。“你是从哪偷来的?”方少阳的脸上竟浮现出少见的羞赧:“从莫小闵办公室的抽屉里。”苏伊州不禁哑然失笑,为了她,他真是什么都敢做。
不知道是谁主动,两个人轻轻地拥吻在一起,从浅浅的吻一直到激烈的,那感觉真好,就像把自己放心地交付给对方,不用管什么未来,什么明天,一切都随风去吧,只有眼前的片刻欢愉才是最真实的。方少阳把手探进苏伊州的衣服,她没有反对,一直微笑着,带着少女的羞涩和妩媚,方少阳怜惜地吻着她的脖颈,她的胸口,她的肚脐,身上的每一寸肌肤,这是他的女孩,他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应到,她完完全全地属于他了。
当方少阳带着激动的哽咽进入时,苏伊州紧紧搂住他的脖子,他肩上的那弯齿痕宛然如新,就像一道纹身,深深地烙在他年轻的躯体上。伴着让人窒息的吻,他们同时到达高潮,苏伊州用尽力气抱着俯在身上的躯体,眼泪止不住流到唇边,咸咸的,苦涩的,就像这躲不开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