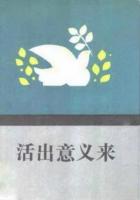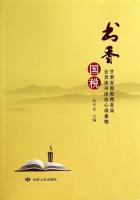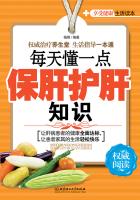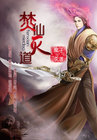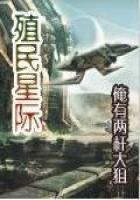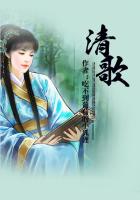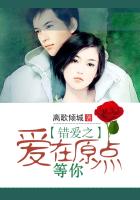有好长时间了,每当我从德格印经院门前路过时,总有什么在叩撞我的心扉。一时,又不清楚那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八月里一个炎热的中午,又从德格印经院门前经过。伟岸的杨树枝叶如盖,绿荫下一条淙淙银溪送来沁人肺腑的凉意。印经院对面,一座钢骨水泥的大楼正在拔地而起。人声沸腾,机器轰鸣,同印经院门前的安静形成了鲜明对比。回首,印经院褐红色的高墙也同往常,今天却显得异常的沉默,就如一位阅历太深的老人,正在中午的阳光下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与思索。
一想到印经院像一位老人,我的心不禁“咯登”一跳,这印经院老了吗?我知道,印经院已经有了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对于一座建筑已不算年青,可印经院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抬头看,高墙上的那对镏金孔雀竟在我的想象中展开了翅膀,飞离印经院的屋顶,飞舞去了白云朵朵的蓝色天幕上。这对美丽的孔雀,抖开了五彩神羽,绚丽,灿烂,光芒四耀。充满活力的优美舞姿,令人眩目的光斑,分明是在向人们宣告:德格印经院不可能是垂暮的老人,重新焕发出来的青春光彩,源于他所拥有的不朽,他所拥有的神奇生命力。
于是,莽莽的雪峰冰川,辽阔的大漠草原,异国归来的游子泪花,高楼里从事研究彻夜不灭的灯光,竟一时毕聚眼前。有人注目,有人顶礼,有人关心,有人钻研。德格印经院偏居康藏高原一隅,可是名声却传遍了世界,作为藏族文化灿烂的明珠,闪亮于千万人的心中。
我曾经粗略地领会过德格印经院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仅仅是听人介绍,眼前便呈现了一个万花筒般的奇异世界,在这座伟大的艺术殿堂里,胜景接踵而至,美不胜收,叫人目不暇接。我,曾经狂喜地幻想过,假若真成为一名研究者,钻研开来,在这里,该有怎么样一派奇妙的境界啊!
且不说那有着二百五十多年历史的、庄严肃穆带着浓郁喇嘛教派气味的建筑外表;也不说大殿经堂里那些色彩辉煌、造型生动、让雕塑家们叹为观止的众多神像;更有那满壁、满廊的壁画,满壁栩栩如生的佛国臣民,多少年来,就一直这么逼真地向凡人们暗示着:神秘莫测的佛界同宽阔宏伟的世俗生活原出一辙!这些都不必说了。
单说那一块块木刻经板吧。
早先,它们是生在山谷里的桦树,斧伐刨平,烟子熏过酥油浸煮,经过好多道工序才由木刻高手来精雕细刻。一个笔划,常要数刀才成。小小的经版,每一个字母都勾画了了,清清楚楚。刻就一块经版会耗去多少工时,多少心血?一块又一块,八百三十多部书,经版达二十三万块之多。其涉及的内容更令人咋舌:从佛学理论、文学辞学、诗词音韵,人物传记,到天文地理,医药医学、历史典故、机械原理……几乎无所不包。一块不大的木板,它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已经远不止文字所记载的,那上面附丽着一种精神!
有人说,喜马拉雅山是高耸入云的凝固了的海洋,因为那里的化石说明,在喜马拉雅山上可以找到海洋里的一切。
这有点像德格印经院,因为在那里取出一本书,都可以从中发现藏族人民在千年前进、发展中的足迹来。正因为这一点,有理由说德格印经院不光是一片知识的海洋,它还是一座丰碑,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般的丰碑。
有人以为,印经院完全是神佛的领地,它所拥有的文化艺术都属于佛国的艺术。再说,当年印经院因宗教而产生,后来也因为服务于宗教而名扬四方。这种说法虽有他的道理,但我们还是发现,在印经院大殿的经堂里,除了神像,还有一位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唐东杰布”,他也在享受着香火。他是藏戏的开山鼻祖,又是一位了不起的桥梁等工程的建筑专家,他一生的事迹在藏族人民中广为传颂。此外,大殿里还供奉着德格第十二代土司曲加?登巴泽仁的塑像。在二百五十多年前,就是他倡导并领导了修造德格印经院。就因为这,人们当然有理由不能忘记了他。诚然,在印经院内保存着讲解佛教教义、宣扬佛法、戒律的如《甘珠尔》、《丹珠尔》等书。可在印经院内也保存着用韵文形式传授治病救人方法的医书《四部医书》及其它同佛教毫不相干的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本是外来的,传到我国藏族地区,一个佛教竟演化成了黄、红、花、白、黑五个教派。有内行说,佛教来到藏区,有时很难分辩出“舶来”的踪迹。这倒让人想起鲁迅赞扬过的“拿来主义”了。不过,这得看你怎么拿来和你的胃液是否消化得了。话说回来,在印经院里,喇嘛教五个教派的所有经典是一应俱全,没有重此轻彼。
由此可见,印经院是一处人与神可以一堂“共处”,科学与宗教也能一楼“并存”的场地。这奇妙得看上去还是和谐的“结合”,大概算得上德格印经院的一大特色。从这里倒也反映出了德格印经院对知识的态度是兼容并蓄,有包罗万象的博大气派。
然而,印经院的褐红色的围墙确实太高、太厚了。以致使翘首仰视、合掌磕头的虔诚信徒们完全把它看成一块神秘的佛国圣土。多少年来,怀着虔诚的心情议论它、朝它跪下、围着它转经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不得而知。但是才过去不久的、十年动乱中在它身边发生的事倒还依稀记得点。就在乱的高潮中,有人异想天开地在印经院一侧筑起一道高墙来,满以为这堵墙断了转经者的路,转经者就只好“望墙兴叹”了,然后“面壁而悟”,转回到“革命”路上来迈大步。殊不知,墙是人筑的,人也会拆墙。你明里筑,他暗里拆,筑了拆,拆了筑,乃至派员站岗。然而漫漫十年,究竟哪一天中连一个转经的人也没有呢?这恐怕要成为悬案。
到了一九七九年,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重新贯彻执行,有段日子里,印经院前尘土飞扬,转经的人多到了脚步也难以移动的地步。于是,“疯狂”、“狂热”一类的评语骤起。愤愤不平、想出来制止一下的也不鲜其人。曾几何时,那浪头却消失了,目前的印经院虽还不至于门庭冷落过分,却再也没有一九七九前后一段时间里转经的人那么多了。原因之一是一大批宗教活动点的开放,方便了信男善女们就近拜神。真是堵塞莫如疏导。这“疏”不仅是疏散,更是一种引导。站在印经院前,望着几个老阿妈手摇转经筒,步履蹒跚,突然想起伟大的列宁,他在什么时候说过“宗教是一个历史现象”。那么,历史本来就是一个过程啊!
早就有人把德格印经院喻为“藏族文化宝库”了。浩如烟海的文卷是藏族先辈们不朽的贡献,也就成为了不朽的历史。整理、研究、继承,使之为今天服务,妥善保护好它,就是今天我们这代人的职责。中央、省、州、县集资一百五十多万,在不损印经院原貌的前提下,要加固它,整修它。同时,还将建一座附属建造。有人难以理喻,说花那么多的钱,还不如推倒旧楼,另建一座新的印经院。但更多的人却理解了:保护印经院古朴、独特的原貌,就是保护了印经院不可再造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特色,这是在保护具有历史价值的美!
有一年,寄居异域的一位老游子归来了。他一见到印经院就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是的是的,这就是原来那座印经院,没想到它还是这么地完好。在国外,有人说它早就被共产党变成一把火了,我还真没有想到。”他惊讶、激动,继而自豪极了“这是我们的,这是外国没有的!”
恍惚中,我觉得我已随着寻对灵气四溢的孔雀,遨游在了万里长空了。极目四望,无数粗犷的群山挽起钢铁的臂膀,恰似藏族人特有的英武豪迈的形象;条条奔涌的江河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又恰似藏族人永不枯竭的力量,就是这群山和江河构成了莽莽的康藏高原,孕育出了这伟大的文化,印经院只不过是一个缩影。这块联接广大汉族地区和辽阔西藏的枢纽地带上,藏族人世代生活。万仞雪峰留下过他们的脚迹,千里牧场上响彻他们的歌声,有多少幻想曾随着寺庙颤抖的号音化为了飘烟,而当他们怒吼了,沉重的枷锁纷纷锵然堕地……于是,历史有了记载,有了印经院……
想到这里,一股壮美、博大、深厚的爱意在我的心房腾涌。藏族人民的命运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命运是连在一起、是相通的,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由各兄弟民族世代共同创造的。德格印经院所保存的不仅是藏族人民的文化,更是藏族人民政治、经济、历史综合记载。它是藏族人民的,也是中华民族的。
一时里我豁然开朗:每当我从德格印经院门前经过的时候,原来是一股爱的情思在叩撞我的心扉,那是我对藏族人民的尊敬和佩服。也是我,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豪情和自信在叩撞我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