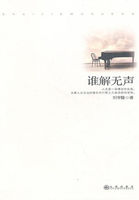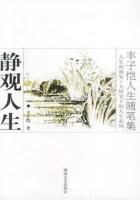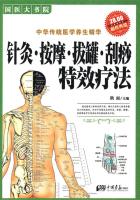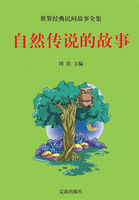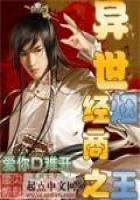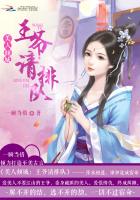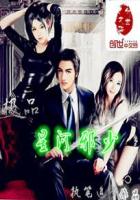九十二、小葛妹妹来去匆匆
电影《决裂》的主题歌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歌词,是“啊呀勒,啊呀勒耶——人望幸福(耶)树望春(勒),解放挖掉了咱穷命根(勒)”。
“解放挖掉咱穷命根”,是一个庄严的承诺。可是——做到了没有,是怎么做的,究竟还打不打算做?这些,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答案的。
“四人帮”故意用苦行主义来遮蔽这个承诺,他们的公式,大约就是“越穷越苦越革命”,连农民抠鸡屁眼的那点儿钱,都要被诬为“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其他的,可以想见。
人民,不是抽象的圣徒,是要过日子的,要油盐柴米,要多几尺棉布。自从1963年经济复苏后,我记得,我省的猪肉一直是敞开供应的,到了1967年两派大武斗,物资供应开始紧张,此后就是凭票供应,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四两油、半斤肉地对付,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垮台后的一段时期。
“革命”,为什么越革越穷?
人为什么没有奔头?
在这样的悖谬之下,人们怎么会“精神饱满”?又何来动力“忘我苦干”?
1976年夏季的农民,还是那样默默地生存着。我跟随老王下乡蹲点,都是吃派饭、住老乡家。各处的农民,一如既往地贫寒,但家家都还收拾得挺干净。吃派饭的时候,房东大婶总要苦心炒两个鸡蛋,以示尊重。
我有时也被派去和其他公社干部蹲点,“抓路线”,“抓方向”。夏末,老王派我去公社南部一个大队,配合那里的工作组开展工作。我到了地方一看,原来工作组的领队,就是那个“摸手”干部。
他大概不知内情,对我毫无敌意,反而有几分恭敬。在大队部开会时,他讲完了话,还特别请我也讲一讲。他对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等人介绍说:这是咱公社下来的,请他给你们讲讲。”
我讲了些什么,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大队干部们全都在洗耳恭听,若有所悟。
我的感觉,很奇特。在我们大队,大队书记是压在我头上的大山,而在这个大队,大队书记对我毕恭毕敬,有如下属。这个反差,是怎样产生的?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体制”。
在南部大队蹲点的时候,我忽然接到公社妇联主任的电话,妇联主任有家室之累,一向担任留守,她对我说:你的一个什么同学,女的,姓葛,跟一帮人来咱们公社参观,打听你。我告诉她了,你在南部大队。你等等啊。”
片刻功夫,小葛在电话里说:是我啊,我们地区组织知青参观团,来你们县参观学习,你们不是全省知青工作的典型吗?我们一会儿就去南边公社,你在路边等着吧。”
是小葛妹妹来了!
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上了公路,在路边张望。等了一个多小时,路过的大卡车倒是有几辆,但没见有车停下,也没见车上有人跟我打招呼。
我失望而归。
当晚我赶回公社,在招待所里等。小葛妹妹从南边回来后,我们终于见了面。
我问她:上午在公路边,怎么没等到你?”
小葛妹妹说:嗐,你那个样儿,头发老长,被风刮得那个乱,跟狂人似的,我还敢叫车停下吗?”
小葛妹妹对我近期的思想变化很满意,觉得我有了进步。
我叹口气说:我还是怀念邓小平在台上的时候……”
小葛脸色一变,急忙打断我:嘘,你说什么呢?你这人,还是那么乱讲话,这是什么时候了!”
我把话咽了下去,心想:这不就我们两个人吗?小葛这人,还是俗。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小葛妹妹是对的,太对了。
第二天,小葛妹妹一行人走了。在公社办公室,妇联主任一见我就问:“那是你什么同学呀?一接你电话,那眼泪,刷刷的!我看得真亮的(清清楚楚的)。哎呀,看你们这同学感情!”
我“嘿嘿”两声,应付了过去。
就这样,我这公社“秘书”,做得渐入佳境。
我吃饭的那个镇公社食堂,有一位卖票姑娘,容貌端庄,时间一久就熟了,见面都要打个招呼。后来,忽然觉得她有点儿过分热情,想了想,才明白是什么道理——我们公社有县里派驻的几个青年干部,他是把我当成县干部了。
且不说我不能接受她的任何暗示,就我这知青身份,一旦戳穿,那该有多尴尬?
我只有装看不见。
每天早上,我还是要漫步阡陌间,看原野一片葱茏,飘着一层夏日的雾气,心里很是敞亮。
大喇叭里的歌声,也正应和着我的开朗心境:“江山万里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九十三、唐山大地震那个月
7月盛夏,公社班子全体拉到一个水库边,住在老乡家,关起门来办“爬坡学习班”。
所谓“爬坡”,就是指提高思想。那年头上面下来的精神,全是违背常识的,连干部也很难理解,因此需要“爬坡”。
这次爬坡,是爬“基本路线”的坡,也就是,要深刻领会“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书记和主任,每人配一个秘书写心得材料。领导先给秘书讲,自己的思想有哪些落伍之处,后来是怎么通过学文件提高的。其实全是空话,思想本是没影儿的东西,落伍了怎样,提高了又怎样?都是“糊弄鬼子”吧。
我们公社原有3个专职秘书,加上我一个临时的,是4个,专给排名前四把手写。其中一个比较老成的秘书,叮嘱我:你负责的副书记,我看讲得不怎么样,到时候过不了关,你就要沾包。你必须跟他说清楚,他讲的深度不够。”
这是经验之谈,我很感激,马上照办了,还给老王也打了招呼。
于是,这位副书记的稿子不过硬,在他还没念的时候,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爬坡”开始后,那场面相当严肃,有军宣队、工宣队、县里派驻的干部等等,一圈人压阵,一位一位过筛子,讲评。
我负责的那个副书记磕磕巴巴把稿子念完,果然,众人通不过。那位副书记也没法儿责备我,因为我已经有言在先——你提供的素材原本就不行。
副书记只好认栽,红着脸说下次再提高,也就这么过了。
轮到一把手关书记做发言,说得还不错,条理清晰。
关书记没做过基层一把手,跟前任书记比起来,有点儿“面”。公社的中层干部背地里都叫他“关老太太”,意谓“处理事情不果断”。
在场的军宣队老房,是个营级干部,说话水平不太高,平时做正式发言时,老是词不达意。这在平时没什么,毕竟他是个老好人,可是这次却捅了娄子。
他咳嗽一下,对关书记的发言发表看法:我看老关的斗争性不够,公社班子软、懒、散,很严重,可以说,那个那个……登峰造极了。”
大伙鸦雀无声,气氛骤然紧张,老房毫无察觉,啰里啰嗦又说了不少。
他话音刚落,关书记在炕上坐直了身板儿,也咳嗽了一下,说:我要讲两句。我们公社的班子,我认为是团结的、是坚强的,革命生产各项工作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是哪个人说不行就不行的!各位同志,要发扬成绩,不能听风就是雨!我的话完了,散会!”
关书记平时脾气和善,这次脸色都变了。老房一听这话,脸涨得通红,啥也说不出。
下午,后勤一位助理对我说:“这老房,嘴上没个把门儿的,瞎说!关书记一发话,他懊糟了吧,连晌午饭都没有吃。”
整个过程,我看得目瞪口呆,似乎领会到了某种规则。
权威是不可持久战的,哪怕他一脸慈祥。
公社秘书中,有一位胖子,戴个眼镜,眼睛老从镜片上面往外看,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官。他大我一岁,“文革”前应该是念到初二了,但我跟他接触多了,觉得他的水平就只像“识俩字儿”的。
我没事儿跟他聊聊天文地理,他啥也不懂。我一说,他就惊讶得眼珠溜圆。我那时候年轻,不懂得尊重人,就想捉弄他。我估摸着,哥伦布是谁,他一定不知道。
一天会间休息,我问他:你能把鸡蛋竖起来吗?”
胖翻译说:那哪能?”
我说:我能。”
他眼珠瞪得溜圆:你吹牛吧?”
我坚持说:我能。”
他狡黠地眨眨圆眼睛:不许用别的东西支撑,也不能用胶水儿粘。”
“那当然,直接竖。嘎个东(打个赌)怎么样?你输了,给我五块钱,我输了我给你。拿个鸡蛋来吧。”
一旁看热闹的房东,赶紧从鸡窝里掏了个生鸡蛋出来。
胖翻译说:等等,我看看。”
他从眼镜片上面,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会儿,递给我:你弄吧。”
几个主要领导不在,满屋子的干部都在看着我俩。我拿起鸡蛋,“咔嚓”一声就墩在了炕沿上。
鸡蛋直直地竖在那儿,蛋清从下面流了出来。
满屋子人,笑得前仰后合。
胖翻译急红了脸:你这不耍赖吗?都破了。”
“你也没说蛋壳不能破呀。”
事后,老王对我说:你对胖子,要尊重一点儿啊,毕竟是老同志了。
你这小子!”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我们毫无感觉。第二天,消息传开,晚上关书记下令,今后半个月,全部睡到院子里去,不准在屋里睡。
老乡帮我们在小院的臭李子树下,铺上秫秸,打了一宿地铺。7月底了,晚上还真是有点儿凉意,早上起来摸被子,好像潮潮的。我心想:像这么在外面睡半个月,那可糟了。
第三天,禁令自动解除,谁也不肯再在外面睡了。
这次“爬坡学习班”,思想虽然紧张,身体可是享福了。水库给我们派了做饭师傅,最后一天,是“全鱼宴”,都是从水库里打来的活鱼。伙房连高粱米饭都没准备,整整一桌的鱼,可劲儿造!
不吃饭,光吃鱼就吃饱了,我人生中就这么一次。
学习班结束时,后勤给每个人分了一条大鱼,有七八斤重。我请假回家,拎着大鱼进家门的时候,姥姥差点儿没吓着:这是什么呀?这是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