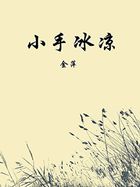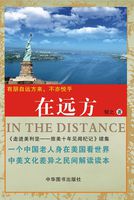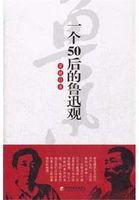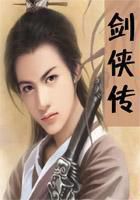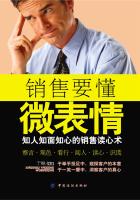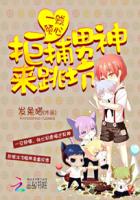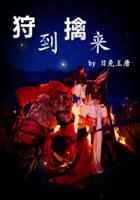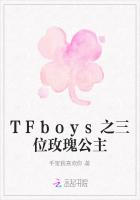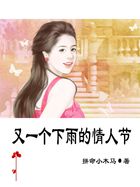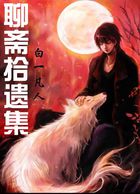五十、报社怀疑是“伪作”
我在省报上发表的这篇稿子,还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1972年,知青写东西的情况,还非常罕见,加上我这稿子又有一点新意,譬如用了“鬣马萧萧”这样的古词儿,把报社编辑雷了一家伙。编辑觉得奇货可居,立马决定采用,可是心里没底——怕我是抄来的,就打电话到我们公社去问。
一问,有此人,但会不会写东西,不敢保。
编辑呲了牙,想了想,对我们公社党委说,那你们给我们寄一份证明材料来吧,证明有此人。然后,编辑又问清了我父母的单位,打电话到我父母单位,询问人事处,问某某人是否有个孩子在农村插队。回答说:没错儿。”编辑便又问:这孩子给报社投了一篇文艺稿,写得不错,请问他父母会不会搞文艺创作?会不会是父母代写的?”
人事处的人一听就笑了:“我们这儿是科研单位,没听说有谁能搞文艺他作的。”
这一说,编辑放心了,等公社盖有大红印章的证明一到,稿子就发表了。那时候没稿费,报社寄给我一份报纸留作纪念,也就完了。
那我写稿图个啥呢?
除了要证明自己,总还有所图。
稿子一发表,我们大队倒还没啥动静,公社机关却有不少人知道了:某大队还有这么一个人,能耍笔杆子。
——我要的就是这个,名气!
我被意外的成功所激发,越发来了劲儿,每月都要投个一两篇。投稿一多,看自己的两笔字,实在写得太臭,就苦练钢笔字。那时也没有字帖,我就把表哥写给我的信当成字帖。他的字,还有点儿自成一体的模样。这样苦练了两个月,好了,我的字,起码有“体”了。后来我也帮编辑部处理过稿件,知道凡是字写得差的,编辑都厌恶,命中率极低。
那一年春,好朋友李兄走了,去了延边,投奔他姐夫去了。临走时,给我介绍了一位镇上的下乡知青,跟我们不在一个公社。我慕名到他劳动的地方去找到了他。
这位老兄姓王,见面一聊,果然才气横溢。他在学识上,兼跨文学与哲学,跟我大聊郭小川的诗《甘蔗林——青纱帐》,外国的则是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谈起古典文学来,也滔滔不绝,“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就挂在他嘴边儿上。
这是什么时代啊,能有这样的奇人!我大为振奋。
我不再是孤军作战——瞧瞧王兄这才气,将来都能做省委书记了。
半瓶子醋如我,能不发奋努力吗?
五十一、图书馆是我的大课堂
在迷茫中踏上一个虚幻基石,我自以为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信心百倍地前行了。
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在此之前,尽管我也读过那时书店里罕有的几本“另类”书籍,比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先生的《世界通史》,但离搭起基本的知识框架还差得远。
除了拼命搜罗“禁书”外,我还发现了一处学习的好地方,可以使我眼界大开,那就是市图书馆的阅览室。在理论上,那时我们是最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当时面对人民的公益事业并不多。就算是图书馆,对于借阅者也有诸多限制,我这样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借书是想也不要想。但那里的阅览室,是无条件向公众开放的,我可以在阅览室里翻阅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没人查我的单位。
1972年,文学爱好者被压抑已久的欲望爆发出来,各地的文艺刊物——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在阅览室里,我看得眼花缭乱,拿出随身带的软皮抄,记下我闻所未闻的“经典词句”。
我一向以为,要想写一手好文章,在最初,一定要有搜集汉语文学词汇的习惯。我们平时看社论、看教科书看得多了,即使写文学作品,也是一副八股腔,面目可憎。不经过一番积累,想写出花团锦簇的文章,那是妄想。
与我大致同龄的、很多后来出了大名的知青作家,大概当初都做过这种功夫,譬如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贾平凹等等,他们的现代汉语表达功夫,远超过此前此后的作家。那些在“文革”期间念中小学的作家,就别指望能有“文采”二字了。
那时在阅览室读书的感觉,无比之好。从农村回家探亲,我必去阅览室坐上一两天。在这里,没有雨雪风霜,见不到土得掉渣的老农,只见窗明几净,人人都屏息敛气读书。
我想我这辈子再不可能上学了,不可能再坐在教室里了,那么,就权当这里是教室吧。从那时起,读书于我,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是一种“代偿”体验。
40年来,“读书无用论”几次甚嚣尘上,甚至成为全民共识。读书是没啥用,但是,打麻将有用吗?暴饮暴食有用吗?也都没什么用,人们为什么仍然乐此不疲呢?
可见,读书若是去掉了功利心,也还是很美好的,就像在街上看漂亮女人。
有一次,我在阅览室里正埋头读报纸副刊,一位年轻女士忽然凑过来,很感兴趣地问我是哪个单位的。
我红着脸说:我是知识青年。”
那女士很惊讶,跟我交换了彼此的大致情况。她说她是一名工人,愿意读读写写。
这位女士在看我的时候,神色间有无比敬佩之意。是啊,一个知青,前途茫茫,居然还能来这里看书,不是傻子,就是今日所谓的“潜力股”,她势必印象深刻。
不想多年后,她成了与我同系同年级的大学同学。不过,在学校里,读书已经完全变了味儿,那种传奇感也就没有了。我们在大学里彼此认出,后来却连朋友也不是。
五十二、一夜间“百花齐放”
现在的教科书对“文革”时间的界定,是整整10年,而在我们那时的概念里,“文革”也就是1966到1968那三年的混乱时期。从1969年以后,大动荡收场了,随之而来的,是“新秩序”,但却压抑得要死。
这情况,从1972年春天起忽然有所转变。
1972年,是“十年浩劫”中短暂的春天。
我那时身处穷乡僻壤,不可能知道什么内幕,变化是从广播里获知的。不要小瞧现在只有驾驶员才听的广播,在那个年代,它就相当于今日最权威的“央视”。
1972年的“五一”,我回城探亲,住在家里,贪恋着短促的城市生活,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一首陌生的歌曲,男声独唱,声音激越,歌名叫《北京颂歌》。完了又有一首《雄伟的天安门》;完了又有一首《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再一首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哇,心都要醉了。
我被惊呆了。那时节的所谓音乐,除了8个样板戏,就是15首历史歌曲。而在15首历史歌曲里,还包括《东方红》、《国际哥》两首天天都听的老经典。在这些熟得不能再熟的旋律之外,广播电台只要播出一个另外的旋律,就能让人们一激灵。
东北的“五一”,正是初现绿意的大好时光。这一组新播的歌曲,虽然也是“颂歌”,但庄严、辽阔、高昂,透露出“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舒展气息。
没有什么能比音乐更能制造气氛的了。从那一天起,大家小巷,无论是电线杆上的大喇叭,还是住家窗口里的收音机,整天就是播放这一批优美的歌曲。
这是一股“解冻”的春风。
政治坚冰开始融化了,它融化的声音,妙如天籁。
声音,是用来满足耳朵的。那么,满足头脑的呢?
也有了。
那一年,周恩来总理发话——这一切“解冻”都缘于他——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诗人贺敬之的《放歌集》我们终于能买到新的文学书了!这之前,书店里除了1970年出版的6本马恩著作单行本之外,别无新书,连鲁迅著作都没有。《放歌集》的再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本诗集是浅蓝色的封皮,上面有延安宝塔山。贺敬之,此前我并不了解他,看了书,才领略了他的歌谣体《回延安》、《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领略了他模仿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
这些诗,若放到今天,人们不捂嘴笑就不错了,可在那个年代,我如闻天音。你看,“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还有“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这诗句,在当年堪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和小镇青年王兄经常交流信息,我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放歌集》的再版,都很激动。
这是一个信号,文艺要松动了。王兄的记忆力好,张口就能背诵多年以前熟读的贺敬之诗句。贺敬之,成了我们心目中活着的神。
闸门一开,洪水是挡不住的,新华书店马上又解禁了一批“文革”前出版的小说,都是无名之作,内容没啥意思。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的,永远不敢放出来。外国的书也有,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也出来了,只是一个姿态吧。那时我们读抨击资本主义的作品,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没有感同身受啊。
那一年,还有一本令我激动的新书,诗人李瑛的《枣林村集》,里面收进了很多他在“文革”前写的诗歌。我在本书前面提到过“锅盖一掀,十里饭香”,就是他的句子。
“文革”前的“十七年”,在我们心目中,已经被圣化了,任何能再现往日气氛的文字,读起来都那么亲切。“文革”中的知青,最大的理想,就是社会生活能回到“文革”前。
那一年的从春到秋,我是在激情中度过的。东北平原上的夏季田野,绿色茫茫,清晨,朝露未散,有线广播喇叭里,放着气势磅礴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我扛着锄头,走向田野,满怀憧憬……
那就是我的青春,很糟糕,很简陋。但毕竟是青春,一回想起来,就要激动得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