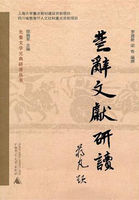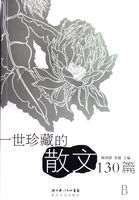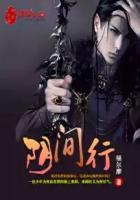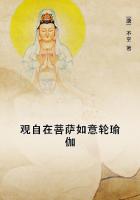三十二、远嫁的团支书
我们大队,有一位很不错的女团支部书记,姓丁,那一年才18岁。我对她有深刻印象。
那个时代的青年,一般是两个极端,一种是因为前途迷茫,精神世界比较灰暗;另一种是信奉“适者生存”,扭曲了人性,比较急功近利。而这位容貌秀美、性格开朗的丁支书,却既能保持女孩子的本真,又能适应时代。
她是回乡青年,家就在我们附近的第3生产队,初中毕业回乡参加了劳动。农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名义上不能脱产,可是当时政治任务极多,绝大部分时间里,小丁都在各个生产队“蹲点”,帮助生产队长完成各种阶段性任务。因此,小丁实际上不用干多少农活。
当然,她人不笨,即使是干农活儿也不差。
小丁到我所在的生产队蹲过点,跟我认识,有时愿意和我谈谈样板戏什么的。她很敬重我“有知识”,但也对我在政治上不能“与时俱进”有点儿蔑视,只不过嘴上不说就是了。
满口“革命”术语的乡村干部,在待人处世上却还能保留一份本真,这很不容易。小丁就能轻易做到。
她永远是乐观的,到哪儿都是笑盈盈的,跟谁都能说上话,说话办事,透出干练。
在百无聊赖的乡村,小丁书记也算一道风景吧,一身很得体的小夹袄,一双说话就笑得眯起来的丹凤眼。
她在群众中,口碑不错,没听见有人说她任何坏话。她的老爸我也认识,一个挺热心的老农。
小丁在我们队蹲点大约有一个冬天,完了就走了,只留下这么个印象。
一年之后,3队的回乡青年中有我的朋友,突然告诉我一个惊天的消息:小丁和3队的生产队长、一位有妇之夫搞上了,搞大了肚子,在家里生了孩子!
那个生产队长,30岁出头,以我当时的眼光看,就是一老奸巨猾的家伙,人品上没有一点儿可爱之处,是在乡村中稍有文化、很吃得开的油滑人物。
那位队长有老婆有孩子,他们是怎么搞上的呢?老农们猜测,只能是“野合”了——在高粱地里干了那事儿。
我在震惊之余,百思不得其解:农村虽然人才匮乏,但好小伙子还是不少,小丁年纪轻轻的走上了仕途(那年代叫“政治进步”),她怎么能看上30岁出头的大老爷们儿?
当然,这在现在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了——20多岁的,都能看上80多岁的了。
3队的朋友所说的情况,很可怕:小丁怀孕后,一直瞒着外人和家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直到在家中炕上突然临产,血流了一炕,孩子也死了。
两个多月后,听说小丁身体恢复了,大门不出,大队团支书的职务也给撸了。又过了几个月,听3队的朋友说,小丁嫁到本县很远的一个公社去了。
小丁后来还能不能回来走娘家?
我想,能。但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她。
三十三、战争遗孤
东北这块儿土地,辽阔安宁。可是自从清末以来,到1948年,这地方就没消停过。大名鼎鼎的张大帅,出身实际上就是“胡子”——土匪。后来“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莫名其妙地沦于敌手,日伪当局欺压中国人,不让老百姓吃大米,吃了就是“经济犯”,要枪毙的。
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青纱帐里“胡子”又起,据我们屯儿的老年农民说,往山里那边去一点,村村都有人当“胡子”。高粱长起来以后,他们就出来劫道,手持木棒,俗称“棒子手”,见到路人就一棒子“削倒(打倒)。
胡子,让战后的老百姓谈虎色变。
那时候,我们这边靠近铁道线,屯子里没有“胡子”,村民在村庄四周建起了土围墙,“胡子”来了,老农就拿猎枪、土枪抵抗。当然,也有的时候花钱消灾。
老农们说,“胡子”来打家劫舍的时候,个个骑高头大马,一人一杆枪,气势吓人。但“胡子”怕“中央军”,当时国民党军在省城有一支“铁石部队”,经常来扫荡“胡子”。“中央军”也是一人一匹马,疾驰而来,胡子完全不能抵抗,落荒而逃。
“胡子”怕“中央军”;中央军”呢,怕“八路”。
后来,在1948年夏,国共两军在省城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围城战。那时,有一些饥饿的难民从城里跑出来。
我下乡那地方,离当年著名的“红旗街卡子口”有30公里远,侥幸跑出来的难民,有的就从我们这里路过。
历史,也刻在了我们屯儿的年轮上。我们生产队有一位马倌,人很善良,不幸是个豁子嘴(兔唇)。他有个宝贝儿子,是方圆几十里内学历最高的一位——高中毕业生。
这位高中生,就是当年那场战争的遗孤。
1948年夏,他还在襁褓中。他的亲妈,当时还是个小媳妇吧,好不容易从卡子口里跑出来,路过我们那儿,实在带不了这孩子了,就给了豁嘴儿家里。豁嘴儿两口子无后,就抱养了这孩子。
老两口心疼孩子,给孩子起名叫满囤,俗是俗,但可以看出爱之切来。
他们疼孩子,小时候不让孩子干活儿。孩子喜欢读书,豁嘴儿就全力供养,竟然一读就读到了高中毕业,可惜遇到“文革”,只能回乡来劳动了。
我们屯儿里的老农,一点也不尊重这位高中生,因为在老农眼中,这是一个读书读废了的典型。
他是啥活儿也干不好。
虽然人还算机灵,但高中生在农村,就是个异类。我是个半拉子初中生,但也觉得他是个异类,他是在镇中学毕业的,身上并没有“城市气息”,还不如那几位下放工人。
他就这样,几头不靠。
那时候的媒体,讲得好听,说农村知识青年可以参加“三大革命”,也就是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而实际情况是,农村根本没有科学实验,只有后来安装的电灯泡算是科学装置。就算是有科学实验,满囤先生也没学到什么实用的知识,参加不了。
满囤家在屯里是孤姓,没有家族势力,阶级斗争”从政)也轮不着他,连记工员都当不上。
生产斗争,满囤又十分不灵。
但不管怎么样,他是在一个比较殷实的农家长大的,还念到了罕见的高中毕业。他那位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的老妈,若有知,也该放心了。
三十四、台湾姑娘
1970年的夏末,我沉闷的乡间生活有了一点儿松动。那时候,大队要搞一次大批判宣讲活动,到各生产队去宣讲。
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这纯粹是扯淡。但夏锄过后,没有事儿干,扯扯淡也行,大队决定搞一家伙。现在我回想,那大概是为了政绩。
在农村搞大批判,不容易,因为识字的没多少。正好各队都有下乡或回乡知识青年,于是大批判的主力,就是这帮人了。
当时我们有10个生产队,一个队选派一个年轻人,集中到大队,写好大批判稿,每人大概读三五分钟,就算一场大批判会。如此演练好了后,就到各生产队去巡回。
我们生产队,当然派的是我去,老农早就知道我在这方面有“能水儿”。
那时候9队派来的是一位回乡知青,女的,是一位很稳重的圆脸姑娘。
她是镇上中学的初中毕业生,模样与气质,都不像是乡下人。有时候宣讲结束,我俩回生产队同路,能边走边聊走上一段。
那女孩很有城府,也很有上进心,所谈的内容都不很俗。我一度对她很感兴趣,可是后来发现,她的感情经历可能比较丰富,不是我这样的单纯小子能匹配的。
在单调的乡村生活中,巡回大批判也是一抹亮色,不亚于今日之选秀活动。我们这个宣讲团,一天跑三个队,所到之处,受到隆重欢迎。现在想想,当然很滑稽,几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每人上台去念一段抄来的稿子,老农就像听圣旨似的听一遍,然后散会。
这样一搞——能多打点儿粮食?能巩固一点儿什么?
都是扯淡。
一次,我和那位9队的女孩同路,聊天中,她忽然说:我妈是台湾人。”
这个背景,让我很惊讶。一个台湾女人,怎么会流落到东北的乡下来?
她没对我做解释。
有一天,我们在大队部集中,准备下生产队去宣讲。正巧遇到两位从北京来外调的警察。“外调”,这也是“文革”用语了,就是对某人的政治历史进行调查,要天南地北的找到相关的证人,出具证明材料。
这俩警察中,有一个较为年轻,说话也幽默。他见我们大队部竟然集中了10个年轻人,看样子都不像是农民,很感意外,便问:你们是知青?
都是本地人吗?”
我们分别报了祖籍,什么江苏、湖北的都有,他说:我说的嘛,打死我也不相信你们是本地人。”
这时候,大队长很得意,就开始吹:我们这地场,连台湾人都有,你信不信?”
大伙知道,他是在说9队的那姑娘。
那警察瞅瞅我们大队长,一撇嘴:“那是啊,林子大了什么鸟儿没有?”我们哄堂大笑。
巡回了三天,大批判结束,我们10个青年都成了朋友。在老农群体中,知青和回乡青年,彼此的认同感最强,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怎么也比一般老农要高一点儿。
过后不久,我听说,“台湾姑娘”把户口转走了。
那时候,城里的工厂,已经开始在下乡知青当中招工了,虽然只是县工厂招人,但能跳出农村挣工资,那就是好。“台湾姑娘”是不甘心一辈子陷在农村里的,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转了户口,把自己的身份改成了下乡知青,以便将来谋个好前途。
我再没见过她,只记得她的颧骨略高,脸蛋红扑扑的,有细细的绒毛,像水蜜桃。她走路很快,性情内敛但骨子里很昂扬。
几十年后,我偶然想到她,觉得她妈妈不可能是台湾女人,很可能是日本女人。
“伪满洲国”的时候,日本曾移民30万到东三省,组建开拓团。抗战结束后,这些日本平民散落在东北没人管,直到1946年夏季起,才被分批遣返回去。
“台湾姑娘”的妈妈,可能就是在1945年的时候,流落到我们那里的,嫁给了农民,“黑”下来了没有走。对外不好说是日本女人,就说是台湾女人。
那么,9队的那姑娘,就应该是半个“日本姑娘”了。改革开放后,也不知她是不是能沾上这个身份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