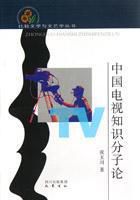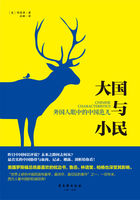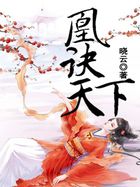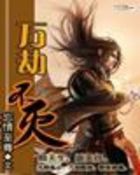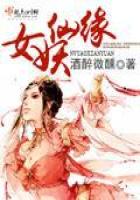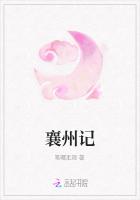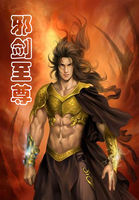由于生长在十兄弟姐妹的大家庭,父母也无法确切地记忆我的出生年月,身份证上写着: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那就姑妄当作自己的生日吧。
但我仍然惶惑,在生活的汪洋大海里载浮载沉地向前凫游。
父亲在世时,是福州一个小手工业者,十口之家,糊口不易。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几乎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我的青少年都是在武夷山下的山城三明度过,那是我永难忘怀的第二故乡。
我自幼酷爱文学,还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动笔“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利用课余和寒暑假断断续续地写了几年,到了高中毕业时,居然写出了洋洋十七八万字的“大作”,书名至今还记得,叫《春阳秋草》。但这部乡巴佬孩子笔下的幼稚之作,竞招来无穷的厄运。
校方没收了书稿,召开批判会,把我当作黑典型,批为“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一本书主义”等等;我升大学之门从此被关闭,差点连高中毕业的一纸文凭也捞不到,幸亏十分疼爱我的语文老师苦苦求情说项,才掮着高中生的牌子离开校门,我永远感激和怀念我的语文老师,她的名字叫:叶素青。
我不想忸忸怩怩地说自己是不想当作家,我的志向就是从事文学写作。只是叹息:人生的道路已经走了一半,我的文学处女地还是一片荒芜,才开出这一星弱小的花。
高中的那一场打击,并未使我文学之梦破灭,也未令我上大学的热望冷却。在“文革”中,虚掷了十年光阴之后,我回到母校任高中语文教师;恢复高考之后,和我的学生一起应试,虽然考了一个很高的总分,但年已而立,又初为人父,真如范进中举,但却无范进的风光,只被录取于一个地区的师范大专,做一名“老童生”。不过,总算过了大学瘾。
1979年秋,移居香港,出于爱好,仍选择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现在香港某大新闻机构任编辑,业余坚持“爬格子”。这本小册子里所收的,便是几年来“爬格子”的业绩。
说起来,我练习写作的时间不算短,14岁时已在报上发表文字了,那时用的是“巴童”笔名,意为:乡巴佬的孩子。现在改为“巴桐”,是因为年龄不小了,也为了自勉,希望能像梧桐树一样成长起来,不要老没长进。因此,“童”字也就变成了“桐”,取其谐音。
末了,我要衷心地感谢海峡文艺出版社对我的关怀和爱护,让这本小书得以面世;同时感谢宋祝平先生为小书作了序;还要感谢香港知名老作家曾敏之先生,他为这本书取了名。
要感谢的太多,最终要感谢的是读者,蒙您的不弃,这本小书才摊在您的面前,让我们藉着文字神交,作心灵上的沟通。
散文集《香岛散记》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