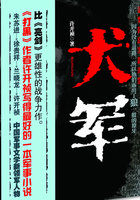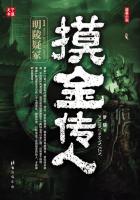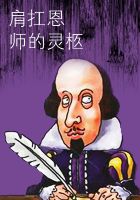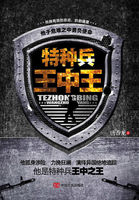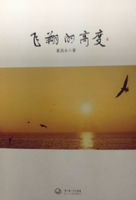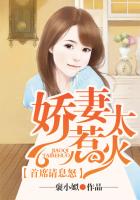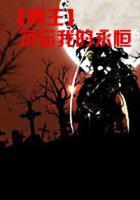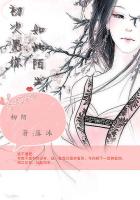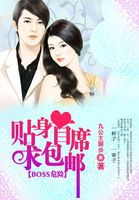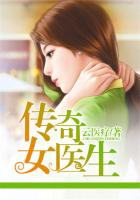坯王自从认识了杏儿,心里再也搁不下旁人了。坯王想,有了杏儿,这辈子算没白活。等忙过这阵子,就央人到杏儿家提亲,把娘留下的那支凤头金钗送给杏儿做聘礼。
这天夜里,坯王大柱静静地躺在炕上,两手交叉枕在脑后,想着杏儿要是把辫子盘成发髻,再插上金钗和红绒花该是什么模样啊。忽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大柱忙起身开门,杏儿跌跌撞撞地进来,抱住大柱就哭,坯王慌乱不堪。
上弦月,像美人盈盈含笑的嘴角。今夜,因了这弯月,星空没心没肺地乐成了一朵花,它对杏儿大柱的愁苦浑然不觉……杏儿离去时,把两条乌黑的发辫齐根铰下留给了坯王。
一所崭新的土坯房远离镇子,孤零零地立在南岸的柳树下,大柱从此不再帮人脱坯,整日待在坯屋里。有人在夜间见过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问他,也不答话,只痴痴地望着远处。那里,有璀璨撩人的光,是城里的灯,杏儿住那儿。
来年八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塌了不少房屋,可相思古镇南岸那座土坯房却完好无损。据说,大柱在脱坯时,把杏儿的青丝剪碎搅和在土中,每一块儿土坯都散发着杏儿的气息。
如今,坯屋尚在,坯王不知去向……
祭秋
红酒
缨子紧紧地拽着娘的衣襟走在十月的旷野里。
相思镇田里的秋庄稼都拾掇完了,褐色的土地像赤裸着胸膛的汉子,唯有一棵枯黄的高粱傲然挺立在地中央。一阵秋风吹过,黄叶簌簌,似在诉说着什么。
地头开有一簇黄莹莹的野菊花,缨子松开娘的衣襟,快步上前齐根儿掐断,又飞快地跑到那株枯黄的高粱前,刚要动手折,却被娘厉声喝住了。
为什么呀娘?缨子委屈地问。
娘说,独独留一棵庄稼在田里是有说头的,那叫祭秋,祈求来年五谷丰登,人丁兴旺。
哦,祭秋……缨子好像明白了。
那个妖精呢?娘突然问。
娘只要说起金雀儿,历来就是这个称呼。
缨子跟爹在城里读书,心里有一百个不乐意,又不敢跟爹娘说。娘死活不去城里住,说是不想看那个妖精。
金雀儿没给缨子爹做小前是个唱眉户的戏子,好歹也算是个角儿,演过《张古董借妻》里的沈赛花。戏里的赛花女本是有夫之妇,被秀才李成龙借去哄骗老丈人家的财宝,不想弄假成真确确实实做了秀才娘子。戏外的金雀儿却被在县衙做事的缨子爹一眼相中做了二房。
缨子爹本无心娶小,只是缨子娘有了缨子以后多年不再生养,缨子爹说,丫头片子终归要嫁人,百年后连个打幡摔老盆的人都没,还不叫族里人笑掉大牙?
金雀儿被收房后便不再唱戏,跟缨子爹住在城东一处宅子里。缨子被爹接进城读书的那天清晨,金雀儿早早起床做饭。别看她自小跟班唱戏,却也做得一手好茶饭。时候不大,桂圆红枣粥,红豆冰糖馅儿馍馍,细细的咸菜丝儿就端上了桌。缨子坐在炕沿上,一句话也不说,大眼睛追着金雀儿的身影转。
金雀儿比娘年轻多了,穿碎花布旗袍,琵琶扣,小圆口绣花鞋,走路轻轻地像在云彩里飘。缨子心说,她就是比娘的腰细些,会打扮些,可不如娘好看,她脸上有浅浅的雀斑呢,别以为旁人看不出来!
缨子吃饭了……正出神想心事的缨子吓一跳。看着金雀儿递过来的青花瓷碗,欲伸手接时,却瞟见她白嫩嫩的胳膊上有一道一道的血痕,结着褐色的痂。缨子吃惊地瞪大眼睛,突然觉得恶心,起身抓起书包一溜烟儿跑了。金雀儿一手端碗一手拿筷子追到大门口,没追上,摇摇头,叹口气,怏怏而回,不知这孩子怎么了。
缨子爹寡言少语,忙完公务回到家中,一进门先把头上的礼帽摘下递给金雀儿,接了她递过来的手巾擦脸擦手后就坐下咕嘟咕嘟抽水烟儿,眼皮也不抬。再不就是撩起大褂快步走到当院里的那株石榴树旁,对着鸟笼里蹿上蹿下的画眉子发呆。每逢这个时候,缨子会轻手轻脚沿着墙根儿溜进西厢房内,摊开书本温习功课,耳朵却听着外面的动静。姨娘金雀儿扎上个蓝花围裙,挽起衣袖忙着生火做饭。如果不是风箱啪嗒啪嗒响的话,这所青砖黛瓦的小院就死一般的沉寂。
学堂放假了,缨子被爹送回相思镇。缨子娘围着女儿问长问短问东问西,最后的话题总会落在姨娘身上。
那个妖精待你好不好?待你爹好不好?缨子娘一连串地发问。
缨子说,别的都好,就是金雀儿姨做的饭我不想吃。缨子从不叫金雀儿姨娘。
娘仔细端详着缨子说,我家缨子果然瘦了,脸尖得像我纺出来的棉线穗。
缨子接了娘递过来的糖水蛋,嘴角一撇,说,她胳膊上总有血,一道一道的,真脏。
缨子娘闻言,一怔,不再言语了。
姨娘金雀儿是关中人,自小被卖进戏班子,几乎和家里断了来往。有时金雀儿也会倚院门站着,偶尔听见有关中口音的人就会招呼人家来屋坐坐,东绕西拐,变着法打听娘家的消息。
小院儿里的石榴花红灿灿地晃人眼,金雀儿在这个院子里不知不觉也住满两年了。两年里,金雀儿一点没变,走路还是轻飘飘地似在云彩里飘,腰还是细得一扎就能握住。缨子爹越发沉默寡言,脸上能拧下水来,动不动就回乡下住,把金雀儿和缨子留在小院里。
金雀儿开始频繁地找郎中把脉,吃完汤药吃丸药,吃完丸药吃膏方,把个小院折腾得像个中药铺,就连画眉子的叫声也弥漫着浓重的药味儿。
傍晚,隔壁李二婶送过来几个红柿,缨子贪吃坏了肚子,晚上起夜时,听见姨娘房中有动静,缨子敛声屏息听了一会儿,像是哭声,低低抽泣,很压抑的样子。缨子就在窗外叫,姨,你哪不舒服?金雀儿没回答,房里却没了声息,缨子讪讪回到西厢房。
次日清晨吃饭时,缨子又问。金雀儿说,缨子你发癔症吧?缨子越发奇怪,大人们的事真让人不明白,哭就哭了呗,还不愿承认,真是的。
缨子爹回来了,娘也来了。娘是第一次踏进这个小院,金雀儿乱了方寸,赶紧拢了拢头发跑出来,低眉顺眼站在一旁。缨子娘也没看她,只是拉着缨子进了上房。
夜里,缨子娘熄了灯,坐在炕上搂着缨子,也不说话,偶尔往对面屋看一眼,又看一眼。缨子爹和金雀儿不知在说些什么,身影映在窗棂上,像皮影戏里的人儿,很晚很晚,灯才熄掉。
太阳露了头,画眉子叫得正欢,缨子娘把六个银圆硬塞到金雀儿的蓝布包袱里,拉起缨子随着金雀儿向外走。
深秋时分,通往关中的那条官道上几乎没有行人,雾气氤氲中,金雀儿挎着那个蓝布包袱急急地走着,羸弱的身影像田里那株枯黄的高粱……
缨子小声问,娘,那妖精还回来不?
娘劈头给了缨子一巴掌,厉声说,少家失教的丫头,那是你姨娘!
茹先生
红酒
相思古镇只有一个剪头理发的铺子,叫茹先生修面铺。
开修面铺的茹先生却是个女的。茹先生年近四十,少言寡语,瘦高条个儿,白净脸,长得蛮清爽。在女人眼中,茹先生长得中规中矩,不妖不媚。茹先生本人的发型怎么看都像是三四十年代的明星,镇子上的女人只是在画上见过,眼热得不得了。
修面铺开在镇子东头古槐树旁边,门前是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两边全用青石砌就,留有一级一级的台阶。镇子上的人感到奇怪,理发不叫理发叫修面,茹先生不是先生居然还叫茹先生,搞不懂了。越是搞不懂就越想搞懂,相思古镇的人们没少费琢磨。
琢磨归琢磨,可不耽误上门来收拾头发。男人们对修面铺里可以转圈儿的皮椅子最感兴趣,坐上去软活活的,像躺在暄暄乎乎的棉花垛上。女人们三三两两地下河淘菜洗衣,茹先生修面铺的大门正好对着那台阶,女人们洗衣时也能忙中偷闲朝她那里瞄上几眼。
茹先生不苟言笑,只一句“侬来了”就缄口不语了,铺子里多热闹跟她没关系,她只是专心做活。若把手头的活计做停当了,就拿面镜子放人身后左照右看,客人没不满意的。这时,茹先生嘴角才会浮起一丝笑意,抖抖手中的围布,软软地说:下一个。脸上的笑意便收回酒窝里了。
相思镇的爷们儿来剃光头,茹先生手中那把明光锃亮如月牙般的剃刀就有了灵气,上下翻飞极富节奏。茹先生剃头不像其他人那样搬着你的头摁来摆去,让人憋屈。她给人剃头时,或高或低都是调整自己的姿势,有时还半蹲着做活。头剃干净了接着刮脸,全套活做下来,不多不少九九八十一刀,有人专门数过。还说剃头这手艺看似“毫末技艺”,却是“头顶功夫”,茹先生手艺精湛,做活时不急不躁,颇有高手风范呢。
茹先生微微一笑,轻轻摇头,一句“谢谢侬”就再没话了。手下却不停歇,一条热毛巾捂住头,待头皮捂热,再用十指按压轻拍,那舒坦都沁到骨子缝儿里了。
茹先生给人剃头修面不论价钱,你随便给,钱也行,物也中。有一家子来理发,孩子就抱着只鸡过来。
镇上有个叫黑虎的,一脸络腮胡子,常常干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勾当,换了钱就去喝酒赌博,谁拿他也没辙。黑虎也是茹先生修面铺的常客,拾掇完了拍拍屁股走人,从不付账。茹先生也不计较,照样认认真真地给他剃头刮脸。有人看不过,出来打抱不平。黑虎就耍横,说,怎么着?剃个头算个
呀?茹先生儒雅地摆摆手,说乡里乡亲,和气生财。
好像谁也没问过茹先生为什么一人生活,茹先生也从不讲自己的身世。有好事的主儿就去给茹先生做媒人。茹先生笑笑,摆摆手:不当真,不当真。也有人说茹先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上海滩十里洋场混过码头,还说她家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夕跑台湾去了,她就投靠远房亲戚来到了相思镇。理发时有人搬出传闻来求证,茹先生还是淡然一笑,摆摆手:不当真,不当真。
镇子上的古槐开花时,一场运动也闹腾得如火如荼。黑虎领一帮痞子孩儿胳臂上戴个红箍箍就成了风云人物,他们把茹先生的铺子砸了,说修面修的是修正主义的面子,说茹先生是大军阀的小老婆,挂着牌子游街,还给她剃了阴阳头。
白天游街,晚上,茹先生用蓝花布裹住头,照样给人剃头刮脸。
黑虎听说了,晚上也领人开茹先生的批斗会。筋疲力尽的茹先生在回家的路上不慎摔进沟里,双腿骨折,再也没能站起来。
黑虎他爹卧床两年,形容枯槁,发乱须结,三伏天撒手人寰,老人留下话说要把自己收拾干净再走。黑虎整天作怪不干好事,谁愿意上门来伺候个死人?黑虎他娘哭着骂黑虎,一家人手足无措。
门推开了,茹先生被人背着进了黑虎家。
茹先生开始给老人剃头刮脸。腿断了,不方便,她就让人把老人上半身抬起,放自己怀里理发。大热天,停放两天的老人已有了异味,茹先生全然不顾,聚精会神,剃头修面,不多不少还是九九八十一下,同样用热毛巾捂头,十指在头部摁压轻拍,一丝不苟。全套活做完,茹先生浑身上下像水浇了一般。
黑虎“扑通”跪在茹先生面前,把头磕得砰砰响。
送走了爹,黑虎负荆请罪,到茹先生屋里跪着哭着要学修面。茹先生不放话,黑虎就跪一天。第二天,黑虎接着跪……后来也说不清茹先生到底收了黑虎没,反正黑虎见天在茹先生身边伺候着,背着茹先生走街串巷给人剃头修面。
茹先生去世时,黑虎披麻戴孝,亲自为茹先生净面剪发。
黑虎的剃头铺子开张了,还叫:茹先生修面铺。
箍大的
陈敏
这是我爷爷讲的一个真实故事。
一天,村子里传来了箍匠的吆喝声:“箍大的吆!箍大的!——当——”声音古老而苍茫,随着悠扬的铜锣声盘旋在小镇上空。镇里人闻声后知道箍匠来了,便纷纷搬出破锅烂盆和破损的缸缸坛坛、木桶、陶罐让箍匠修补。
而箍匠呢,和以往的箍匠大不相同,像是跟人玩捉迷藏似的,让人只闻其声,难见其容。在闹哄哄的街市或小镇的桥头,冷不丁地吆喝一声,让人难觅踪影。河东人听那声音来自河西,河西人听见声音来自河东。
走街串户的箍匠多以修理瓢盆桶碗等小件什物为主,而那个箍匠只喊着:“箍大的。”这大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有多大?有嗓门高的人,追上一句,朝着那个声音询问:“箍盆箍桶吗?”箍匠没有回音,又问,“箍碗吗?”吆喝声便随之消失了。
“箍大的——”喊声时而传来,又时而消隐。有时,好几天也不闻其声。不过,也有人说自己亲眼见过那个箍匠。箍匠年纪大约三十四五,挑着担子,扁担的一头是带有抽屉的小木柜。柜上放着弓子,上方的支架用铁链挂着一面小铜锣,两边各有一个小锤,走起路来,小锤敲打着铜锣叮当作响。
箍匠的叫喊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同样是那句“箍大的——”,那声音连同箍匠一起被一个归家的秀才碰了个正着。秀才见到箍匠顿时来了气,也没好言语,气冲冲地顶了句:“箍大的,箍大的,有本事你怎么不去箍丰阳塔呢?丰阳塔倒是个大东西。”
秀才轻蔑地哼了一声,甩袖而去。
丰阳塔位于镇东头的草庙坡上,建于唐朝,经历了千年风雨。可有一年夏天,来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雨,大雨倾盆,火光冲天,天空传来吱吱的龙叫声。突然,一个炸雷骤然响起,一条火龙从天而降,把古塔顶炸出了一个豁口。村里上了岁数的人说,古塔原有九层,后只剩下了八层,最上面的那层被雷抓走了,抓到了三百里以外的黑女潭。黑女潭出了一个女妖。女妖兴风作浪,祸害百姓,龙王把丰阳塔顶抓去,立在潭边,降住了女妖。丰阳塔顶除了留下一个缺口外,塔体上还烙下了一道龙爪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