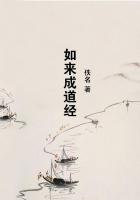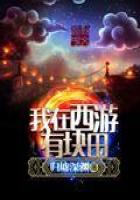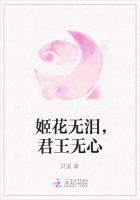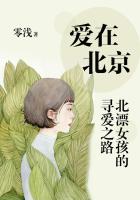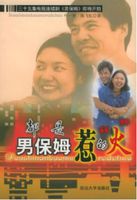前言
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於湛者,或卒业於王,学於王者,或卒业於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
文简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从学于白沙,不赴计偕,后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枫山试睟面盎背论,奇之。登弘治乙丑进士第。初杨文忠、张东白在闱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为也。”拆名果然。选庶吉士,擢编修。时阳明在吏部讲学,先生与吕仲木和之。久之,使安南册封国王。正德丁亥,奉母丧归,庐墓三年。卜西樵为讲舍,士子来学者先令习礼,然后听讲,兴起者甚众。嘉靖初,入朝,陞侍读,寻陞南京祭酒,礼部侍郎,历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致仕。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犹为南岳之游。将过江右,邹东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来,吾辈当献老而不乞言,毋有所轻论辩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
先生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良知之学,各立门户。其间为之调人者,谓“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何异?何同?”然先生论格物,条阳明之说四不可。阳明亦言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是终不可强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谓阳明训格为正,训物为念头,格物是正念头也,苟不加学问思辨行之功,则念头之正否未可据。夫阳明之正念头,致其知也,非学问思辨行何以为致?此不足为阳明格物之说病。先生以为心体万物而不遗,阳明但指腔子里以为心,故有是内而非外之诮。然天地万物之理,不外於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若以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万物以为广大,则先生仍为旧说所拘也。天理无处而心其处,心无处而寂然未发者其处,寂然不动,感即在寂之中,则体认者亦唯体认之於寂而已。今曰随处体认,无乃体认於感?其言终觉有病也。
心性图说
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心也而不遗者,体天地万物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发,未发故浑然而不可见;及其发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发见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惧慎独以养其中也。中立而和发焉,万事万化自此焉,达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归之者耳。终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无所不贯也。”“何以大圈?”曰:“心无所不包也。”包与贯,实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物以为心者,小之为心也甚矣。(略图)
上下四方之宇
心(始敬)>性(未发之中)>情(已发之中):仁、义、礼、智之端>万事万物天地>心(终敬)
古今往来之宙
求放心篇
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观吾心於无物之先矣,洞然而虚,昭然而灵。虚者心之所以生也,灵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观吾心於有物之后矣,窒然而塞,愦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虚焉灵焉,非由外来也,其本体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内往也,欲蔽之也。其本体固在也,一朝而觉焉,蔽者彻,虚而灵者见矣。日月蔽于云,非无日月也,镜蔽於尘,非无明也,人心蔽於物,非无虚与灵也。心体物而不遗,无内外,无终始,无所放处,亦无所放时,其本体也。信斯言也,当其放於外,何者在内?当其放於前,何者在后?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为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祇益乱耳,况能有存耶?故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
论学书
格物之义,以物为心意之所着。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於外,故有是说。不肖则以为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体,心体物而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为心意之著见,恐不免有外物之疾。(《与阳明》)
学无难易,要在察见天理,知天之所为如是,涵养变化气质,以至光大尔,非杜撰以相罔也。於夫子川上之叹,子思鸢鱼之说,及《易》大人者天地合德处见之,若非一理同体,何以云然?故见此者谓之见《易》,知此者谓之知道。是皆发见於日用事物之间,流行不息,百姓日用不知,要在学者察识之耳。涵养此知识,要在主敬,无间动静也。(《寄王纯甫》)
学者之病,全在三截两截,不成片段,静坐时自静坐,读书时又自读书,酬应时又自酬应,如人身血气不通,安得长进?元来只是敬上理会未透,故未有得力处,又或以内外为二而离之。吾人切要,只於执事敬用功,自独处以至读书酬应,无非此意,一以贯之,内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开物成务之学,异于佛老者,此也。(《答徐曰仁》)
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宇宙间只是一气充塞流行,与道为体,何莫非有?何空之云?虽天地弊坏,人物消尽,而此气此道,亦未尝亡,则未尝空也。(《寄阳明》)
古之论学,未有以静为言者。以静为言者,皆禅也。故孔门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动静着力。何者?静不可以致力,才致力,即已非静矣。故《论语》曰:“执事敬。”《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惧慎独,皆动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静不可见,苟求之静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灭之中矣。故善学者,必令动静一於敬,敬立而动静浑矣。此合内外之道也。(《答余督学》)
从事学问,则心不外驰,即所以求放心。如子夏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仁在其中者,非谓学问之外,而别求心於虚无也。(《答仲鶡》)
心存则有主,有主则物不入,不入则血气矜忿窒碍之病,皆不为之害矣。大抵至紧要处,在执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树根着土,则风雨雷霆,莫非发生。此心有主,则书册山水酬应,皆吾致力涵养之地,而血气矜忿窒碍,久将自消融矣。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如车两轮。夫车两轮同一车也,行则俱行,岂容有二?而谓有二者,非知程学者也。鄙见以为如人行路,足目一时俱到,涵养进学,岂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为讲习之际,涵养致知,一时俱到,乃为善学也。故程子曰:“学在知所有,养所有。”
朱元晦初见延平,甚爱程子浑然同体之说。延平语云:“要见理一处却不难,只分殊处却难,又是一场锻炼也。”愚以为,未知分殊,则亦未知理一也,未知理一,亦未必知分殊也,二者同体故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所以体夫此也。敬义无内外也,皆心也,而云内外者,为直方言之耳。(以上《答陈惟浚》)
执事敬,最是切要,彻上彻下,一了百了,致知涵养,此其地也。所谓致知涵养者,察见天理而存之也,非二事也。(《答邓瞻兄弟》)
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穷索?”须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实地。首言“识得此意,以诚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进,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终又云:“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见得这头脑,亲切存之,自不费力耳。(《答方西樵》)
夫学不过知行,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说命》曰:“学於古训乃有获,知之非艰,行之唯艰。”《中庸》必先学问思辨,而后笃行。《论语》先博文而后约礼。《孟子》知性而后养性。始条理者知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程子知所有而养所有,先识仁而以诚敬存之。若仆之愚见,则於圣贤常格内寻下手,庶有自得处。故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则知行并进矣。(《答顾箬溪》)
道无内外,内外一道也;心无动静,动静一心也。故知动静之皆心,则内外一。内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内外,混动静,则澄然无事,而后能止。故《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止之道也,夫“不获其身”,必有获也,“不见其人”,必有见也,言有主也,夫然后能止。(《复王宜学》)
夫所谓支离者,二之之谓也。非徒逐外而忘内谓之支离,是内而非外者亦谓之支离,过犹不及耳。必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一以贯之,乃可免此。(《答阳明》)
夫学以立志为先,以知本为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真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于圣学思过半矣。夫学问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则志立,志立则心不放,心不放则性可复,性复则分定,分定则於忧怒之来,无所累于心性,无累斯无事矣。苟无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则情炽而益凿其性,性凿则忧怒之累无穷矣。(《答郑启范》)
格者,至也,即格於文祖、有苗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诣之义,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进,学问思辨行,所以造道也,故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求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诚、正、修工夫,皆于格物上用,家国天下皆即此扩充,无两段工夫,此即所谓止至善。尝谓止至善,则明德、亲民皆了者,此也。如此方可讲知至。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谓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谓也;居安、资深、逢源,即修、齐、治、平之谓也。(《答阳明》)
夫至虚者心也,非性之体也。性无虚实,说甚灵耀?心具生理,故谓之性;性触物而发,故谓之情;发而中正,故谓之真情,否则伪矣。道也者,中正之理也,其情发於人伦日用,不失其中正焉,则道矣。勿忘勿助,其间则中正处也,此正情复性之道也。(《复郑启范》)
慎独格物,其实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学问思辨行,所以至之也,是谓以身至之也。所谓穷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远而天下,暂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体认天理而存之也。(《答陈宗亨》)
所云主一,是主一个中,与主一是主天理之说相类。然主一,便是无一物,若主中主天理,则又多了中与天理,即是二矣。但主一,则中与天理自在其中矣。(《答邓恪昭》)
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古之欲明明德二节,反复推到格物上,意心身都来格物上用功。上文知止定安,即其功也。家国天下皆在内,元是一段工夫,合外内之道,更无七段八段。格物者,即至其理也,意心身与家国天下,随处体认天理也。所谓至者,意心身至之也,世以想像记诵为穷理者,远矣。(《寄陈惟浚》)
集者,如虚集之集,能主敬,则众善归焉。勿忘勿助,敬之谓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即精一工夫。若寻常所谓集者,乃於事事上集,无乃义袭耶?此内外之辨也。然能主敬,则事事无不在矣。今更无别法,只于勿忘勿助之间调停为紧要耳。(《答问集义》)
本末只是一气,扩充此生意,在心为明德,在事为亲民,非谓静坐而明德,及长,然后应事以亲民也。一日之间,开眼便是,应事即亲民。自宋来儒者多分两段,以此多陷支离。自少而长,岂有不应事者?应事而为枝叶,皆是一气扩充。(《答陈康涯》)
天地至虚而已,虚则动静皆虚,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静言。
虚实同体也,佛氏歧而二之,已不识性,且求去根尘,非得真虚也。世儒以佛氏为虚无,乌足以及此。
格物即止至善也,圣贤非有二事。自意心身至家国天下,无非随处体认天理,体认天理,即格物也。盖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为之著,无非用力处也。阳明格物之说,以为正念头,既於后面正心之说为赘,又况如佛老之学,皆自以为正念头矣。因无学问思辨行功,随处体认之实,遂并与其所谓正者一齐错了。(以上《答王宜学》)
阳明谓随处体认天理,是求於外。若然,则告子“义外”之说为是,而孟子“长之者义乎”之说为非,孔子“执事敬”之教为欺我矣!程子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格物是也,更无内外。盖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为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答杨少默》)
以随处体认为求之于外者,非也。心与事应,然后天理见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来,随感而应耳。故事物之来,体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则天理矣。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宇宙内即与人不是二物,故宇宙内无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
云“敬者心在于事而不放之谓”,此恐未尽程子云“主一之谓敬”。主一者,心中无有一物也,故云一,若有一物则二矣。勿忘勿助之间,乃是一,今云“心在于是而不放”,谓之勿忘则可矣,恐不能不滞于此事,则不能不助也,可谓之敬乎?
程子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故古本以修身说格物。今云“格物者,事当於理之谓也”,不若云“随处体认天理之尽也”。体认兼知行也。当於理,是格物后事,故曰“格物而后知至”。云“敬而后当於理”,敬是格物工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