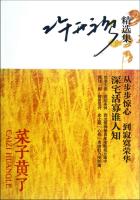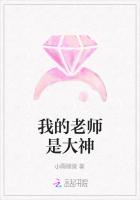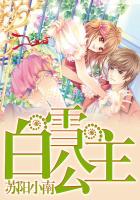她们俩商量好了为父母请来一个可靠的保姆后,于1998年3月18日一道携着两个人共同的女儿谢金莹(她俩给女儿重新取名)南下深圳华安学校。
华安学校是一所平民学校,是专门招收那些打工子弟和流动人口子弟的学校,尽管学校目前规模不大,小学一至六年级仅有160多名学生,但这里收费低廉,甚至为贫困学生免费,还特招了一些孤残弃儿,且又能保证教学质量,学校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和支持。
谢真在学校里日夜拼命工作,当她升任为主管业务的副校长后,仍然不忘社会上那些下岗困难的同胞姐妹,她在深圳和武汉公开招聘了20多名下岗女工来学校工作。
而今,谢真有了秋萍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在事业上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姐妹,她决心和秋萍一道共同创业,将华安学校越办越红火。
女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
女人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
女人婚姻不幸想离而离不了的时候
女人离婚后走投无路的时候
她们除了依靠法律外
还可以走进——
女子婚姻驿站
“新太阳女子婚姻驿站”创办以来,颇受人们关注,虽然它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女子婚姻避难所”等民间机构晚创办了许多年,但它毕竟作为我国首家民间妇女保护所诞生了,它成立至今,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心和支持,也成了近期的一个新闻焦点。
“新太阳女子婚姻驿站”站长张先芬在历经三次曲折坎坷的离婚之后,立志创办此站。她的生活经历与人生道路本身就是一部女性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弱女子蹒跚在艰难的人生路上
1948年,张先芬出生在湖北省嘉鱼县簰州镇。
父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高材生,武汉被日本占领后,父亲回乡当了名医生。张先芬四岁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母亲为了张先芬和弟弟的前途,带着他俩来到武钢与一工人组成新家。
八年后生父刑满释放。生父将张先芬接回乡下,与继母生活在一起。12岁的张先芬辍学在家洗衣、做饭、种菜、捡柴禾,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三年自然灾害,村子里许多人活活饿死,张先芬却顽强地活了下来。
当父母买下两间养蜂场将留下的破茅房给张先芬后,张先芬就开始独立谋生。
13岁的张先芬与村里成年妇女一道割谷、插秧、锄草、挑粪……每到夜深人静,她就想念远在武汉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妹。她经常给母亲和弟妹写信。
信寄多了,没钱,就托人捎信,当她听捎信的人说自己的信能带给母亲和弟妹欢乐与安慰时,她的信写得就更勤了。
14岁时,她将自己种的蔬菜、养的鸡鸭、收的大米干菜积起来,起早贪黑步行100多里路送到生母的家,帮生母渡过生活难关。
两年后,“文革”开始,生父被迫害致死,留下孤零零的张先芬独自谋生。
20岁那年,村里同龄女孩都出嫁了,她成了村里的“老姑娘”。
就在这年,“四清”工作组组长与她相恋,组长为了自己的仕途抛弃她时,她在初恋失败的极度痛苦中投河自杀,幸而被人救起。
生母可怜女儿,将女儿接回武汉。张先芬靠在江汉一桥帮车夫拉车上桥一趟得五分钱、帮人洗一床被子得3分钱谋生。
张先芬是“黑户口”,没有工作,出身“反革命”,经常遭受被遣送回乡的痛苦。
母亲为了她能在武汉安身,就四处托人说媒,对女婿什么条件也不讲,只要能娶女儿就行。张先芬走投无路时匆匆嫁给了比自己年长15岁的丈夫。
婚后,她心头仍是沉甸甸的:没有城市户口,出身“反革命”,是找上门的媳妇;丈夫的家人怨她骂她冷落她歧视她;街坊邻里也另眼看她。
她整天呆在家里苦闷而孤独。她给人当保姆带孩子,每月挣10元钱补贴家里。
自己有了两个孩子后,日子更艰难了。她找到省公路局做泥瓦工,每天将大孩子锁在家里,抱着小孩子到工地筛沙、和灰、拖砖、提泥桶,挣得几个微薄的临时工工资糊口。
日子久了,夫妻性格与感情越来越不和,张先芬经济能够独立时,便提出离婚。
离婚时,她已是30岁的女人了,为了求知,自学一门技术,她从识钟表查字典开始,与两个孩子一道从小学课本学起。她先后学过缝纫,学过无线电修理,也曾卖稀饭赚钱报考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