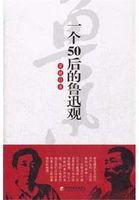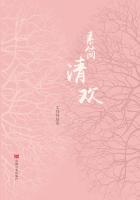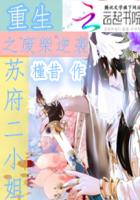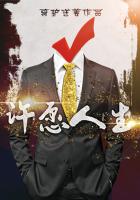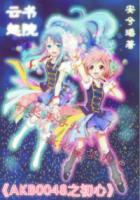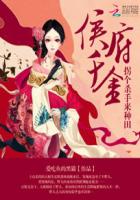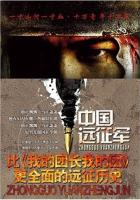不是所有的泥瓦匠都能胜任打灶头这门绝活的。在我们乡下,“砌”字经常被“打”字所代替。我们将砌墙,砌灶头称呼为打墙、打灶头。家境尚为殷实的人家,每隔两三年就要重新打一回灶头。家主必定想方设法延请附近稍稍有点名气的泥瓦匠。有经验的泥瓦匠打出来的灶头就是不一样——火旺,烟少,省柴火。铁镬子与灶肚的边缘贴得密实,青烟轻易不会蹿将出来。新灶头打得相当饱满,又高低适度,自会赢得主妇的欢心——这些当然是从老灶头的实用性能来说的。那些缓慢的年月,灶头除了管住我们的一日三餐之外,还管我们的审美——我的一丁点儿民间绘画的知识,基本上也是从灶头上得来的。一个新的灶头打好了——我是说它相当饱满地站立在我们的厨房里了,并且已经被石灰泥粉白了,它像模像样了——还不能算是最后的完成。打灶头的最后一关是描画——在灶头的白粉墙上画上民间的吉祥图案,这活儿凭的不是蛮力,而是巧思——这也是最容易让泥瓦匠出名,最能看出泥瓦匠师傅能工巧匠的一刻——他磨起了墨,他取出了墨笔,在砚台里蘸一蘸,甩开手腕,在灶头的右边位子拉了一条笔直的线——然后让笔底的文字紧紧地抱住这条直线——那是传统的“米中用水”四个字,其中的那一条直线就成了这四个字的中间的公用部分。每次看到泥瓦匠完成这一个小小的巧思,我们总是在一旁小声喝彩。接着,泥瓦匠师傅用朱砂在灶头的中间画下一条欢蹦乱跳的鲤鱼——实际上只画下一个高高翘起的尾巴和一张张开的鱼嘴——鲤鱼的两根须还在微微颤抖。至于鲤鱼的本身,那是用不着画的,它隐藏在灶头中间凹下的半圆形里去了。鲤鱼的身体部分完全保存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也因此,这条传说中的鲤鱼始终是鲜活的,半完成的。它的大小也长年累月地考验着我们的想像力——鲤鱼是一个积极上进的民间符号,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在中国民间妇孺皆知。这虚幻的一笔,既是一个隐喻,又可以看出民间匠人构思的巧妙。有些有绘画天赋的泥瓦匠师傅,很会考虑图画的布局,给老灶头的勾边也极为讲究,笔底,线条率真、稚拙,一丝不苟,如丝如缕。那些在乡间极少一展才华的泥瓦匠乘着打灶头的那一刻,会将细密的心思,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全部放入到虚实相间的图画里去——灶头上不仅画有腊梅、松柏等传统的花卉植物,还画着仙鹤、喜鹊等吉祥的飞禽。我曾看到有户人家的灶头画,精美得让我差点儿认为是专业画师所为——在某户人家的一口超大型老灶头上,我甚至看到一只栩栩如生的猛虎,正威武凶猛地踱步下山……这些无名的工匠,在打造一个个老灶头时,仿佛也在打造自己的一颗爱美的心灵。这些自生自灭的民间美术作品,从未具上作者的姓名,它们无名地生成,又无名地消失——在默默无闻的民间,在一个宽容和满不在乎的民间,在一个缓慢的民间……
芝麻总是被当作一个转喻来使用……芝麻的小太有名了,以至早于我的想法收入了一部成语词典。至于我将它收入我的《江南词典》,我想我一定是在向世间所有的小事物致以一个诗人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