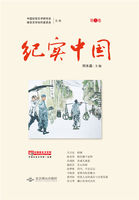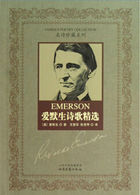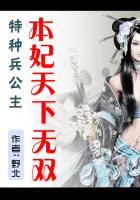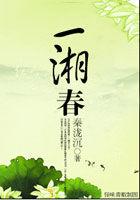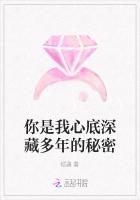正如鼓点属于北方的山峦、大漠、长河,月琴的喑哑之声天生就应该飘忽在江南的水面上。这种朴素到可以不上油漆的乐器,大概就是为了江南贫血的女人、垂柳、残月、断了一角的凉亭、有着冗长水袖的越剧等等事物而发明的。从形状上看,月琴的肚子特别大,丰满如一轮满月;月琴的脖子细而且长,令人遐想和怜惜。月琴的三根弦居然能弹出那么多丰富的乐音,这是五音不全的我万难理解的。月琴的声音里有一种苍白的语调,它精粹的嗓子里满是单一、凄凉、悲苦,仿佛月光底下一个匆匆赶夜路的异乡人发出的叹息。很好笑,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三根弦的乐器,以为它就是三弦,就是早年的沈尹默在一首诗歌里吟唱过的那一种东西。其实,三弦是三弦,月琴是月琴,是同一个乐器家族里流着同一种血液却素无往来的两门穷亲戚。和三弦一样,随便在哪个乐队中,月琴谦卑到都可以放弃自己的形状,放弃自己的性格,完全消隐在无名之中。但是,当月琴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无论它在哪个角落,我都能区分得清清楚楚。三弦、月琴、二胡,它们都是为了江南而存在的,它们的声音之所以存在,完全是为了证实这个世界里我们所受的苦——代替世界上无数的肉嗓子给喊了出来。所以,我也许可以这样说,月琴就是民间性情的绝响,是山歌一类毫不做作、毫不虚伪的东西。它的声音是做不得假的,正如一个人负重时本能发出的声音。它的声音又是可以自娱自乐、自己减轻灵魂重负的——上世纪整个九十年代,我在我老家石门北边的一所乡村中学里谋生,每到中午休息时间,在底楼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代课老师操起一把木质发白的月琴,擦干净,调试好,接着,声音就开始响彻整座校园。有时候,学校里一位年轻的数学兼音乐女教师主动走到他身边,放出柔美的嗓子伴唱,唱的是越剧,唱腔平和,缠绵,婉转,清越;月琴的伴音细脆,尖锐,急速,好像一个一个感叹号,准确地点在那些著名的唱词上。这一老一少,这一男一女,这月琴,这越剧,在那些秋高气爽的午后,在这桐乡最偏僻的乡村中学里,是我此生再难听得的美声。
在露天电影场上看这出越剧,我还有了一个重要的收获,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个标准的美女形象——王文娟扮演的凄美绝伦的林黛玉——这个形象延伸到好多年之后,还以年画的形式张贴在我家厢房的白粉墙上——她陪伴我度过了孤寂和禁欲的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