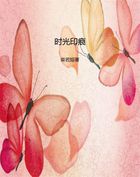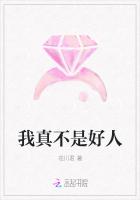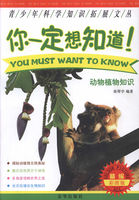秋风一紧,草木凋零。地上枯黄的杂草已经明显地矮下去。似乎这卑微的小草也懂得了谦让——就这样大大方方地给蟋蟀让出一条道来——说白了,是给蟋蟀好听的声音让出一条道道来。在我,蟋蟀这小虫子是因其鸣声感人而从小记在心上的。所谓“趋促鸣,懒妇惊”,蟋蟀的声音,按照晋代陆机抄录的这条当时的顺口溜,听着是连懒妇也会悚然起惊的。想来蟋蟀的鸣声一起,寒冬追着脚后跟也就快到了。寒意逼人,家里的懒妇不得不动手缝制过冬的衣裳。加之蟋蟀的叫声缠绵悱恻,凄清异常,懒妇或离人动点感情自然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蟋蟀可以说是最早记入方块文字的一只名虫子。诗三百篇,多有歌吟。《豳风·七月》一篇,更是大书特书。早年我读“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怎么也搞不懂月份后面两个字的意思,后来读历代注解,才知“斯螽”、“莎鸡”云云,不过是蟋蟀众多别名中的两个,正所谓“一物随其变化而异其名”也。在人类的童年时代,蟋蟀已经有那么多花样儿百出的名字,《诗经》以降,更不知凡几。北方有叫这小虫子“蛐蛐”的,我们这里一律叫“赚绩”。捉“赚绩”是我们小时候乐此不疲的游戏。在松软的泥地里,在茂密的山芋藤上,总有黑漆如墨的“赚绩”蹦跳出来。在我们看来,蓦地蹦跳出来的“赚绩”的高度和速度已接近于飞翔。因此,“赚绩”颇难捉到。一次,有位朋友告诉我他捉“赚绩”的狼狈状——明明看清眼前的“赚绩”了,五指并拢,连着身子按下去,捏紧的手掌心顿时涌上一阵毛毛糙糙的感觉,仔细一瞧,才知摁住的是一只傻傻呆呆的癞蛤蟆,恶心得手脚发麻,触电般将这秽物扔出老远。而那“正黑有光泽,如漆,有角翅”的“赚绩”,又在一边其声琅琅了。近读邓云乡的《草木虫鱼》,对其《蟋蟀》诸篇佩服得不得了。老先生说到蟋蟀对生长的地方也是有所选择的,文中写道:“生于草中的,体软;生于砖石间的,体刚。”由此,带出了蟋蟀不同的性情,前者“性情温和”,后者“性情猛劣”。一地之中,尚且如此,考之江南与胡地的蟋蟀,自是性情迥异——这是从蟋蟀天性好斗的标准来区分的。正是因为蟋蟀有此特性,千百年来,与蟋蟀有关的故事也就层出不穷。蒲松龄《聊斋志异》有“促织”一文,叙大明宣德年间因宫廷斗蟋蟀成风,于民间征此小虫,弄得不少人家家破人亡,给老百姓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此文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斗蟋蟀的习俗据北宋顾逢的《负喧杂录》记载,源于唐天宝年间。想来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皇帝老儿闷得慌,变着花样儿破闷解颐。而后世玩蟋蟀鼎鼎大名的,恐怕算南宋权相贾似道了,这位半闲堂主人置军国大事于不顾,整天与群妾沉溺于蛩戏之中。玩得兴起,心头发痒,干脆又写了部《促织经》——头头是道地探讨蟋蟀的优劣来了。贾似道的经验是:“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青麻头。青项、金翅、金银丝额,上也;黄麻头,次也;紫金黑色,又次也。其形以头项肥,脚腿长,身背阔者为上。顶顶紧,脚瘦腿薄者为上……”一代权相,俨然论述蟋蟀的专门家。有意思的是,他的方法还颇得后世首肯,比如邓云乡先生就认为,后世判定蟋蟀的优劣标准,大致不出他的这个范畴。
新年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们的节日,它和我们成年人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或者至少,新年和我的关系不那么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