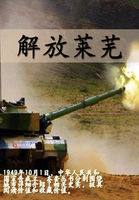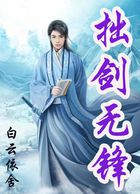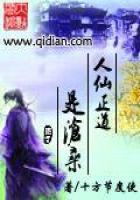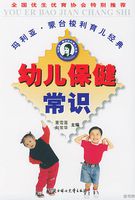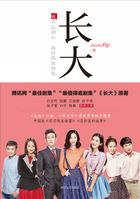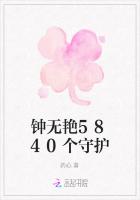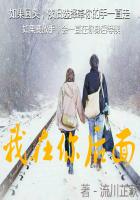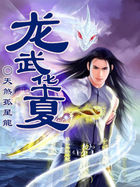夏日纳凉的晚上,身子像一只大虾,蜷缩在竹匾里。头顶是敬畏的星空,心底是盲太太土不拉叽的谜语——“移移娘,刷刷娘,光头和尚扁头娘。——打灶头间里四样常用东西”。一个少见的连环谜语。谜底至今还记得——依次是:抹布、洗帚(刷子)、铜勺和羌刀(铲子,炒菜用具)。因为常见,所以记得;因为手抓目摸,所以它们是一个个实心的名词,每一个都有体积、重量,还有色彩。比如,抹布是灰黑色的,洗帚是焦黄的,羌刀是苍白色,唯有铜勺,是沉甸甸的橙黄。铜勺似乎是这四样器物的领班,不光是它的那个大光头,它值钱的那个黄金般的颜色,还有它放在灶头上的位置——要么孤傲地雄踞在镬盖顶上,要么孤独地挂在灶边下,或者水缸口。铜勺是不合群的家伙,大头大脑,它最好的位置可能就是趴在一个平面上。如果让它仰天向上,就很不安分,多半是滴溜溜地旋转,不肯稍息。铜勺与铁镬子经常摩擦的一边,常常是亮堂堂的,是完全灿烂的金黄的颜色。其余地方,因为铜绿,常是黝黑的,是沉默,与灶头间里幽暗的光线结成了一个牢固的联盟。为了对得起那个年代清澈而略带甜味的水,我曾多次用瓦片将家里的铜勺一次次擦亮。对于水而言,铜勺的确是一个温暖的家园,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铜勺都像一个怀抱,将水揽在它宽大的臂弯里——而提水,实在是铜勺唯一的用处。确切地说,铜勺只在两条线段上工作,其一,将水缸里的水提到铁镬子做饭,烧菜;其二,铁镬子洗净之后,将脏水舀到天井里。其余的时间里,它都在休息。说来也怪,我小时候,家里的东西,什么都拿出来当玩具,可是灶头间里的这些东西从不敢轻易动用,甚至连拿出去玩的想法都没有过。后来读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到武林高手们手中的武器希奇古怪的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看到铜勺,纳闷。大概金大侠小时候对铜勺印象不深。要知道,在吾乡(金庸是吾乡隔壁海宁袁花人),铜勺是家家户户少不了的日常用具。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读钱彩、金凤的《说岳全传》,里头有八大锤大闹朱仙镇一回,叙狄雷、岳云、严成方、何元庆四小将挥舞大铁锤杀入敌阵,印象极为深刻。在冷兵器时代,锤为十八般武器之一,从模样上看,我们家的铜勺倒是一柄剖开、挖空、分成了两半的大锤——写到这里,没见过铜勺的读者大抵有个印象了吧。可惜,家里的这把铜勺,自从半个家搬到石门镇上,早不知去向了。且不说像我们这些两脚从泥田里拔出来的家庭,就是现在的农家,铜勺这玩意儿,也是日渐稀少。城市里更是早已绝迹,家家都通了自来水,哪还有铜勺的用武之地。现在的农家,需要备一把勺子舀水的,也不会想到笨拙的铜勺,只需要一把铝勺,拿在手里,轻得像塑料做成的——这完全和一个时代的轻浮互相吻合,彼此印证。
瓦的黑眉毛,配合着白粉墙那张光泽细腻的脸,就显现着一种古老的朴素——这种朴素庇护着幅员辽阔的水的居民……这道弯弯的眉毛在一种怪异的时尚中已经被拔得差不多了。江南只剩下一堵单调的白粉墙,仿佛是民间文化近一百年里受尽惊吓后的一个惨白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