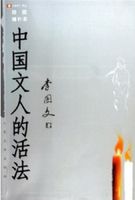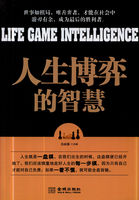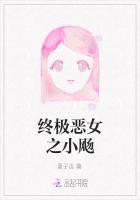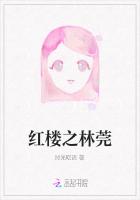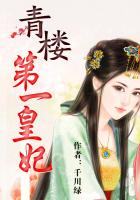像一根射线有一个顶点,一个圆有一个圆心一样,塔鱼浜既是我的顶点,也是我的圆心。塔鱼浜也十分有可能还是我的终点。我记得那里墨色瓦楞下每户人家的歌哭生聚;记得早晨一缕炊烟的蓝色成分;记得一条白狗和另一条黑狗的爱情以及它们的主人的私情;记得两三条潮湿、幽暗、冗长的弄堂,以及弄堂口的沁凉的风,“日那娘”的粗口、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侧身相让时肚皮擦出的颤栗;记得两脚踏上木桥时“吱嘎吱嘎”的声响;记得一个老人敲潮烟时因用力过猛而敲落的烟嘴;记得谁家厢房传出的哭泣;记得生产队出工和收工时那面必敲的铜锣;记得我叔叔拆烂污阿二用圆珠笔书写着“韩林”两个字贴在柴堆上的纸条;记得盲太太的谜语和随即被我们一一破解的谜底;记得那个给我带来了鲫鱼的机埠——那些搬运到高处的水洗净了我的童年;记得生产队仓库的墙上偷偷画上去的下流画;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父亲从乌镇“野坊”(锅厂)里带出来的几粒铁弹子;记得那个带给我侮辱的绰号,为此我愤怒地用碎瓦片打爆了几个同龄人的头;记得我母亲莫名其妙的病——一只摇摇船载着有气无力的她去镇上医治;记得夏天的晚上坐在条凳上听到的毛骨悚然的鬼故事;记得那里河流的走向,河面上疯长的水草,水草下面的鱼虾……记得泥墙上数不清的小洞洞,洞里面的蜜蜂,用一根细长、坚硬的麦管勾引出来的过程,以及它尾部被活生生撕开的蜜;记得平房的墙面上一年四季挂满的农具——锄头、铁耙、扁担、竹匾、蓑衣和斗笠;记得一个大雪天潜入生产队粮仓的众多麻雀,以及麻雀突然遭袭的无助的惊恐;记得初春的一天,挽起裤管,走下河埠头,立定在水里,脚踝被小鱼儿轻轻咬啮时的麻痒;记得头顶的星象,那神秘的被风吹乱的图谱;记得村子里无名的棺材,挤在阴晦的桑树地里,黄鼠狼出没的时间;记得我、三毛、咬毛、小英坐在泥地上“抓七”的游戏;记得有一年夏天,在长坂里的一只深水池塘里,我将村里的一个姓施的小男孩托举出水面的壮举;记得村里的白粉墙上,用血红的油漆刷出的一条条政治标语;记得背着竹,去队上的番薯地里偷挖番薯的黑暗中的晕眩;记得水泥广场上,用堆满场地的小捆稻子修筑和挖掘我们的“地道战”;记得这些从银幕上搬下来的“战争”而造成的我们的鼻孔里的两条黑乎乎黏稠稠的鼻涕;记得那些用村里唯一的一只木船去娶亲的日子和抬着棺材,撒着霉头纸出殡的日子;记得生产队里开会,全大队的“四类分子”到齐了,低眉顺眼,甘心接受贫下中农批斗的少数几个晚上;记得“四类分子”严子松(隔壁邻居)逢年过节,早早关了矮门,关了大门,偷偷拜阿太(即祭祖)的情景;记得每年春天,我去油菜田掘来桃树、梨树的树苗,满怀希望地栽种在屋前屋后,却没有一棵得以存活的沮丧;记得我和二弟一道去杭州,以四百元的价格扛回一台西湖牌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架在屋前空地上,让全村村民观看的得意时日;记得我追随母亲,离开塔鱼浜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记得在我的祖父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的,却一直高耸在我的想象中的那一座神秘的宝塔……塔鱼浜曾经是我的——“我的童年没有消耗完的地方”(拉金语),虽然我并不比它的青草高出多少,但是我记得,我记得。
桃花太美了,这种美,甚至让你的血液逼将出来,浇灌她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