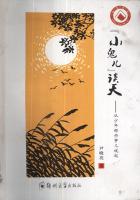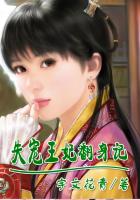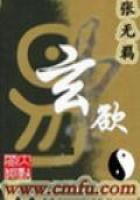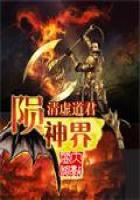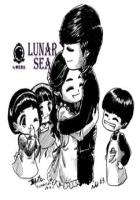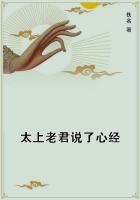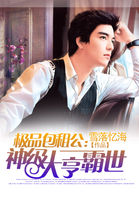起初,桑葚是青绿色的,接着是暗红、紫红,最后是油光锃亮的乌墨色——这样的桑葚才算熟透,这样的桑葚用不着手摘,微风一吹,桑树稍微摇晃一下,它就噼噼啪啪往下掉,风一大,松软的泥地上往往是积了厚厚的一批。它的甜味肯定吸引不少的蚂蚁前来觅食,以至那些挂在桑条上的,总是被一只大头黑蚂蚁霸占着,美滋滋地、白天黑夜地尽情享受着……有时候还有麻雀,叽叽喳喳的,两只细细的脚爪锁定某一根桑条,将那尖尖的鸟嘴儿伸向茂密的桑叶里去。鸟儿自然认得哪些是熟透的桑葚,哪些味道才纯正,它精明得很呢,加上它灵巧的身子,总是先于我们的小手摘走枝条上最美味的桑葚果子。有一年,我们恨死了这些无孔不入的老麻雀,我们扎了好几个稻草人——这回不是将那些稻草人插到稻田里,而是插到了桑树地里,有个捣蛋鬼还屁颠屁颠去稻田里搬了几个上来,摆在桑树地里。在秋风乍起一望无际的坡地上,浩浩荡荡的稻草人一字儿摆开,坚定地去捍卫桑条上紫嘟嘟的桑葚,这是我小时候一大快乐的发明——自然,回家是少不了给大人们一顿臭骂的。严厉一点的家长还操起了家伙(总是一把扫帚柄),在我们低贱的不值钱的屁股上好一顿乱抽乱打,嘴巴里还絮絮叨叨地教训着:桑树上的野果子有什么好去保护的啊(狠声),你格只小棺材,稻子才重要哩,稻子让麻鸟吃完了你吃什么(狠声)……祸是闯大了,弄不好还要上阶级斗争这一堂大课,只好拼命忍着。当然桑葚的不重要,不是经过了这一番打骂我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里,桑葚不像葡萄那样做得了酒,也不能像一般水果那样上得了台(桌)面,客人来家了,可以拿上来招待客人。那玩意儿只能在野地里随摘随吃,偷偷地吃,一边干活一边冷不丁摘着一个吃,入口粗糙,还有一种青草味,还要担心它的乌墨色涂黑了嘴唇,让小伙伴们笑话。在我们乡下,谁都知道那个不怀好意的顺口溜——“嘴巴乌嘟嘟,像只大屁股……”但是,熟透的桑葚的确是鲜美的,又饱含着甜蜜的汁液,又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在那个买一斤白糖或者红糖都需要糖票的年代,我对于甜味的认识其实是桑葚给我的。桑葚在我舌蕾上留下的甜甜的味觉里,有一种美好的情怀,有一种健康的回忆——甜蜜的、快乐的,又是野性的。据说桑葚还有白颜色的,我不曾见到,见到了也不会吃——哪里抵得上乌墨色的有着一层深沉亮光的那种诱人。桑葚好吃,却从未看见市场里有卖,大概保存颇为不易的缘故吧。或者,自古至今,种桑人从没有卖桑葚的意识——对一棵桑树而言,桑葚算得了什么。桑树的宝贝全在于一片片桑叶,手掌般的桑叶才是江南财富所聚啊。
桑树不甚美观,它们仅以浩大的气势取胜。剪尽了枝条的桑树,像抱头蹙眉的和尚,蹲在原野上,哗啦啦一大片,好像在呐喊(喊冤叫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