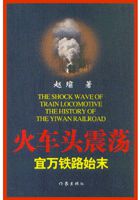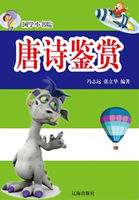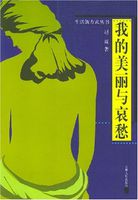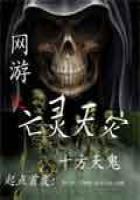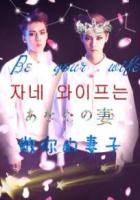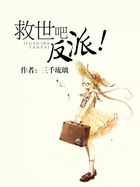青蛙是一个笼统的来自教科书上的名字,乡下叫田鸡,乡下没人会咬着舌头青蛙青蛙地叫唤的。如果细分一下,吾乡的田鸡至少有三个品种,即花背带、青壳田鸡和泥咯多。它们都可以统一在青蛙的名目下各自发出洪亮的叫声,而其中的花背带是蛙类中的上品。花背带,因其背上的条子花纹,故名。我小时候常去沟渠边将那倒霉的花背带捕来,仔细研究过它脊背上的这些条纹。它们就像人的手指肚的“畚箕”和“螺纹”一样,没有两只花背带的花纹是相同的。花背带也是田鸡中最机灵的一种,总喜欢躲在浓荫的深处,利用周边植物的藤茎或者叶子作掩护,一边唱歌,一边享受夏日的阴凉。而其正前方通常就是水渠或白茫茫的池塘,以便于它们遇到威胁时快速逃脱。花背带腿长,爆发力强,是动物世界有名的跳远冠军。其叫声也美妙动听之极。花背带是江南蛙类中的宠儿,可以说随便哪一只都是出类拔萃的。花背带暴突的眼睛,始终警觉的姿态,大概是长年深受直立动物的威胁而养成的自然本性。那些年里,如果捕捉到花背带,一般都满足了饥饿年代人的口腹之欲。而青壳田鸡和泥咯多,田野里跳跳蹦蹦的丑陋的家伙,多得连赤脚踏入田里,都能在脚底下踩到。捕到青壳田鸡和泥咯多并不难,捕到了,一般都去喂洋白鸭。青壳田鸡因为全身皮肤呈青色,故名;泥咯多也是因为皮肤呈泥土色而给取的名字——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它们的学名究竟是什么。就像大千世界里,大多数人总归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徒一样,蛙类世界中,优秀青蛙花背带的数量岂能和铺天盖地的青壳田鸡与泥咯多相比?当然,即使后两类多到无法计数,人类中的优秀耳朵也是完全能够区分得出它们的叫声的——夏天的水田里,特别是新雨过后,其声鼓鼓、沉着、底气十足的,自然就是花背带的声音;其声嘤嘤、轻巧、轻浮连成一片的,是泥咯多无疑。小时的印象中,青壳田鸡似乎是蛙类中的哑巴,很少听到它们的叫声。而夏夜听蛙声,即使在悠远的古代,也是赏心乐事——且不说晋惠帝听到蛙声问大臣:为公乎?为私乎?类似于后来白猫黑猫总要上升到国事的问题。辛稼轩“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单就诗句的清新,已是十二分的喜人,何况还有稻香扑鼻,蛙声清静着咱的耳根——听着应该是蛮高兴的事情。古人谓“一池蛙唱,抵得上半部鼓吹”,此话应当不假吧。不过,那样子的听,毕竟有如领导下乡体察民情反背了双手走过场的嫌疑,若真要是安家在水田边,没日没夜听大小青蛙的交响乐,怕自己的耳刮子早就受不了。美国夏威夷州大岛的居民就是一个例子,据说该岛居民的日常生活目前已经被当地大量繁殖的青蛙的大嗓门搅乱,市长大人正打算斥资二百万美元号召居民和青蛙作战呢。所以北京人将蛙鼓贬斥为“蛤蟆嘈坑”,还是有道理的。
我一直以为,“清明”两字,和这个时段的人文、气候非常相宜。单从词源学上说,“清明”也是一个绝妙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