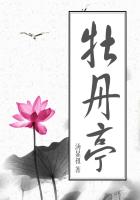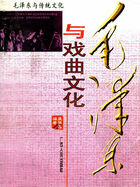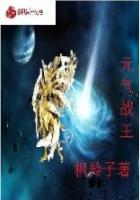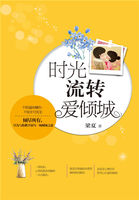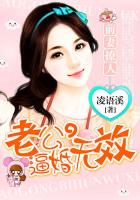筷子原名箸,在《礼记》和太史公的《史记》里,都有这个“箸”字现身。一项事物,由口头的命名到用文字固定下来,其存在世间,必定久矣。筷子当然是华夏民族最早的伟大发明之一,而且我相信它肯定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但是由于它的发明,我们的祖先由进食时的用手撕扯,到用一双精巧的筷子夹食,的确优雅多了。凭一双小小的筷子,人类就这样和野兽区别开来。单从字面来讲,箸原就是,又作,前者是竹子筷子,后者是木头筷子。后世筷子的材质大抵不出这两种。至于坟墓里出土的象牙、金银等筷子,毕竟是少数,奢侈之物,普通老百姓哪能消受得起。人类远古时期,普通的竹子或木头筷子都没有保存下来,早和使用它们的祖先的尸身一道烂在泥地里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筷子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形成一条坚固的文明的传承链,以至到了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得练就一项使用筷子的绝技。毫无疑问,筷子是手指的延长。一双灵活无比的筷子,“能夹、能戳、能撮、能挑、能扒、能掰、能剥,凡是手指能做的动作,筷子都能”(梁实秋),中国人舞动起这两根小木棍,让发明了刀叉的西洋人既羡慕又无奈,又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聪明。在洋人眼里,筷子几乎成了一根小小的魔术棒,它简洁、轻便、几乎无所不能。且看一位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描述:“两根简洁的木棍取代了西方餐具复杂的刀叉,使得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而是成为和谐地被传送的物质。”和谐传送食物,这正是筷子的妙用。也是中国人嘴巴和食物之间达成的默契。筷子应该成为黄皮肤的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件圣物,人人都有一双筷子,使用一双筷子,使用筷子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绝技。每天,轻轻夹着物质文明的成果。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某些精神和物质的页码,是建筑在这两根灵巧的小棒棒上的。筷子的发明和使用,是整个中国人的骄傲。但是,筷子这个语词的发明,它的专利,它的骄傲应归还给江南人。读者或许不知道,筷子一词其实是江南人的贡献。江南方言,箸与“住”“蛀”同音,偏偏江南是一个行舟的地方。偏偏那些船是用木头制作的(岂可言“蛀”)。据说从前江南做小本生意的船户人家,撑船是大有讲究的。祈求一帆风顺,是每天永远不变的主题。而撑船言住,岂非麻烦。大抵撑船的人当中,不乏灵机一动之人。你说住,我偏说快,快走——快走快走,久而久之,快走变音成了快子。普通的筷子多半竹子做成,于是又加了一个竹字头,变成了——筷子。到了清代末年,据说筷子筷子,快生贵子,成了一句流传极广的顺口溜。由于筷子使用时成双作对,它还成了象征白头偕老的定情之物。江南一带,新婚闹洞房,不少地方有把筷子从窗户扔进新房的习俗。随着一把筷子哗的一声落到地上,紧接着,闹洞房的男男女女齐声呼喊:筷子筷子,快生贵子。——筷子还有这样的功用,倒是那位发明这个语词的聪明船家所始料未及的。
田埂上,乱石堆里,平坦光洁的大路中央,癞蛤蟆仍会大摇大摆,当仁不让地占据要津……在上帝的所有造物中,癞蛤蟆算得上一个丑陋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