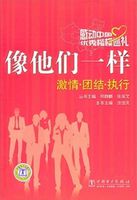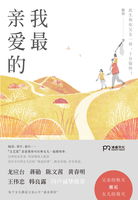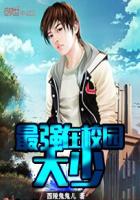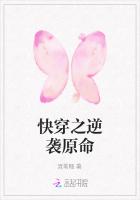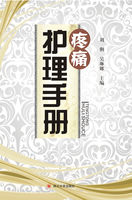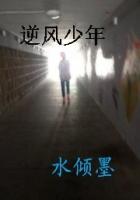如同筷子是人的手臂的延长一样,高跷是人的双腿的延伸。而任何一种有关人类自身的发明都是为了方便自己,将人的身体从某种困境中解放出来,我想筷子和高跷都不例外。今天,在一些狂欢的节日里,我们还能见到演员踩着高跷表演杂技的情景。高跷让人的体型突然变得夸张起来,就此产生一种喜剧的效果。高跷的那种难度不算太高的游戏,还是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当然,喝彩决不是高跷当初得以发明和使用的本意。也许我生在一个——天意要让我看到许多古老事物消逝的时代。在水泥路还没有冷冰冰地延伸到我的乡村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春秋两季的雨水足以让每一个试图外出的农民发愁,也让我和我的小伙伴的游戏至少中断半个月以至更久。于是,一种简单的代步工具兼游戏玩具被制作出来了——我们找来了两根大小适宜的青竹,截得一般长短,再费点时间去野外寻找树的枝桠。找到了,砍下,放置在青竹竿的一个适当的高度上,用麻绳一圈又一圈整齐地结扎完毕,一把高跷就算完成了。在那个连一双长统套鞋也消费不起的年代,我们就这样自己解决了雨天外出白相甚至去学校上学的困境。在今天,让我的女儿无法想象的是,当年小学教室里面的三堵墙上(除却挂着黑板的那一堵南墙),下雨天,总是倚靠着一排简陋而寒伧的高跷,灰头土脸的,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在我出生的那个乡村,好多年里,无论雨天还是晴天,推开人家的门角落,里面除了一根粗壮有力的门闩,必定还有一副瘦骨零丁的高跷,静静地斜倚在白粉墙上,等待着小主人的双手将之取出,无限风光地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蹒跚着前行。伴随着连绵不绝的雨天,我们踩高跷的技术也越来越娴熟。我们能够左右两手各各把住高跷的上端,一推一拉,就像父辈摇橹驾船一样,让高跷驮着自己在一起一伏的身体的波浪里惊险地前行。那时,我外婆家位于村子的南边,从我家门口走去,起码要五分钟的时间,有时外婆家或别的人家屠宰生猪,按乡村的习俗,必定要分送红白喜事里有来往的人家一碗猪血,我有时就左右两手各端了一碗猪血,用臂膀夹紧了高跷,来来往往替外婆家或别的人家分送这份固有的温情——这一方面是为了炫耀自己踩高跷的技术,另一方面,我喜欢邻里乡间串门时的那种亲密的气氛,喜欢听一听那熟悉的赞美声。当一碗冒着丝丝热气的美味佳肴送到友好人家的八仙桌上时,我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叠声的谢谢,还有艰难时世里生我养我的乡村的那一份豁达——它们成了我一生中最难忘却的记忆。
或许是桂花树栽种在月亮上的那个高度,决定了它如此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