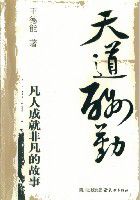在文学的政治性问题上,莫言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是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时过境迁,谈起自己的作品,莫言便不再唱“超越政治”的老调,而是标榜自己的作品里也有“政治”。2012年12月10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回答提问的时候,这样说:“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的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很多不恋爱的人看了小说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莫言承认自己的作品里有“丰富的政治”,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他的“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是什么“路数”的政治,他的“最大目标”又是什么样的“目标”。同时,他的话也缺乏逻辑上的缜密——他没有具体区分并阐释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他对“文学”的笼统肯定,对“政治”的笼统否定,也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学并不总是“好的”,并不总是教人“恋爱”的,而政治也并不总是“坏的”,并不总是“教人打架”;世间既存在“比政治美好的文学”,也存在“像政治一样坏的文学”,甚至存在“比政治还坏的文学”,实在不可一概而论的。
总之,“诺奖”从来就不是“无关政治”或者“超越政治”的“纯文学”奖,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注定不是。一个作家,并不是越远离政治,他的精神品质就越纯粹,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就越高。否定文学的政治性,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诚实的文学态度,是对文学常识和写作伦理的冒犯。伟大的作家不仅从不否定文学的政治性,不逃避文学的“政治性责任”,而且还积极地介入政治,因为,对他们来讲,政治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叙事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构成。所以,我们根本无须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应该追求能够使文学的精神更加自由和健全的政治性,应该追求能够更内在地升华文学的审美价值的政治性。
《诗经》里有政治,《楚辞》里有政治,《史记》里有政治,“三吏”、“三别”里有政治,《红楼梦》里有政治,《阿Q正传》里有政治,汪曾祺的小说里也有政治。所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文学,来评价一个作家,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既是“文学奖”,也是特殊意义上的“政治奖”。谁若对“诺奖”的历史有基本的了解,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无疑是“诺奖”评委观察文学的基本角度,是他们评价文学的常用尺度。2012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明显甚至尖锐的政治性。
3
“诺奖”评委们在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最终会转化成严重的傲慢与偏见。在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赛义德所说的“东方审判者”的傲慢姿态。
笼统地讲,西方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西方中心主义”,分别站在两个极端点上看中国。一种是像歌德那样,将中国看成人人皆君子的“理想国”,一种是像赫尔德那样,将中国看成一个缺乏“战斗精神”和“思维精神”的充满“奴才”的国度。这两者其实都是一隅之见。像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也有着复杂的多面性,而且,随着世易时移,这种多面性也会发生新的位移和转换,从而形成一种与时代性相关的“新国民性”。从国民性与生存境况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人,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迥然有别,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也多有不同。现在的中国人,一方面,因为价值体系的变构、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安全感的匮乏,而陷入变革时代固有的道德困境和伦理危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抑,体验着一种惶惶然的焦虑情绪;另一方面,从来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人,像现在的中国人这样有更多的现代性诉求,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和人格尊严感,有越来越强的公民意识和言说冲动,越来越热心于介入公共生活和公益事业,越来越不能容忍阻滞进步的社会不公和权力腐败。总之,现在的中国,与六十多年前的中国截然不同,与1976前的中国比起来,则简直可以说“换了人间”。中国人自己真切地感受着这样的变化和进步,西方人也要克服长期形成的“东方学”印象和“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偏见,要看得见这些经过艰苦努力才赢得的精神变化和文明进步。
然而,在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里,我们看到的,却仍然是一百年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话语,是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生活的极为严重的“偏见”:“他比那些喜欢模仿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令人震撼。他的语言属于辛辣的那种。在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我们找不到西方幻梦般跳舞的独角兽,也看不到在门前跳方格的天真小女孩。但是他笔下中国人的猪圈式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莫言为那些不公正社会下生存的众多小人物而辩护,——这种社会不公经历了日本占领、毛时代的犷戾和当今的物欲横流时期。”(He is more hilarious and more appalling than most in the wake of Rabelais and Swift — in our time, in the wake of Garcia Marquez. His spice blend is a peppery one. On his broad tapestry of China’s last hundred years, there are neither dancing unicorns nor skipping maidens. But he paints life in a pigsty in such a way that we feel we have been there far too long. Ideologies and reform movements may come and go but human egoism and greed remain. So Mo Yan defends small individuals against all injustices – from Japanese occupation to Maoist terror and today’s production frenzy.)通过明显的意指与朦胧的暗示,“诺奖”评委们处处将“中国”与“西方”作比较,“西方”的文化和西方人“幻梦般”的生活,那么优雅高级,那么富有诗意,中国的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却仍然停留在“猪圈式生活”的原始状态。中国的确仍然处于现代文明建构的滞后状态,但是,用如此傲慢的“东方学”态度来审视中国,用如此充满偏见的语言来“阐释”中国,却很难说是一种积极的对话态度和有效的言说策略。
像法国的十三个欣赏《废都》的“女评委”一样,“诺奖”评委更感兴趣的,就是在中国文学里发现纯粹“东方”式的生活图景——愚昧、野蛮、阴暗、龌龊、淫欲、腐败、堕落等人性背面的东西,就像美国人马森(Mary Gerchude Mason )在她的《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中华书局,2006年7月)“中国社会”一章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要找到一个与他们想象中的残缺而丑陋的中国“同符合契”的叙事体系。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让他们兴奋不已的叙事体系,就是莫言的字里行间弥散着土匪气和血腥味的作品,就是莫言的一打开来就立即发出粗野嚎叫和凄厉惨叫的小说。莫言在《红高粱》和《檀香刑》中对脔割酷刑的渲染,在《酒国》中对吃“婴儿”的渲染,在《丰乳肥臀》中对恋乳癖的渲染,在《蛙》中对“迫害狂”的渲染,在《生死疲劳》中对“怨怼心理”的渲染,都给人留下缺乏分寸感和美感效果的消极印象。尽管莫言关于仇恨、怨怼、酷刑、施虐和“吃人”的猎奇叙事,夸张逾矩,戏谑失度,既缺乏深沉的悲剧感,又缺乏丰富的社会内容和人性内容,但是,这种极端化的描写,却符合“诺奖”评委们的“东方学”理念,符合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消极想象。
“诺奖”评委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象来界定莫言。他们把莫言界定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无畏斗士,把他包装成中国的掀天揭地的索尔仁尼琴。在《授奖辞》里,“诺奖”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一上来,就称赞莫言的作品“扯下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宣传广告”(tears down stereotypical propaganda posters),就称赞他“用嘲笑和尖锐讽刺的笔触,抨击了一个荒谬的中国近代历史,那是一个人民生活和思想贫乏,政治制度虚伪的时代”( Using ridicule and sarcasm Mo Yan attacks history and its falsifications as well as deprivation and political hypocrisy),就称赞他“揭露了人类本质中最阴暗的一面”( reveals the murkiest aspects of human existence)。仅仅将“高密”视为中国之特殊的一隅,或者,将“高密”的文化当做小说家自己的独特“心象”,这对“诺奖”评委来讲,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更愿意借助莫言的作品对“中国”和“东方”说话,所以,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莫言创造出来的由驴、牛、猪、狗构成的“动物世界”,将那个封闭偏僻、虎狼当道的“高密”,当做整个“中国”的象征:“高密东北乡包含着中国的传说和历史。在几乎没有外人来过的高密,驴与猪的叫声盖过了村干部的声音。在那里,爱与邪恶都被赋予了超越自然的力量。”(North-eastern Gaomi county embodies China’s folk tales and history. Few real journeys can surpass these to a realm where the clamour of donkeys and pigs drowns out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s and where both love and evil assume supernatural proportions.)他们将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看成“野蛮人”(the brutality of China’s 20th century)。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了支持他们这一判断的叙事体系,所以,他们高度评价莫言的写作:“他展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也没有怜悯;他展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既鲁莽,又无助,又荒唐。”(He shows us a world without truth, common sense or compassion, a world where people are reckless, helpless and absurd.)显然,这样的判断,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化”性的,显示出的是一种“东方学”意义上的傲慢与偏见。如果说莫言的叙事态度是极端而任性的,那么,“诺奖”的阐释和评价就是简单而片面的;如果说作家的极端的态度,总是意味着对生活的歪曲和对人物的轻慢,那么,“评委”们对它的认同和赞赏,则意味着对一种消极的叙事伦理的不负责任的纵容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