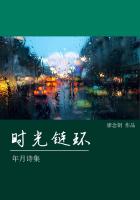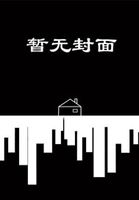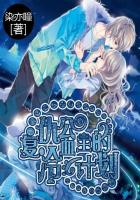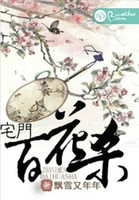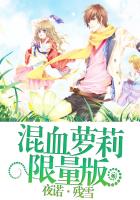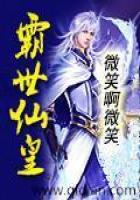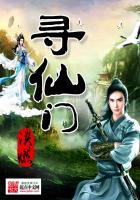余易木是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人,也是个人主义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自由是浪漫主义的灵魂。余易木珍惜自己的自由,“当时青海省文联决定调余易木当专业作家,他坚辞不肯,认为一旦成为作协体制内的人,写遵命文学,就不自由了”。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这种捍卫自由的执着,显然含着超越了利害计较的浪漫主义激情。他坚信浪漫主义是一种美好的情怀,没有这种情怀,生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在他看来,浪漫主义不可能纳入时代和集体的框架之内,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意愿和行为,正像他在中篇小说《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所说的那样:“实际上,没有浪漫主义的时代,只有浪漫主义的人。正是生活在现实主义时代的浪漫主义的人和人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倾向,构成了人类不朽的春天的强大的生命力。”浪漫主义的人具有高于现实的生活诉求,不满足于庸庸碌碌的生活,不屈服于压抑性的生活原则,因此,常常会突破现实生活的僵硬形式,做出一些不合常情常理,但却符合高尚的道德原则的事情。例如,江明为了解救被诬为“右派”的朋友马文豹,他竟然写信给“毛主席”,而且相信“他老人家会理解的”。马文豹极力劝阻他:
“江明,我的老朋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友谊,但你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我求求你,求求你——”
“问题不在于友谊,而在于真理。”
“我明白,江明,可是——”
“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江明坚定地说,“退一步说,即便有什么后果,我也不怕。我,一个共产党员,为了真理,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说完,他推开马文豹——马文豹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
“我求求你,江明!”马文豹带着哭腔说,“我的一生已经毁了。你批判我,揭发我,怎么都可以,但你一定不能这样做,一定不能……万一做了,江明,再后悔,就晚了……”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江明的行为,无疑是幼稚的,甚至近乎“精神病患者”的疯狂,但是,从浪漫主义的角度看,却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对一己利害得失的关心,表现出追求真理的无法遏抑的热情和勇气。
事实上,小说《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的主题,固然在揭示极“左”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求真精神的压制,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和伤害,同时,也是在“反右”的背景下,探讨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意义和价值,在探讨应该如何在极端“现实主义”的时代守护“浪漫主义”的精神。像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一样,这部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伦理性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只过“现实主义”的生活?如果没有最起码的“浪漫主义”,那么是否还有真正的爱情?
罗曼·罗兰说自己的时代不缺乏“好会计”,但缺乏“好诗人”;对余易木来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不缺乏现实主义者,但缺乏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倾向”在对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的广度与深度”,引起了余易木的警惕和思考。在他看来,一切现实主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被新的现实所取代,都会被人们忘记,只有浪漫主义是常新的:“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往往只是那些生活在当时的浪漫主义的人和当时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倾向。”在他看来,没有浪漫主义,就没有真正的爱情。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余易木笔下的人物,都不曾失去过对于爱情的浪漫主义的态度。《春雪》中的相爱的人虽然被时代的风暴“将鸳鸯打在两下里”,但是,他们心中的爱情之火并没有熄灭,对爱的记忆和怀念仍然折磨着他们的心。而《初恋的回声》中的人物则在爱情生活上,表现出了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超越了对自我利益和物质利益的盘算,赋予爱情一种高尚的利他精神:“什么是杨芸理想中的爱情?——文学作品就是她的蓝本。大凡做过艺术家之梦的人,都不免沾染浪漫主义倾向。客观地说,杨芸梦想的既不是漂亮,也不是地位,更不是金钱与舒适。她梦想的究竟是什么?她本人也不完全清楚,然而,我们确信,有过类似经历的读者一定心中有数。杨芸愿意献身,而且渴望献身,但这仅仅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那些乱投帖子的芸芸众生!”理想的爱情,就是充满诗意的心灵体验,是一种内在而深刻的美好感受。
然而,在一个天天唱着浪漫主义高调,其实却一点都不浪漫主义的时代,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残酷的斗争中,江明也被“拗弯了”,他的母亲也因为收到了儿子被定为“右派”的加急电报,而脑溢血病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被斗了167个小时,写了128页的检查。被发配到青海以后,在屈辱和饥饿的折磨中,他渐渐地成了“精神病患者”。
真正的浪漫主义是温柔的,也是尖锐的;是抒情的,也是反讽的;它会温柔地抒情,也会尖锐地反讽。像抒情一样,反讽性也是浪漫主义叙事非常重要品质。在余易木的小说中,浪漫主义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爱情的诗意的抒情化叙事,一方面,是关于现实的尖锐的反讽性叙事。在《春雪》中,关于夜晚时分满天飞雪的描写,就寄寓着作者的反讽性态度,而充满悲剧感的抒情性,与充满批判力量的反讽性,到小说结尾的时候,则同时达到了高潮:
我注视着她的背影。
她很慢很慢地走了几步,忽然狂奔起来。在这一瞬间,我仿佛模糊地听到了窒息的哭声。
我一动也不动地站着。透过重重雪帘,我注视着她那逐渐远去的背影,直至消隐在黑夜中。
我回过身来,心里一片空虚。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刚才走过的脚印,几乎都认不出来。但生活道路上的足迹却并不那么容易湮灭。我掸了掸外衣上的积雪,把衣服裹得更紧些。天那么冷,跟冬天全无区别。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想起了雪莱的名言:“冬天来了,春日怎能遥远?”——可是,春天里为什么还有这样料峭的冬天呢?
小说中人物发出的“天问”,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余音缭绕,袅袅不绝。虽然,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又一场“极左”的“运动”,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留在人们心上的伤口,愈合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从那一道道的伤口里,我们看见了这样的后果:人们对世界的信任感,被瓦解了;人们热爱并追求真理的信念,被颠覆了;人们的亲密关系和真诚的交往态度,被破坏了;人们想象并创造幸福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内在热情,被扑灭了。
在《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中,备受屈辱的江明则直接喊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抗议:“……我这辈子太不愉快了!我要生个儿子!派个代表去!去过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在现实中,人们吃不饱肚子,天天挨饿受罪,但是,江明发现,在电影里,人们都过得很幸福、很满足:“吃饭难,但在银幕上却很容易。譬如,粮票。没有粮票,吃得成饭吗?——吃不成。前年冬天,有粮票,没有证明,照样吃不成。可是,请问你在哪部电影里看见过粮票?噢,天地良心,中国艺术家的想象力确实不同凡响!……”在长篇小说《荒谬的故事》中,他试图解剖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如何从家庭,一直蔓延到社会生活领域,试图揭示“文革”发生的文化根源。邓老太太做为一家之主,颟顸而独断,总是通过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意孤行地主宰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生活。她喜欢借用时代流行的话语和手段来操控家人。她也搞“忆苦思甜”,“做为家庭的独裁者,她像所有独裁者一样,处处不忘提醒儿孙们她所建立的功勋,她所赐予的恩泽。”她极力阻止孙女邓菡嫁给相爱的人,从而破坏了她的幸福。邓菡最后终于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独裁者,也像许多文明的独裁者一样,并不是不希望她的子民幸福,而是希望她的子民以她所许可的方式幸福。”邓老太太完全不理解幸福的真谛,恰在于它不可能是给予的,更不是强加的;她不知道,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是不会有真正的幸福的,因为,幸福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它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欢畅的自由感。
余易木关于“文革”的叙事轻盈而又沉重、浪漫而又深刻。在小说反讽的深处,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真理的求索,通过这种深刻的思考,他为自己的充满启蒙意识的反讽叙事,奠定了稳定的精神基础。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他所达到的高度,所表现出的深刻,是许多当代作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例如,他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人的兽性的大发作,而兽性大发作恰恰是历史上所有跪着造反的本色”。例如,对“文革”造反派动辄诬人为“叛徒”,他以瞿秋白为例,阐释了这样一个无疑更符合现代性伦理的观点:“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信念,能否算叛徒呢?依我看,不是,因为政治信仰自由是人天赋的自由权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一个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宜妨害他人之自由为终点,具体地说,当一个人自愿地放弃自己原有的政治信仰的时候,只要不给他人——同志、组识等——造成损害,就没有理由称作叛徒。所谓‘自愿’,无非是指不是出于别人胁迫、追求私利等等原因。”他的这些思想,与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表达的自由观高度契合:“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才必须要对社会负责。在仅仅关涉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他的独立性照理来说就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其身体和心灵,个人就是最高主权者。”“文革”悲剧发生的全部思想根源,就在于人们完全不知道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价值,就在于权力毫无边界、毫无限制地侵入个人的生活领域,按照一种疯狂的想象和理念来“组织生活”,从而造成了普遍的人道灾难和严重的社会悲剧。
拜伦在《希伯莱乐曲》写出了这样的诗句:“呵,失眠的太阳,忧郁的星,∕犹如泪珠,你射来颤抖的光明。”余易木无疑是喜欢这样的诗句的。中篇小说《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中的人物江明,在经历了“反右”苦难的炼狱之后,在1964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倾诉着自己对珊玲的矛盾心情,“生活已经使人们失去了爱的勇气”,他说服自己,也说服珊玲,选择分手,因为,现实生活的惊涛骇浪,随时都有可能将爱情的孤舟打翻。他用理智来安慰自己,但是,这安慰,“犹如忧郁的星星从幽暗的天穹深处射来的一线颤抖的光明——它清晰,却遥远;灿烂,但多么寒冷。”余易木的小说,有着与拜伦的诗歌同样的意境。在他的叙事里,有泪水苦涩的滋味,有星星无边的忧郁,但也有太阳的温暖和光明。在颤抖的光明里,我们感受到了余易木的细腻与敏感,也感受到了他的力量与深沉。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他的作品里照射出来的光芒,将在穿越漫长的时间隧道之后,把苦难岁月的生活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的子孙后代。
2012年4月18日,北京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