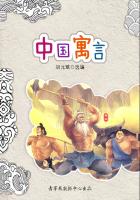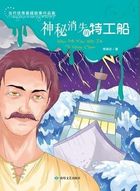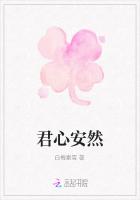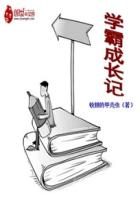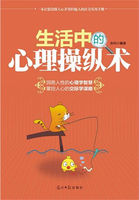有个处级单位的领导,是我以前的朋友。由于不在同一个系统工作,我们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了。
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友人孩子的婚礼上,我们不期而遇。一见面,我一下子愣住了:“这是他吗?”
这是一个个头比我要高、身体比我壮得多的东北汉子,典型的大老爷们儿,怎么竟披起了长发?望着他那既不水灵,也不光滑,还夹杂几许白丝的“披肩发”,我诧异地张开了嘴,半天也合不上。
“你——”我用手拍拍他那满是沧桑的脸,生怕认错了人。
“哎呀!老兄,是你呀!”他还是那样豪爽,对我表现出来的疑惑竟毫无觉察。
“你不是在前线项目部当经理吗?”我又深入地问了一句,生怕弄错。
“是呀!一年多没回来了,怪想大家的,呵呵!”他还是一脸的潇洒。
酒席开始了。可这顿酒,怎么喝都有点不爽。
毕竟是多年前的老朋友了,在酒桌上那一晃一晃的满头“老发”,让我看着不舒服。
几次想问个究竟,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留发是人的自由,咱是不是管得有点宽了?
然而,到酒席的最后,我还是没有忍住。就悄悄地向一个知情人问道:“到底为啥要留那么长的头发呀?不伦不类的!”
“唉,这不是较劲嘛!他领头承建的这条管道工期短、标准高、任务太重,又在大山里边,很多人担心不能如期完成任务,他就发誓:不在规定的期限内啃下这块硬骨头,就不理发!”说这话的人也在那个项目部,一脸的倦意和疲惫。
一时间,我无语了。
我不得不承认对这位昔日的友人真的了解得还很不够。以前,只知道他是一个敢打敢冲的主儿,而如今,这头长发让我看到了他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
他在同自己遇到的挑战较劲,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较劲 是一种境界
我一直在琢磨“较劲”与“较量”这两个词的区别。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词经常被使用,也经常被混用。
应该说,在性质上它们是相近的,但在使用的范畴上又有明显的不同。当反映两种对抗的势力博弈时,人们爱用“较量”来形容,但有人在描述善意的实力对峙中,也常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
与此同时,人们在反映内部矛盾的冲突中,常首选“较劲”这个词,但也有人在形容对抗性冲突时,对“较劲”这个词会不停地加以诠释。
我认为,能把二者较为明确区分开的角度,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前者侧重于描述事物的客观状态,后者侧重于表现人们的内心活动。
较劲,其实较的是不同人的思想境界。
历史上,凡是能做到以较劲的心态去做一件事的人,一定会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
这其中,可能是有一个伟大的目标或事业吸引着他,也可能是有一种大爱或大恨激励着他,但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这个劲头,会令河川改道,会让大地动容。
公元前496年,长江中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因小怨而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在今天的浙江嘉兴一带的冲积平原上展开。
战争的统帅是两国的国王,一个叫夫差,另一个叫勾践。
这一仗打了三年,最后夫差统领的吴军攻入越国的首都会稽,越降。由于越国大将文种买通了吴国的大臣,该大臣从中斡旋,说服了夫差。所以夫差没有把越国灭掉,只是把勾践以及随从大臣、后宫人员都带回了吴国为奴。
勾践在吴国为奴三年,受尽屈辱,但他全部都承受了。甚至夫差生病,他前去为其尝粪便,以此来为夫差寻找病因。他的“忠心”让夫差彻底感动,不久便释放了他。
勾践回到越国,本可以舒舒服服地重温旧梦,继续当他的国君。可他没有那样做,他要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准备复仇。
尽管这样做有着非常大的风险。
为了不消磨斗志,他放弃了自己舒适安逸的王宫,搬进了破旧的马棚中居住。
他睡在柴草上,在房梁上吊下一根绳子,绳子末端拴着一只奇苦无比的猪苦胆。每天醒来,勾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尝一口苦胆,让苦不堪言的汁液浸满身心。
这就是“卧薪尝胆”典故的来由。
就这样,他整整坚持了二十年,天天如此,雷打不动。
这二十年,勾践对内鼓励繁衍人口,努力发展经济;对外不断派文种出使吴国,积极进贡财宝,又让范蠡把他的美女情人——西施献给了夫差。
终于,机会来了。
公元前473年,勾践毅然起兵,将夫差团团围在姑苏城内。还陶醉在一派莺歌燕舞之中的夫差,此刻悔之晚矣。几经交锋,屡战屡败,随即,自杀于宫中。
“尝粪问疾,卧薪尝胆”,勾践为了光复国家,忍人所不能忍之辱,受人所不能受之苦。他创造了奇迹,一个与挫折、失败命运较劲的奇迹,一个常人无法企及的奇迹。
较劲 是一种挑战
1983年9月,到河北省委党校参加为期两年的脱产学习。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很较劲的同学,至今难忘。
当时,我们有一门主修课是《资本论》,这是马克思的一部鸿篇巨作,内容博大精深。
我们这帮同学一看那厚厚的几大本,再加上还要阅读的一大堆相关资料及书目,头顿时都大了。
有一天晚上,有个叫“老幺”的同学敲开了我们宿舍的门,手里拿着一本书,问:“这个符号是啥意思?”
“你都看到这儿了?”我反问道,内心十分疑惑。“老幺”是我们给他起的绰号,因年龄比我们都小,个头也不大。
“没有,我先翻翻,啥也看不懂!”“老幺”嘿嘿地笑着,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这是表示政治经济学概念里的一个符号,是几个英文单词第一字母的组合,代表……”
“这英文字母还能这样组合呀?”“老幺”一脸虔诚地继续问道。
“入学都几个月了,这个还没懂?那你入学考试是怎么混进来的呀?”同宿舍的人听到我们的对话后,围过来七嘴八舌地数落起他来。
“老幺”立刻没了电,满脸通红地退到了屋外。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五一”,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回家探亲去了。那时的同学都是有家室的,一到节假日都会马不停蹄地往家赶。
时间过得飞快,几天后,我们返校了。
一走进宿舍大楼,发现“老幺”竟然没有休假。我们放下行囊后,就直奔他的宿舍,想要探个究竟。
可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什么都明白了。
只见他的床头、书桌上全都堆满了书,一本摊开的《资本论》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红杠杠。桌子的一角,杂乱地放着两个饭碗,一个里面放着半个馒头,另一个是少许的咸菜丝。
“这几天,你一直在用功?”有人边翻看他那画着红杠杠的《资本论》,边问道。
“老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嘿嘿地笑了一下:“我这是笨鸟先飞啊!笨鸟!”
“先飞”这句话“老幺”说对了,可他一点也不笨。
后来,我们才知道,短短的几天假期,他对《资本论》的理解已远远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因为在课堂上,他竟可以向老师提出有关商品流通的一些问题来,这是《资本论》第二部的内容,而当时我们第一部还没读完。
很快,我就进一步感受到了这种差距。
一天夜里,我睡不着,漫无目的地走出宿舍四处闲逛。无意之间来到了教室门口,发现门是虚掩的。
推开门,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没有。正要退出来,突然发现远处黑暗里好像有一点亮光,像鬼火似的,一闪一闪的。
“什么人?”我壮着胆子问道。
“是我,幺!”
这是“老幺”典型的自我介绍方法。他已习惯于别人叫他为“老幺”了,而自己则调侃自己叫“幺”,简洁而又明了。
“深更半夜你在这里干嘛?”
“嘿嘿!研究点事。”
“什么事呀,一个人在这儿冥思苦想?”我追问了一句,可话一出口又觉得问得有点无趣。
但“老幺”一点也不觉得我多余,反倒同我“研究”起他的问题来。
“你看,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理论讲得那么透彻,可现在中央竟然支持私营业主的发展,你说这不是明明白白鼓励剥削吗?”
“这你就是瞎琢磨了。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我一脸严肃地回答道,像是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
“可我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当初共产党闹革命,死了那么多人,不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吗?”
“老幺”立刻现出一脑门子的官司。
“那你就是一宿不睡觉,又能想出什么名堂呢?”我觉得这样同他“研究”下去后果会很惨,就想打道回府。
“我想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大块头的。”“老幺”没理会我的态度,一字一顿地继续说道。
“去!去!”我没等他说完,就连忙逃出了教室。教室本来就挺大,又没开灯,他抽的烟头在嘴角上,忽明忽暗地闪着红光,有点瘆人。
第二天,我悄悄同几个要好的同学讲了这件事,他们听后都哈哈地笑了,说:“你才知道呀?那小子每天都在那里跟自己较劲呢!”
自己同自己较劲,使他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老幺”成了一个名人。
因为他总在想一些别人想不到的问题。不论他想得对与错,在那个年纪和那个时代里,就很不一般了。
有人甚至试图给他换一个称谓,想称他为“老大”,是取其老有大胆的设想之意。但很快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使他在“老幺”的位置上再也动弹不得了。
那是一天下午,刚下课他就来到我们宿舍,说道:“一会儿帮我接个站。”
“行呀!接谁?”大家立刻响应。我们学校离火车站挺远,一块儿去接站也可以散散心。
“我媳妇。”
“东西多呀?”有人不解地问道。
“没啥东西!”
“那——,我们去干啥呀?”有人开始起哄。
“嘿嘿!”“老幺”摸了摸后脑勺,欲言又止。
“莫非?”大家都是过来人,一看“老幺”这架式突然有了几分警觉。
看到大家一脸的问号,“老幺”只好坦白,说:“我怕我认不准!”
“什么?”屋子里立刻一片哗然。
“我真的想不起她长啥样啦!”“老幺”一脸诚恳地解释着。说完怕大家不理解,又把一张照片递了过来。
这是他和媳妇的合影,照片上的那女人挺漂亮,一看就是典型的农家女子。
“你老婆,你怎么会不认识?”我用拳头捶了他一下。
“真的,有时候会愣神!”“老幺”无辜地拱拱手。
我顿时明白了,他的心思没在媳妇那里。说不定以前也是这样,每天晚上都在漆黑的夜幕中,苦思冥想他那海阔天空的理想!
大家轰地一声笑了,散了。
可我心里产生的那种感慨却久久挥之不去。
较劲,对一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对自己人生的另一种挑战吗?
尽管这种挑战的过程充满艰辛,这种挑战的方法有时会剑走偏锋,这种挑战的结果也许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但是,这毕竟是人生的一种自我超越。
任何超越都是有代价的。
较劲 有时是一个误区
毫无疑问,较劲会激发出强大的正能量,但它同样也会释放出负能量。尤其是自己跟自己较劲,有时会陷入巨大的心理误区。
由于工作的原因,近些年来,我经常会同一些上访者打交道。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渐渐发现,在上访者的队伍里,沉湎于自己同自己较劲的一些人,往往结局都不太好。
也许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曾经遭受过某些挫折。或者他们虽然知错了,可没有得到予以改正的机会。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事情能不能解决,各级组织均已做了结论。对此,这些人自己心里很清楚,可是,他们就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于是,不停地上访、闹访甚至缠访,乃至产生各种各样的过激行为。
实际上,他们已陷入了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泥潭之中而无法自拔。
有一个老同志,为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起始年限问题上访了二十多年。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的总部到基层的组织,从部长到科长,找了无数个人,谈了无数次话,他就是坚持自己认定的时间是对的。
为了让组织上承认他认定的参加工作时间,他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人的白眼,耗费了多少精力,流了多少次眼泪,真是难以计数,但他认准此理,不依不饶。
我曾接待过他几次,每次看到他那满头白发就会想:这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岁数了,何苦还要认这个死理呢?
其实,对于他的申诉,各级组织都是认真受理的。各种各样的调查、核实,信函、报告也做了不少,其结论都不是老人家期望的结果。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政策是一条线,它管的是一个面、一个阶段的事情。而他的问题只是一个点,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诉求。
而他的这个点,正好在这条线外面的边缘上。
如果二十几年前,随大溜能走上线的话,也许也就走了,只要无人追究也不会出什么大事,毕竟是在战场上流过血的老同志,谁也不会计较。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二十几年的上访,已形成了二十几年的答复,而且所有的答复始终是一致的。如果要推翻这一个个白纸黑字、大红印章的历史答案,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和确凿的证据,谁也不敢做,也做不成。
况且,如今有那么多上访者,都瞪大了眼睛互相盯着,有些人没事还在找茬,如果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就纠正某一个历史定论,那又会激起多大的波澜呀!
可对此,这位老同志并不理解。
他以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特有的执着和坚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奔波在上访的路上。
领导的关心,他不理解;亲人的规劝,他听不进去。无论走到哪里,他手里总是拎着那厚厚的一大摞材料;无论见到哪一级领导,他总要如数家珍地叙述他那段艰难的历程。
他坚信,他认定的时间是唯一正确的。只要自己不死,就要找下去。
无疑,他是在向自己的那段历史宣战!
不幸的是,他最后倒下了,倒在了一场意外交通事故之中。
听到这个噩耗,我和同事们都很难过。本来他的家境很好,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也有不菲的退休金。家中的妻儿对他也非常照顾和体贴,周围的邻里、同事对他也十分尊敬。
他应该有一个愉快而幸福的晚年。
但是,漫长的上访之路早已改变了他的心智,使他对外界关闭了自己的快乐之门。
他的内心深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过去的自己,另一个是现在的自己。这两个人在他心里不停地厮杀,而且一定要拼出个胜负。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就这么走了,带走了自己的全部遗憾,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痛心。
事实上,在不同的上访路上,不同的上访群体中,类似这样自己跟自己较劲的人和事还有很多。
有的人甚至用自残、自伤的极端方式来表达这种情绪。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是针对某一级组织或个人,实际上,其内心深处,都是在上演这种自我导演的心灵悲剧。
这其中,尤其是那些对自己曾经苦苦追求、认可的事情,现在却要翻案、纠正的事例,更让人哭笑不得,痛心不已。
针对这类行为偏激的上访者,有一位在信访战线工作多年的朋友曾对我抱怨说:“有些人当初是削尖了脑袋想干这件事,别人怎么拦都拦不住,又是签字又是画押。怎么到现在,全都不认账了,硬说是别人强加于自身的,又要平反,又要纠正。这是为什么呢?”
听了这话,我就告诉他:“如果你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件事情悔恨了许多年、怨恨了许多年以后,你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话,那你该怎么办呢?”
人的情绪是需要宣泄的。可宣泄的方法有很多,唯独他们选择的这一种,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这就是自我较劲的一个源头。
当一个人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过去而又无法改变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他内心寻找平衡的一种情感选择。
当然,这是一种走进误区的选择。
记得,2013年参加学习雷锋活动日时,我在现场看到,一组手工艺作品展览吸引了很多人围观。这是用废旧的易拉罐制成的各种各样的美术作品,构思巧妙,图案精美,一条中国龙翘首飞翔、一匹千里马活灵活现、一幅写有上百个福字的字画熠熠生辉……
“这得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呀!”人们赞不绝口。
作者是一位中年妇女。我问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她笑了笑,回答道:“我买断了。”
买断,是个俗语。实际上,就是指与企业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当初有许多人盲目跟风,“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个行列。后来又非常后悔,其中就不乏一些“上访者”,一些至今还在同自己较劲的“上访者”。
其实,这位中年妇女和他们一样都面临着一种考验,那就是该怎样对待自已曾经的选择。
显然,她现在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一点,从她那洋溢着幸福和成就感的面容与声音里,我们都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没有在心灵误区挣扎的人,毫无疑问是快乐的。
较劲 是一把双刃剑
较劲,是一种心理活动。自我较劲,则是这种心理活动的一种极端表现。
既然是心理活动,主导它的力量不是什么外力,而一定是自己。较劲,有阳光的一面,也有灰暗的一面。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态。
较劲,是一把双刃剑。
敢于较劲的人,一定是一个有激情的人,而人在世上要做事,没有激情肯定是一事无成的。但过于同自己较劲的人,很可能又会是一个性格偏执、甚至固执己见的人,往往会使自己终身负重,痛苦不堪。
双刃剑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可能会伤害自己。这其中,关键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比如说,对于一件事,是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这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不要结果只要过程肯定不对,只要结果不要过程也肯定不对。
当你站在现实的土地上,前者在先;当你站在历史的高坡上,后者在上。
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你与历史的你的结合体。
没有今天的人,是危险的;没有昨天的人,是悲哀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对结果的关注往往胜于对过程的关注。
因此,在较劲的这条道路上,尤其是在自我较劲的这条道路上苦苦挣扎的人就难以自拔。
尽管,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自我搏杀。
其实,在生命的进程中,在每一件事的过程里,沿途都有很多风景。这些风景会带给你很多快乐,会消除你旅途中的疲劳。
可惜,许多人一心只向往那个目的地,而忽略了这些过程中的风景。于是,他们会错过最美丽的进程。
这样,即使当结果真的到来的时候,他们也会茫然而不知所措,甚至根本感受不到抵达目的地的快乐和幸福。
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在路上。
2009年9月,我到了日本的富士山。
车一上山,就开始飘起濛濛细雨,于是许多人兴趣索然地昏昏睡去。他们一心想着的是,到山顶再好好享受“会当凌绝顶”的美丽风光。
只有少数几个人一路欣赏着两旁的风景,一边拍照,一边交流着沿途风光带来的乐趣。
两个多小时后,车到了山顶。大家一下车,立刻傻了眼。
只见雾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一会儿,又下起了瓢泼大雨,上百号人只好挤在一个只有一百多平方米的旅游纪念品商店里。闲逛了半个多小时后,大家诅咒着、抱怨着重新回到车内。
人们跨国越海来到这个地方,得到的却是这么个结果,这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下山的路上,雨停了,雾散了。
有人不断地喊司机停停车,想重新再看看这座名山的风采。可司机一路狂奔,毫不理睬。
有人低声骂道:“这鬼子真不是东西!”其实,说这话还真有点冤枉人家。
这段旅程的时间安排,是在合约里明确规定了的,如果擅自改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尤其对比较教条刻板的日本人来讲,更是不可撼动。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富士山的山顶上,是看不清富士山的。
自己同自己较劲的人,会失去很多应该得到的风景与快乐。无论你释放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都是如此。
对此,我们在深表惋惜的同时,只能给他们以期待。
期待他们在匆匆奔向目标的路上,能歇歇脚、喘喘气,留心欣赏一下脚边的花朵或者小草。因为无论花儿还是绿草,是鲜艳美丽还是郁郁葱葱,盛开绽放的都是生命,而它们的生命只有一个季节。
也许,这些绚烂的花朵和茂盛的绿草也是在较劲。
它们是在同自己短暂的生命较劲,它们要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把更多的花香与美丽奉献给世界。
它们没有对过去的纠结,没有对现在的抱怨,也没有对未来的恐惧。它们为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而充满自信,饱含幸福,放声歌唱。
它们的双刃剑,挥洒自如。
让美丽与时光赛跑,这样的较劲,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