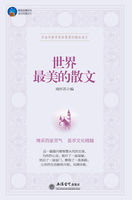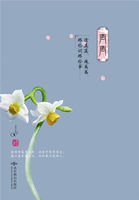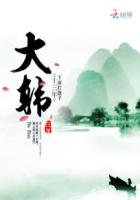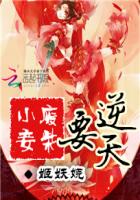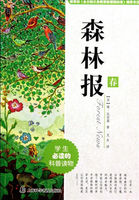家乡集市
深秋,我回了趟分别不到一年的家乡,眼前的一切感觉新鲜多了。用碎砂石铺起的一条不很长的马路,款款地从镇子中央穿过,路两边挤满了新建的商店、饭馆和一些杂货铺面,本来就不算太大的小镇一下子显得臃肿起来,乍一看,倒让人眼花缭乱。家乡的小镇,每次回来,都会给我留下一些陌生而又使人感到亲切的印象。
我虽然身处异地,但思乡之情难了,只要梳理一下杂乱的、有点激动的思绪,家乡那留给我陌生与熟知交织在一起的印象仿佛电影镜头一样掠过脑海,或时隐时现,又历历在目,而其中最清晰的莫过于家乡的集市。
家乡集市,就是逢集的日子,每逢农历一四七日,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一大早就吆着牲畜、驮着家禽、担着蔬菜、挑着山货从四邻八村来到镇子上,早早地占上一席之地,思谋着能好好的做上一桩II心的买卖。集市一般九十点钟就渐渐热了起来,中午时分人头攒动,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集市就达到了高潮,人们通过“买卖”,各取所需。到下午三四点钟赶集的人就慢慢散去了,集也就散了,镇子也恢复了平静。人们赶集除了做一些“买卖”,购置一些家用货物,吃一碗炒面改善一下伙食,凑一凑热闹外,还有一些人通过赶集结识另一些人,趁此展示一下自己,这主要是年轻人的事,因为年轻男女有了接触的机会,多少也含有一些相对象的成分。所以,集市不仅仅是一个买卖的场所,也是乡里人见面、交流的一个平台。那些平时不怎么出门的小媳妇和大姑娘们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鼓鼓遽巍,十分招人注目。小媳妇们头戴一顶白帽,再披上一条纱巾,俗称盖头,证明自己已婚;姑娘们则把一条红的或绿的围巾和一条素纱巾混搭在脖子上,又特意在两条粗粗的辫子上扎上两朵绸绸花,鲜艳夺目。她们的穿着则更很讲究,里面要是穿一件绿的,外面就套一件红的;里面穿的是白底大花的衬衣,外面就罩上紫色的外套,裤子一般是化纤的蓝色或绿色,穿红裤子的也有,大红大紫,吉祥如意。赶集对她们来说有着很大的乐趣和吸引力。她们喜欢在小摊上挑挑拣拣,讨价还价,买一些零吃的,还有一些针头线脑、皮筋扎花之类的小玩意儿,把积攒的钱花完了也就满足了。要是有邻村的小伙子跟在她们后面对着她们打口哨,她们总是露出不屑的神情,私下里却是偷偷瞄上几眼,姑娘们的心这时就乱了,小媳妇们则喜欢指指戳戳,跟着丢笑取乐,常常把姑娘们闹个大红脸。再看集市上的大老爷们,他们很随意地披一件老羊皮祆或黑布棉袄,他们心里装的是位于镇子南头的牲口市场。乡下人耕田种地、驮水送粪靠得是牛、马、驴、骡大牲口,每次赶集他们都想去牲口市场转转,买不买不要紧,关键是看红火、看门道,了解行情。牲口市场云集着“各路人马”,阵容庞大,嘈杂而热闹。有人想出售一头牛,若有买家想接手,就会有人从中讲价、圆价,互不相让,他们一会儿看看牛的牙齿,摸摸牛的骨架,一阵子又瞧瞧牛的毛色,扳扳牛的犄角,品头论足够了,价钱也磨得接近了,买主和卖主还要在衣襟底下抓个手,幵始真正谈价,摸索几个回合,才能把价格定下,一粧买卖就算成交了。最后的成交价外人是不知道具体的数目,只能估摸,这种较为原始的交易手法,虽说有几分神秘,但也防止旁人插手,哄抬价格。
小镇集市上人最多时,都是“挤”着走路,相互撞一下、扛一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摆在路两旁的摊点一个接着一个望不到头,大多是农家地里产的东西,拿来易货换钱,交易的品种也在-不断丰富。这使我不由想起前几年小镇的破旧、冷清,赶集的人也稀稀拉拉,无非是到公家开的商店里买半斤盐,打一瓶醋,扯几尺布,完了再到同样是公家开的食堂里花上五分钱、二两粮票买一个白面馒头解解馋。不几年天气,就有了一个大的对比,令人感慨,我想,一定是好的政策促使了小镇的变化。
生活给了人们希望,人们也没有让生活失望,这首先是通过集市这个交易窗口形成的,也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景。
川口两年
十八年前,我刚刚步入社会这所大学校的时候,第一站就在川口工作、生活了两年。
川口现在是彭阳县的一个乡,其名称不知从何得来,去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川口无川,只是处在一个长长的河道里,乡政府所在地仅有的几家单位也零落地分散在河道两面的山台地上。这里四面环山,看上去天如同一个锅底。
1980年9月。我从固原师训班毕业,被分配到川口小学任教,当年不通班车,我是骑着自行车赶了四十多里路去报到的。川口小学处在一块不大的山台地上,显得有些孤寂,学校有六名教师,五名都是本地的,上完课就回家了。有时候到了课外活动,他们就和我开玩笑,讲一些鬼故事,说晚上你就会听到教室里桌椅搬动和操场上厮杀的声音。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待在空旷的校园里,就会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袭来。有几次,我真想逃跑,但最后硬是坚持了下来。晚上只有把门顶得紧紧的,灯也不敢熄。当时还不通电,点的是煤油灯,我就把它拧小,放在头顶的桌子上,然后伸长耳朵静听,自然不会听到有什么怪异的声响,然后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我当时只有十七岁,白条教书,面对穿着破烂的小学生们,我认真地教他们识字、算数,晚上待在房间里一个人却瑟瑟发抖,我虽是男士,可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老师”呀。在学校吃饭也是一个难题,学校专门为我在附近村上请了一个厨师,其实顿顿都是洋芋面,也没有什么花样,厨房就在学校的前院,破门破窗。有一天早晨我去厨房圉水,发现锅里泡着一双烂鞋,学校也临近放假,从此灶就停了下来。校长人很实在,有事就叫我去他女儿家吃饭。
我在学校每周要上二十节课,从语文、数学到音乐、体育都代。教师少,没办法,赶着鸭子上架,也只有硬着头皮边学边教。有几个班上课都在窑洞里,光线昏暗,教学设施很差。虽然过去许多年了,想来肯定已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在小学只待了半年,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就到离此不远的中学去任教。临走时小学的几位老师送了我一个塑料笔记本,上面签着他们的名字,表示对我的欢送。我到中学教初二一个班的语文并兼初三的历史课,中学人多,课业不重,有一个教职工灶,吃饭也比较方便。
刚到中学时,两个人住一间房子,和我同室的老师也很年轻,是1980年固原师范毕业分配来的,他带初二另一个班的语文。他在中学时比我高两级,我们是校友,他的篮球、兵乓球打得很好,留给我的印象极深。他父亲是河南人,以打铁为业,他小时候就随父亲来宁夏读书,直至走上教师的工作岗位。1982年夏天,他和几位同事到乡政府上面的水坝里游泳,不幸溺水,时年不过二十二三,令人惋惜不已。他曾对我讲过,他在师范上学时有一个漂亮的恋人,能歌善舞,分配在固原西面的一所学校里任教,不久就会来看他的。言词之间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现在想来,都叫人感到心酸。可就在夏日一个平常的午后,在一条深山沟储藏的死水之中,他去了。五天后,他直立于水中,头发飘出了水面,被村民打捞了上来,牙关紧咬,腹中没有积水,显然是他自己用气憋死的。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他倒下得太早了。人的脆弱,常常令活着的人感到一种思维的不可名状。十多年过去了,他的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川口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我常骑自行车行走于崎岖的羊肠小道之上,翻过近二十里的山路,才能通上砂石大路回家,有一次下山,由于路窄坡陡,我被摔下了山坡,昏倒在哪里,还是一个过路的学生将我搀扶了起来,自行车的前叉也摔断了。我曾经填过一首《虞美人》的词,来形容我常走的这条山路,记得上阕是:“一条曲曲白小路,行去天将暮,驱车往来时,常遇风吹雨打山中雾……”
1982年秋季,我离开了工作两年的川口,从此也离开了教育战线,转人到了其他行业工作,十七岁的我怀着美好的理想来到川口当了一名教师,那是一个充满着梦幻的年龄,可面对的是艰苦的条件和难耐的寂寞,独自一人的时候,常常为想家、为自己的“命运不济”而掩门哭泣。现在回想起来,两年的人生旅程,实实在在地锻炼了我,使我懂得了一些生活的艰辛,也使我从稚嫩逐渐走向了成熟。
川口,我真想有机会,再去你那里看上一眼。
(原载1998年7月9曰《固原日报》〉
读书难忘少年时
少年时代是人生憧憬未来走向成熟的一个支点,有许多美好而欢快的事情永留记忆之中,使人终生难忘。对我来说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我少年时期的一些读书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