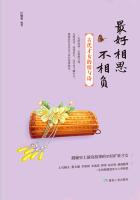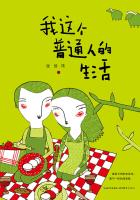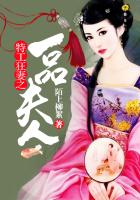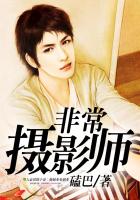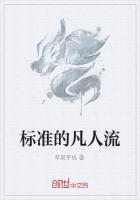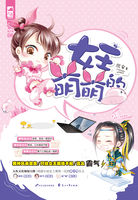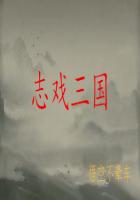周宏兴先生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诗歌评论家,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潜心中国诗歌创作与研究,相继著有《周总理与诗歌》、《李大钊诗浅释》、《瞿秋白诗浅释》及《诗歌创作艺术》等专著200多万字,主编有1000多万字的文学、诗歌等作品,曾两次赴日本讲学。《艾青的跋涉》是他诗歌研究的又一硕大成果。
《艾青的跋涉》历经7个春秋,是周宏兴先生辛勤劳作、历经千辛万苦奔走于全国许多地方,坚贞不渝地追寻艾青的足迹,走访艾青的亲人、知己及艾青本人,遍访艾青的故交、友人、乡亲,收集了半个多世纪中外文学、新闻、美术、史学等几乎所有涉及艾青的大量资料,像燕子衔泥一样地采集史料,潜心研究,长时期思考、构思写作而成的二因而一经问世,就以其内容丰富和写作艺术的新颖极大地吸引了读者,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艾青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赞誉。著名教育家周谷城题词称赞“是一本很好描写艾青的传记文学书”。著名作家张志民在序言中说:写得很细,是一本用事实说话的书。著名诗人雁翼称赞是研究诗歌新美学的新胜利。稻田孝先生则赞美这是一件富有创见的可贵的工作,令人高兴。因而此事也引起了诗人本人的重视。艾青在评论周宏兴先生和为该书写序时,果断地写下了“宏兴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他的这部书的出版,将有助于读者”。
不难想象对这样一个文学巨人的研究,从一无所有到确定课题,再到搞出成果,本身就是一次全面的考验,如果没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没有一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在这样一位大诗人面前,尤其面对诗人那颇为奇特的永不衰落现象,只会是一筹莫展,或最终败下阵来。但是,周宏兴先生却胜利了,也许这种成功是复杂的,很难用短语和浅显的道理说明,或一下子难以论证。尤其当你读此书时,看到那一个个关于艾青的真实故事,那一幕幕鲜为人知的往事,和一篇篇史诗般的名作,及艾青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动写照,你能想象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少艰辛的劳动和对学术多么严肃的态度,从中可以想到一个50多岁的人东奔西跑,走村串户,从大都市到偏远的农村的情景。我想,这也许正是周宏兴先生研究艾青,进行学术建树的献身精神吧,更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拜读《艾青的跋涉》一书,漫步在书中的高山、大海、河流、平川、山村、都市,浏览文明、丰富、繁荣的艺术天地,或喧嚣、激昂、震颤的人物心灵世界,或洪荒、蛮野、封闭的人生绝境,或蓝天晴空,欢乐伴着歌声的现实生活,会使人深深地感到周宏兴先生不仅仅是在写人,也是在写情,在写诗人和作者,甚至在写读者所需要的那种真诚的感情。简言之,就是要将对艾青的研究和整整一个时代结合起来,有意地注人一种丰富的社会内涵,就此将诗人和民族的历史命运、文化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吸引和感染读者,激发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艾青的跋涉》一书,其写作艺术是新颖独到的。它突破了人们常见的那种作家传记的写法,即先划分作家的思想,发展阶段,再用作品和材料做解释,而是一反常规地采用大量的材料和作品,逐年逐月地证实艾青的思想、感情和美学观点的发展过程。在他的笔下,艾青是崇高而又现实的:一方面艾青作为杰出的诗人具有站在历史的潮头上,敏锐地提出、急迫地冋答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的能力;一方面作为普通人,艾青又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感受人民的体温和脉搏,具有常人的情感。因此无论是描写那一杯黄土下大堰河景色的灵魂,还是在黑暗中诗人看到了火炬的烈焰,太阳的光辉,黎明的鱼肚甶,看到了希望、喜悦和胜利,描写为开创新世界英勇战斗的人们时,它都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从而使读者感到了一种真实。所以有人在评论周宏兴先生《艾青的跋涉》一书时,明确地表示该书具有美学和诗创作发展的逻辑性,也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获全国优秀书评一等奖(1994年)发表于《北京日报》,《人民邮电报》、《华声报》转载
“表现自我”琐议
近几年来,文艺界出现了一种“表现自我”的错误主张。这种主张,否定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否定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把文艺的本质归结为作家“自我意识的表现”;把文艺的使命说成仅仅是抒发作家个人的悲欢和各种幻想。这种错误主张的传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对我国新时期文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近年来文艺界兴起的这股“表现自我”的主张,主要来源于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他们主张文艺轻社会、重自我,轻理性、重直觉,否定和破坏传统艺术手法,单纯追求形式和手法的新奇,强调“表现自我”、“非理性”、“潜意识”。这些西方现代派的文艺家由于对西方的现实社会生活感到怀疑和绝望,对西方世界的种种社会现象感到不满,因而把描写资本主义现阶段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所谓人的“异化”现象作为主要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病态。但是,由于这些作家以自我的意识和幻觉来表现他们所感觉到的不合理现象,不但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且,格调低沉,充满着一种对人生、人类前途命运,对一切社会制度的悲观、绝望和否定,宣扬了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非理性主义,使人怀疑一切,涣散斗志,悲观厌世,造成了不好的社会效果,就连西方的许多评论家也表示不满,称它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文学”。可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这种文艺主张却被一些人当做“先进”的理论引进国内,广泛地传播和实践。他们说什么“自我表现”的提出,具有现实与深远的意义,是对文学艺术提出的新课题,是革命潮流对文学的波及,是历史的必然。特别是诗歌理论的三次“崛起”的文章更有代表性。这几篇文章把这种主张说成是新诗的纲领和宣言,提出了“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把“表现自我”作为新的美学原则,作为文学创作,特别是新诗创作的最高宗旨,公开反对描写社会主义新人及他们英勇斗争的精神和忘我劳动的场面。这股“表现自我”思潮的不断扩张和蔓延,致使部分作家脱离生活,脱离社会实际,对党中央提出的“二为”方针表示淡漠,对现实生活缺乏讴歌和表现的热忱,不倾听时代和人民的声音,而是把文学艺术仅仅看做是作家个人的事业,置作品的社会效果于不顾,拼命地扩大个人的、自我的作用。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主张,是背离社会主义文艺轨道的。
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社会主义文艺,就应该深刻地反映我们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如果脱离了现实生活,脱离了时代,只注意“表现自我”,根本写不出深刻动人的好作品来。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历来都是生活的实有者。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泛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对创作和生活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准确的论证,充分肯定了创作对生活的依存性。
当然,文艺是通过凝聚着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的。这样,作品中必然有一个“自我”存在,但这个“自我”与人民的斗争、时代的风云、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是作家对这一切的独特感受,绝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表现作家的“自我”和自我的心灵,竟成了文学创作的全部内容和本质,这是对文艺本质的一种否定,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种歪曲。其实,真正伟大的作家都必然是通过“自我”的思想感情,通过“自我”的个性感受,272来反映时代、歌唱人民的,而绝不是“自我表现”。因此,从形式上看,作品似乎是作家“自我意识”的表现,而实际上则来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高山下的花环》、《乔厂长上任记》、《不该发生的故事》、《在这片国土上》这些近年来出现的优秀作品,你能说它不是作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高度概括的成果吗?可见,文艺作品中出现自我是正常的,但是把作品中有我,同把“自我表现”作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特别是把“表现自我”提到诗歌创作的首位,说成是新诗歌创作的宣言和纲领,具有这个意义那个意义,是“历史的必然”,是“新的美学原则”,而把这种原则当做诗歌或者文艺创作的最高宗旨和目的,甚至提出两个“不屑”,则是极为错误的。这样的观点和主张,必然否定文艺反映社会和生活的职能,把文艺引向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歧途。
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而要做到这一点,要求作品必须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特征,要通过塑造动人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益,必须把表现新时代,反映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作为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完成。如果我们的作家对我们的时代不是满腔热忱,而是一味“表现自我”,或者把文艺的使命,仅仅当做抒发作家个人的悲欢和各种幻想,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就有可能逐渐褪色。
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共同创造者,他们是社会的主人。文艺应该以他们为主要描写对象,为他们服务,而不应该是什么作家的自我心灵、自我力量的“自我表现”。列宁在和蔡特金的一次谈活中讲道:“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深深地扎根在广大劳动群众的深厚处。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毛泽东在阐述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原则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两位导师都强调了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既然为人民,就必须写人民,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歌颂人民的斗争生活、斗争精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党的立场上说话,做人民的忠实代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可见,脱离人民,背离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持两个“不屑”,潜心于“表现自我”,是永远写不出真正对人民有用的好作品的,只能使作家的路子越走越窄,逐渐走向唯心主义、唯我主义的死胡同。
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5周年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1982年)发表于《红旗》,《山丹》、《草原》转载
关于艺术与艺术品走向市场的两点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艺术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得以走向市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信息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进人普通百姓的视野。然而,在热闹的表象背后,理性的思考使我们逐渐意识到当前艺术与艺术品走向市场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请允许我谈两点看法。
一、假和炒的问题。中国艺术作品的真假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在今天的艺术市场,造假已成为一个行业。一个赝品如洪水猛兽的艺术市场,虽然有若干权威的鉴定机构,但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在这样的市场获得自己心满意足的艺术品代价实在是高昂的。面对这样一个艺术品市场,我们不禁要问,造假为什么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