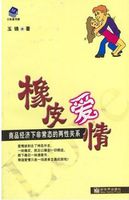他的话音刚落,几匹战马哗啦啦驰骋过来,当先一人,正是渡边。他居高临下,用鞭梢遥指,说:“姚先生,这条街已经戒严,追缉反日分子,你们的安全要留神。”
姚锒一笑,说:“我正和家兄一同喝酒,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原来真是出事了,大佐军务在身,我就不邀请你进来喝酒了。”
渡边略作思忖,跳下马来,将马鞭递到副官手里,进得门去,说:“那,我还真得借你这里小坐片刻,姚大先生,多日不见,你瘦了。”
姚迅起身相迎,也笑道:“大佐阁下,不是这非常时刻,哪能轻易见到你呀?”
渡边往小桌边一坐,左右顾盼姚家兄弟,点头道:“看见你们,我有一种瑜、亮同台的感觉,了不起,姚家出了你们兄弟俩,有意思!”
姚锒试探地问:“大佐与家兄相熟?”
姚迅笑道:“不打不相识,上次在这里被逮去宪兵队,才有幸结识了渡边大佐。”
姚迅摸不清弟弟和渡边之间的关系,琢磨了片刻,反问道:“你怎么也跟大佐相熟?”
姚锒一笑,说:“咱们俩算是一起结识渡边大佐的,至于究竟谁在前,谁在后,怕是只有大佐知道了。”
渡边也看他们,猜出了其中的奥妙,欣赏了一下桌上的菜肴,接过那随从递来的筷子,拣起块肚丝咀嚼了两下,点头称好,然后站起身意味深长地说:“我的潜意识里,隐隐认为二位将会给我在吴尚的任职增添不少光彩。”
他颔首致意,率着卫队扬长而去。姚家兄弟重新坐下,继续喝酒。大约半个钟头后,街头的戒严解除了,随从去外面探听消息后回来,告诉他们,不久前有个人在大通浴室门前,持枪将一个刚刚洗完澡出来的宪兵中佐击毙了。随后此人丢下枪,跑进对面的巷子里,左拐右绕,不知去向。日本人全面出动,却未能抓到他,只捡到了他丢下的那支枪。那支枪称之为老枪毫不夸张,真的是把填充火药打铁砂子的旧式猎枪,至今乡下还有猎户们用它。
二姚会心地一笑,却不言语,又斟了一杯酒,慢慢小口饮啜。
太阳向西缓缓沉去,一阵风吹下树头的叶子来,覆盖在碗筷上面。姚迅仰头看天,说:“奇怪,春天到了,这叶子怎么就掉下来了?”
姚锒不以为然地一笑,说:“春天也有新陈代谢,没啥可稀奇的。”
10
小马在浴室门前假装提鞋跟,半蹲下来,咬紧牙去柳条筐子里将那支填满了火药的猎枪拿在手里,将一截烟头燃着了导火索,对准这个推门出来的鬼子军官,大喊了一声。那鬼子循声看见了他手里那个黑洞洞的枪口,立即撒腿奔跑起来。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人,他熟练地在途中采用了之字形避让方式,身体忽左忽右、忽快忽慢,让刺客失去了准头。
但是,他没料到的是,这支古老的猎枪一声响后,射出的不是粒弹头,而是一团或者说是一片铁砂。他的后脑,以及脊背被这无数的细小铁片所击中,冲击力将他猛地推向对面的石柱。他连一声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断了气。
小马毫不犹豫地抛下猎枪,钻进了巷子。在这片烂熟于胸的曲折巷子里,他如鱼得水,左拐进入顾家巷,穿过一条小街,再进廖家巷,再右拐,进入北仓街,迂回向西,不一刻便到了天禄街。这时,一队鬼子兵正乘车赶来,纷纷跳下来,拦截行人,设立哨卡。
小马尽管跑得快,但还是慢了半拍,被圈在了封锁线内。
他眼睁睁地望着自己陷入了绝境,心中一阵焦躁,决定冒险向前。
但鬼子士兵立即拦住他,厉声喝道:“八格!不准过去!”
小马正待说话,前方已然过去的行人里,有个女人返转过来,一手拉住他,说:“他是我的乡下表弟,不认识城里的路,慢了几步,请你放他跟我来吧。”
这女人穿旗袍,披着长发,面容姣好,正是邹芳。那鬼子兵仔细地打量她片刻,色迷迷地一笑,挥手放行他们过去了。
小马与邹芳并肩而行,心乱如麻:这个女人居然成了他脱身的有力帮手?而在此之前的深夜里,他听到了参加葛家村会议回来的人介绍,晋夫同志的讲话和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支持,大家备受鼓舞,决心依照他的部署杀入吴尚城,在那里跟鬼子面对面地搏杀,才够痛快。
小马听了这些肯定上级领导晋夫的消息后,虽然心中仍有疑窦,但已然将疑心落实在了邹芳身上。她应对电厂失败,北撤队伍被敌人破坏负绝对责任。可是,他对于组织上没有立即处置邹芳感到诧异,这和他之前地下工作所积累的经验相违背。一个熟谙吴尚地下党组织组织人员架构以及活动规律的叛徒,留她活着,简直是在犯罪,后患无穷。
采取这个办法的人,是晋夫无疑,他的目的是什么?小马几乎夜不能寐,他虽然在游击队掩护下,但却不能恢复组织活动,而那个安排自己来这里的神秘人物,也没了音讯。这样的情况让他顿觉迷茫。他狠狠下定决心,看伤势大有好转之时,必须回到吴尚去,纵然在那时脱离了组织,也要以另外的方式为抗日出力!
拿定了主意,小马立即行动起来,趁着凌晨哨兵的疏忽,离开了藏身之处,回到了吴尚,顺便将游击队业已淘汰,准备转交民兵的一支老旧原始的猎枪带走了。他要效仿老枪,率先打响反击鬼子的第一枪。
但这一枪之后,却被这个认定为叛徒的昔日战友邹芳所救,她的出手出乎他的意料。
邹芳离开姚宅,心情矛盾,在回去的路上邂逅了这个变故,看见了那个消失多日的小马,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帮助他脱困,她有太多的事情要问他了。
俩人默默地走到照相馆,开门进去。
邹芳将暂停营业的牌子挂在把手上,免受打搅,然后去端了杯水出来,递给小马,说:“这次行动,是配合老枪吗?我听到了枪声,这一枪把先前老枪已死的传闻给打破了,老枪的安全不会受威胁了。”
小马抬眼望着他,缓缓地说:“要不是你刚才救我,我现在就该把你给干掉的。”
邹芳一惊,问:“你怎么这样说?”
小马盯住她,看她脸部的神色变化,冷然道:“你叛变了,或者,你本来就是一个奸细,混进了地下组织的敌人,此前我们所遇到的一连串挫折,都是因为你的暗中出卖,别以为这一刻假惺惺地救我,就信任你了。”
邹芳一颗心坠沉到了无边的深渊中去。她的五指无力地松开,啪的一声茶杯坠地,摔成了碎片。她的眼神变得空洞了,貌似望着窗外,其实是一片空白,嘴里喃喃道:“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这样?我没有做过任何违背纪律的事情,为什么说我是叛徒、是奸细?”
小马看着她这副模样,有些紧张,伸手去推她一把,邹芳双腿无力地软瘫在地,踝骨一阵疼痛,将她从这茫然惊诧的状态惊醒过来。她努力地爬起身,摇摇头,说:“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我如果是叛徒,出卖了同志,请拿出真凭实据来,否则就是诬蔑,就是陷害!我要向上级反映,向省委、向根据地敌工部申诉!”
小马冷笑道:“认定你叛变的,是晋夫同志,他是你的直接领导,也是吴尚地下组织的领导,他代表组织下了结论!”
邹芳愣了一下,继而反驳道:“他凭什么认定我出卖了组织,凭什么说我是叛徒?晋夫同志虽然是领导,但也不是全知万能的,他也要根据事实讲话。我绝不承认,绝不接受他这样对待我,我还要为抗日做事,对得起自己一颗中国人的良心。”
小马知道认定她是叛徒的证据就是电厂行动的失败和北撤同志被捕杀:前者,她是知情者,后者她是计划者;但同样的是,晋夫同志是电厂行动的策划者,北撤行动的知情人,他们具有同等的嫌疑。可是晋夫是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得到了吴尚地区所有抗日同志的信任和支持,他不容置疑,那只有她担负起这难以洗脱的罪名了。
他有些犹豫,再加上对晋夫的一些疑惑尚未消除,这话似乎油然浮上了心头,不禁说道:“这件事,确实不能肯定你是叛徒,但也洗脱不清你的嫌疑,也许,这才是组织上没有处决你的原因。但我此刻仍然不能把你当作同志,不能!”
邹芳流下泪来,说:“我们都是老容同志牺牲前的旧部,为什么不互相信任呢?为什么要内耗到亲者痛、仇者快的地步呢?这些日子,我对最近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作了回顾,总感觉这中间有什么不对劲。还记得让他回吴尚时,在照相馆地下暗室里召开秘密会议时的情形吗?你、我、老林、大孙、小白、刘持、齐振,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只剩下你我。这意味着什么?”
小马点了下头,迟疑道:“我本来也是必死的人,幸亏有人搭救,才捡了这条命。老容的旧部中,只剩你一个人活着,但这难道不是佐证你的证据吗?”
邹芳咬了咬嘴唇,说:“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是,如果让我活着,是为了承担了所有人无辜牺牲的罪责,就会直接掩饰了那个幕后的元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小马一时无语,脑子里思量着这个疑问:原吴尚地下组织领导人老容直接指挥的八个人,死掉六个,除自己外,剩下一个是出卖同志的叛徒,那么这批在吴尚长期潜伏的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中坚力量,将会烟消云散。吴尚地下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被敌人解决了。在以后的斗争中,晋夫拿什么和敌人抗衡周旋呢?将在乡下如鱼得水的游击队调进城,进行巷战?
他抬眼望着邹芳,说:“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都活着,真真假假,自然会分得仔仔细细。多谢你今天救了我一命,但是,我不能信任你,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查清真相的。”
邹芳正要开口,但眼光刹那间从橱窗的空隙里,看到了一辆插着膏药旗的汽车驶了过来。她说声不好,拉住小马往后门走。但隐约间听到了外面有脚步声,她做个手势,回身来解开暗室入口的木板,低声叮嘱道:“有鬼子来了,你待在下面,千万不要吭声,你要活着,去查找真相。”
小马点了下头,钻进暗室内,由于动作匆忙,原本结痂的伤口破裂开来,流血生疼。他屏住呼吸,藏在暗室的一角,聆听着上面的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