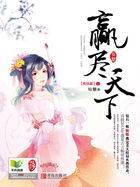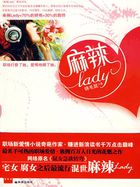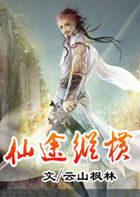古人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一套就是宁夏川。因修渠引水自流灌溉,成了年种年收的富饶之地。
宁夏人因修渠引水而得利,所以与水有关的民间故事很多。“白马拉江(缰)”就是其一。故事说,古时候宁夏川区的老百姓种点庄稼很不容易。下大雨他们担心洪水冲毁渠坝,刮大风又怕沙埋渠道,连那些渠官也提心吊胆过日子。一天夜里,渠官愁得睡不着觉,于凌晨朦胧中,见一匹白马拖着缰绳在野地里走,他也尾随其后,直到一座山下不见了。突然一声鸡鸣把他惊醒,深感好生奇怪,外出察看,仿佛野地上有白马留下的缰痕。他茅塞顿开,认为是神仙派白马前来指引方向。于是他带领民工,按照白马踪迹,终于顺利地开通了渠道。
中卫有人引申白马拉江(缰)的故事说,随着美利渠灌溉面积的不断增加,为满足需求,必须增大渠首的进水量。于是全县人民硬是凭借智与力,在黄河中垒起了几公里长的石坝进水口,直达沙坡头高坡下。工程十分浩大,被称为水下长城,它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有异曲同工之妙。白马拉江(缰)说的是美利渠的故事。还有的说,故事发生在秦渠、汉渠、汉延渠、唐徕渠等渠道的开凿过程中。
中宁人说,白马拉江(缰)故事与七星渠开凿的关系最为密切、生动和完整。
我曾在七星渠浇灌的土地上度过了20多个青春岁月。在渠道旁工作过,带着100多民工挖过七星渠淤沙,领着几个石匠砌护过双阴洞渡槽的护坡,参与过七星渠口改扩建的报道,还默默地注视彰恩渠梢一丝流水渗入地下消失的场景。
我常常独自一人,长时间目不转睛地对着流水发呆,似乎总有一种生命的律动在感染着我……
古代开凿七星渠最大的工程,在于过清水河,穿泉眼山,跨单、双阴洞和红柳沟。另外,还要通过几片沙漠山地,因此,在渠口的胸墙上刻石:“虹飞白马,泽及金牛”(青铜峡上口曾有一铜牛)以示纪念。那时仅每年的水利岁修工程,听听就会令人心惊胆战:
一是扒河口。经过一年的河水冲积,低洼的渠口早已被泥沙和卵石淤塞,正是“一岁所浚,不敌一岁所淤”。若不在春灌前扒开,黄河水进不到渠里,引水灌田便是一句空话。为此,雨水节气一过,冰雪尚未全部消融,渠工们便要站在水中劳作。三人一组,两人一条绳拴在锹把下端,一人扶把用力插下,口喊一二三齐力拉动,才能铲起一小堆石子。泥沙石子被淤积得很坚实,一把新锹用不了几天便只剩其半。有时锹头打滑,溅得三人满身是泥水。背沙石的人更是全身湿透,北风一吹,冰寒彻骨,不少人晕倒水中,有的还命丧黄泉。
二是挖淤。旧时渠道多弯,水流缓慢,加之冲沙撤水闸少而且小,所以渠内淤沙很多。若不及时清除,将严重影响进水量。春灌在即,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加班赶进度。挖沙的拼命挖,背沙的跑着背,稍有迟慢,监工的棍棒立即打来,不少民工在收工后累得连住地都走不回去。
三是抢修渠坝和渡槽。那时国家落后,根本没有什么施工机械,一旦渠毁槽断,那就灾害无穷。打坝全靠背土夯筑,渡槽石头硬凭肩抬背驼,累得吐血是常见之事,砸死砸伤的也不乏其人。因此民工们说:“上一季渠工是过鬼门关,不死也要脱三层皮!”
由于白马拉江(缰)的启示,中宁人发挥聪明才智,在七星渠跨山水沟时,上建渡槽,下修阴洞,避免山洪决堤,大获成功,并题红柳沟渡槽为“虹飞白马”,这是颇具诗意的中宁一景。为了纪念白马的功劳,他们在鸣沙与彰恩中途的大渠旁修了一个白马寺,此地以白马为名,以示永久纪念。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卫县长黄恩锡曾到过这里。作诗《朝发白马寺》:
朝来霁色远,林表出青峰。
雨气浮山翠,风光媚柳浓。
河流遥见水,僧院近闻钟。
初日前村路,登车时正雍。
后来人们在寺旁建了一所白马小学,培养子弟读书。20世纪60年代初,我下乡到学校办事,几次到寺内参观。此寺有一定的历史、建筑和文化价值,可惜被文化大革命破坏殆尽。
1980年,在中宁县编印的文学期刊《鸣雁》上,我发表了《金公鸡和沙河灯的故事》。讲七星渠起名,因渠口有七眼清泉如七颗星闪耀的传说外,还表述了一个新观点:为什么白马能够拉江(缰)呢?因为我发现白马所走的路线,基本上是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行进的。不久,中宁县水电局的工程师李其翔来找我,想探讨七星渠起名的来历。他说:“看了你的文章,我又核对了全县水利地图,确认你的说法有道理。但你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历史和典籍的资料吗?”我告诉他,因为不是专业搞的,所以手头尚未有其他资料。只相信天上的北斗星能在黑夜给人们指引方向,地上七星渠能给百姓带来了福祉。因为无论是七星渠造就了白马寺,还是白马寺成就了七星渠,它们都是宁夏的唯一。白马拉江(缰)故事产生在中宁,也就不会牵强附会了。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