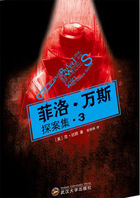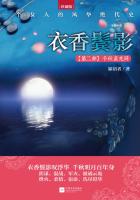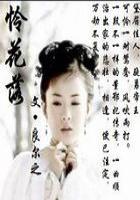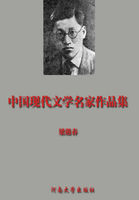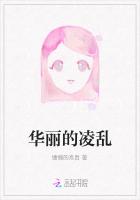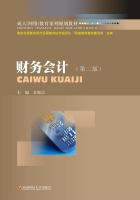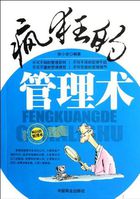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能交上几个情真谊厚的挚友,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尤其忘年交,那就更有高山流水般地韵味了。
一
1974年初春,我是宁夏中宁县广播站编辑。一位小青年拿来三篇稿件投稿。他个头比我高些,身体单薄,表情有些青涩,但眼珠转动灵活,炯炯有神,透出少见的精明坚毅。他叫杨森林,名字里边六个“木”字直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看了一下稿件,语句通顺,表达清楚,但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不够紧密,我告诉他稿件不能用。
这位小青年一句话也不问,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回头对我说:“我还会写的!”一看就是个不服输的人。我虽柔弱却喜欢有个性的人,便对他有所期待。几天后,他又带来几篇反映农民“扒渠口”工地的稿件,虽还不能用,却让我对他有了更多的期望。
原来杨森林是从几十里外的全县重点工程——扒渠口工地上来的。民谚说:“扒一季渠口,掉三层皮!”工程确实很艰苦,但因他能写会画,被鸣沙工程队调出来搞宣传。杨森林是个走一步看两步的人,他不但把工地宣传搞得有声有色,还把工地稿件另抄一份送县广播站,想借以扩大影响。
不几天,杨森林又送来几篇稿件,我挑一篇改了改,说明不用的原因,希望他继续努力。
20世纪70年代前期,社会生活极不正常。有人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立马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此相关的人员也会连坐治罪。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承蒙同事推荐,单位领导信任,组织部审查,又经县革委主管副主任审批,才被破格调任广播站编辑。信任重于泰山。同时我还有家庭责任,另外,也出于保护来稿人免遭祸患,所以工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便对自己所编稿件和通讯员来稿要求都很严格。
杨森林第四次又送来几篇稿件,其中一篇是批判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的评论,内容充实、语言犀利,我改了几处,便在稿纸头上签了一个“播”字,并建议他立即抄写清楚,寄往《宁夏日报》编辑部。当时,全国掀起大批判高潮,“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当月《宁夏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文章,并且署了中宁县杨森林的名字。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件新闻——中宁农村一位作者的评论,竟然被《宁夏日报》刊登在头版头条上了!
几十年后,杨森林在为我们出版的书——《杞乡传奇》写的序言中说,这篇“成名作”,是他一连送了三次稿件一篇也没选用,他因“发怒”而写,是“愤怒出诗人”。而当时的我,则是紧跟政治形势,“随阴阳免遭横祸”。
此后,杨森林的稿件登堂入室,经常被区县的报纸和广播刊播。这位青年作者,很快从中宁农村起飞了。
二
世界是公平的,只要努力奋斗,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杨森林因表现好,曾以青年积极分子身份结合进了大队领导班子。这是一个让许多人羡慕的工作。然而,有高山必有峡谷,大道如砥不可能直通全程。后来有人利用他写的一篇小说,故意对号入座,进行挑拨离间。半年后他重回生产队劳动。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在我看来,有时重锤敲击响鼓,能使声音传播得久远而悠长,这种历练对青年人来说十分重要。“天生我才必有用”,这是一条规律,一个人只要心底敞亮,肯于奋斗进取,机遇总会有的。不久,杨森林在小经挫折之后,被鸣沙公社调任团委书记并兼任电工,还管广播室宣传和为公社撰写各种材料。
1975年春季,邓小平重登政治舞台,大地一度复苏,我下乡采访。鸣沙公社的路线教育试点即将结束,县革委副主任张居正让我参与总结。那天下午,在张居正的临时办公室里,闫福寿、杨森林和我讨论好提纲后,由杨森林执笔。那时他年轻、聪明、出手快。他写一页,我改抄一页,老闫审读一页,然后再送张居正定稿。原以为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一个下午就完成了。这是我们三人仅有的一次合作共事,大家都感到十分愉快。
好事有时也能双降,晚饭时,我们竟然开“荤”了。原来公社庆贺试点结束,灶上到猪场里买来几斤肉,每人分了一小碗,这在当时是很难一见的“超级大餐”。那年头,物资奇缺,全国实行票证经济。干部居民,每月只供应二两油,四两肉,并且常常有票买不到。农民只在过春节时,从生产队分一点肉,此外全年再也闻不到荤腥。我们能在公社里大快朵颐,算是万幸了。
第二年,杨森林如愿上了大学。
当我再次见到已是大学生的杨森林时,从谈吐的儒雅,思维的敏捷,眼界的开阔,想到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句话。
对大学毕业生,当时的政策是“三来三去”(即工厂来的工厂去,农村来的农村去,部队来的部队去),宁夏的政策又另加一条“三不许”(不许留城、不许改行、不许考研),杨森林只能回到中宁中学教书育人。
性格决定命运。杨森林是个不甘虚度年华的人,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不停地读书、写作,积累资本以备改变:“自己的人生舞台,总不能一辈子就死守在生于斯的地方吧?”三年后,因其才干出众,被宁夏广播电台调用为记者,来到了区级单位。随之,他的足迹遍布宁夏山川,写出了大量的新闻和通讯稿件。
1988年,杨森林写出了专著《〈文心雕龙〉与新闻写作》。左民安教授评价说:“对现代新闻写作,如何向古代优秀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吸取营养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文笔清新,深入浅出,读者读了该书之后,会得到多方面的启迪”。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在当年将此书编入“青年记者文库”,作为新闻教材印发全国。同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又公开出版发行了杨森林的散文集《梦系朔方》。对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十分难能可贵。
40岁前,他应邀到德国汉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讲学。50岁以前他又出版了《笑问客从何处来——访德前后日记》和两本散文集《七彩人生》及《黄土高原的花儿》。这五部作品成功实属不易。有人称他是“一匹撒欢儿的黑马”。
王维堡先生总结杨森林已发表过的作品:“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抒发真情实感的纯情作品,另一类则是民俗作品。两者犹似两把犀利的飞刀,轮番在杨森林的手中交替挥舞,描绘现实,解剖人生,令人目不暇接。”王先生还说:“他不仅有才气有悟性,更有一种勇气和社会责任感。”
随着阅历逐渐丰富和能力提高,杨森林被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宁夏画报社总编兼社长,后又任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他一步步登上了新的台阶。
一分辛苦,一分收获。杨森林从中央党校研究生班毕业。有其父乃有其子,后来他儿子杨昊考取清华大学,并在大三时,正式出版了《季节的童话——一位清华学子的心迹》。这本书,全国数十家网站争相转载,新浪网的点击率高达110多万。小杨因品学兼优,被清华大学选拔直升研究生。杨森林教子有方,他后继有人矣!
三
无论学文还是学武,都要先学做人。杨森林的文章论著,越写越好,做人更是有口皆碑。
听朋友说,杨森林很早就为父母洗衣服,还常常为父母做饭。从他写的散文《祭父》和《探母》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人子所尽的孝道。父亲去世后,他请客时常常带着不识字的母亲,并堂堂正正地介绍给朋友,让母亲倾听朋友们说三道四。他母亲有这样一个好儿子,自然少感孤寂,他还把这种孝道延伸到岳父母身上,对他们照顾也是无微不至,使许多朋友敬佩不已。
杨森林对其他曾有情义的长辈也心怀敬重,不忘回报。20世纪60年代末,我在中宁县东华公社当干部,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有人给我讲了一位侠肝义胆好拳师的传奇故事。这位拳师,身手好生了得,用一尺多长的一根木棍,上下快速翻飞,打跑了五个劫道土匪。还有一次,四只恶狗向他扑来,其中一只立起来,将要咬到他的鼻子,他用手指头在这条恶狗的鼻子上弹了一下,四条恶狗都嚎叫着跑远了。
这位拳师曾经为保卫公社的土地出过大力,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起他,都啧啧称赞。一次,我与杨森林谈起这位传奇人物的故事时,杨森林静静地听着。直到我说完,他好一阵没有说话。最后才深情地说:“这人就是我干爹。小时候把我当儿子爱惜,不仅教过我武术,还教我怎样才能侠义、超俗、大度……”原来,杨森林在中篇小说《崖面子上的两棵枸杞树》中,写的那位武艺高超、为人极为仗义的拳师,就是这位干爹。他用自己的笔,为这位长辈立了一个不朽的碑,使这位曾经行走于江湖的传奇人物,父亲的“拜把子”兄弟由此得以永生。
尤其令我感佩的是,杨森林不仅对父母,对有亲缘关系的人关怀备至。对师长,对朋友,对自己有过帮助的人,都多有真情回报。
我的一位师范老师,后来与杨森林同事,也是森林和妻子的红娘。她与任何宗教无涉,却常做善事。但凡听到或看到学生和穷人有困难,她都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大部分去扶助。多年来,经她救济过的人真不少,可她自己得了多种疾病,却舍不得在公费医疗范围之外,去花钱医治。有人称她是“老天真”,她的“天真”感动过不少人。
这位老师的儿子,是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的系主任,媳妇是北京的一位处级干部。
去年,她到北京看望儿子和媳妇,我请她来家住了一夜。她讲了两件与杨森林有关的事。一是她写的回忆录书稿,经广州、四川和宁夏一些文学界人士看过。认为内容丰富,生活独特,一些篇章也很精彩,只要花些功夫整理一下就可出版。为此,杨森林还给她运作了一个免费正式出版的书号,但至今未能修改。二是她退休许久,且远居广州。有一年重返宁夏,杨森林接她到自己的家中欢聚。晚上睡觉前,杨森林给她端来洗脚水要为她洗脚,她硬是不肯,杨森林还是给她把袜子洗净晾干。这位成名已久的后辈,在身居领导岗位之后,还能如此诚挚地侍奉多年前的长辈师友,事之如同父母,使她大为感动,终生难忘。我听了也十分感动,我知道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去年这位老师来京小驻。恰巧杨森林也在北京,他立即出面宴请老师全家。作陪的有我和几位宁夏老乡。宁夏厨师用宁夏羊肉、羊羔肉、沙葱等特产,做出了地道宁夏菜,喝的宁夏饮料和酒。宾主尽欢,感慨良多。老师的儿子已是著名艺术家,珍馐盛宴经历过许多,但他对杨森林的感情和宁夏的饭菜特感兴趣,高兴地说:“今天和森林相聚太高兴了,吃得太痛快了,也太过量了。”老师的儿媳妇说:“难怪婆婆老夸杨森林呢!跟你们这些人一接触,就感到轻松愉快,只要你们在北京,我们就多联系。跟你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也很投缘。”“投缘”二字,说得很好。杨森林对待投缘之人,总会待之以赤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杨森林在德国讲学期间,写过一篇发自肺腑的长文《化作烈焰映太空》。这篇文章在中宁的熟人中传开后,引起多人感叹。杨森林早已当了处级干部,并已成为宁夏的文化名人,又在德国的讲台上赢得了异邦人士的赞誉。但他没有自我陶醉,忘却故交。这篇文章中所写的,是当年帮助过、培育过他的三位公社干部,他们都已经作古。而杨森林却在遥远的莱茵河畔,为这三位普通人,写了这篇情文并茂的悼念文章,对他们的在天之灵表达了深情的感激。在这个物欲横流、人情如纸的年代,但凡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有一种深深地感动。
四
三人行必有我师。虽然我比杨森林年长近20岁,但我深知结交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相当于为自己打开了一个友善世界。“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人,如同一盏明灯,能照亮你的心程,使你深受教益。当然,你自己也必须提高素养,只有相得益彰,才能达到“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层次。
1980年初夏,我写了一篇散文《塞上明珠——青铜峡漫游》。我是个缺乏自信的人,且也不了解文学界状况,便请杨森林看看。此时,他已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在文艺创作上也小有名气,他看后很老练地说:“寄给《朔方》,我看够发表的水平!”果然,当年《朔方》第九期发表了。后来《云南民族文学》和《宁夏风情》都收录了它。
不久之后,我调往银南地委机关,由中宁县来到吴忠市。杨森林调往自治区,两地不足百里,因工作繁忙很少遇面,但多年的情谊从未间断。我在驻地或出差到县乡,每次听到杨森林写的广播稿或看到书报杂志上的文章,都仔细听认真读,为他欣喜。有时他来吴忠采访,也打听我的情况。
几年前,杨森林送我一本他的散文集《黄土高原的花儿》,使移居京城的我倍感亲切。书中描绘的图景,使40多年前中宁的一切又生动地浮现眼前:左家龙头在鸣沙公社黄营大队(今鸣沙镇),我曾在此地带领民工,修理双阴洞沟护坡住过一月有余。书中写的枸杞树、鸣沙塔、铁匠铺、贺兰山岩画、西夏王陵、北塔等,宁夏的物产、民俗和风景名胜,我也熟悉。可杨森林独具慧眼,通过他独特的文学感悟,使这一切都活在他的笔下。
我故乡中卫的高庙,它是看着我长大的。至今我还依稀记得1942年的一天晚上,我站在外祖母家房顶上,久久地看着高庙被大火焚烧的情景。也还记得劫后重建时,画在大殿墙上的“放大样”。旧景如梦,历历在目。杨森林写他在大雪天的《高庙禅悟》一文,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生活本身是禅,像雪一样洁白,像雪一样自然,像雪一样大度,像雪一样潇洒,像雪一样不求回报。活着本身又何尝不是禅呢?人世间什么样的沟沟坎坎又会过不去呢?心灵中什么样的污垢、阴暗,又怎样隐藏得住呢?”
杨森林由农村通讯员到大学生、记者、作家,发生了质的飞跃,他的丰富经历,可说是这代优秀青年的一个缩影,由雪天的感悟,我想到了他的为人。
五
2004年秋,闫福寿告诉我:杨森林不忘老友情谊,为我们运作了一笔宁夏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书号的经费。我便由京返宁,经过整编改写,出版了与老闫合写的《杞乡传奇》一书。森林为我们写了一篇序言《他那一支笔与他那一片天——忆与王非凡、闫福寿的友谊》,这是老闫与我平生的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杨森林。此书发行不久,老闫“西行”了。我想,他是带着快慰走的。至今我常常想起这位不幸早逝的老朋友。也因此想起他生前对杨森林的怀念。朋友之间,能在某种时候助一臂之力,是会令人永远感念的。
我的亡妻罗益群,上海人。20世纪50年代,她和几十位上海学生,响应政府号召,到宁夏读书工作,她们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都贡献给了宁夏建设事业。5年前我写了《益群长歌》一书,杨森林在百忙中从书名、内容、版式、费用等各个环节上,为我具体策划和认真指导,似当家之人。书出后,得到了许多朋友积极评价,她的同学说:“看书后,我们都很激动,不仅为罗益群立了传,也是我们几十位上海来宁同学的集体写照!”我和家人都很欣慰,十分感谢杨森林全力帮助。
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个笨鸟,有时脑子一下反应不过来,常常“慢半拍”。做事只知规矩而不会变通,有时不免给同事和朋友带来麻烦。为此,内心常怀愧疚,却又禀性难改。杨森林知道我的弱点,每次邀我相聚,总是热情如初,似乎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
去年,因工作需要,杨森林在京驻了一段时间。由于同住京华,他常常关照我。他是那种“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的人,古道热肠,每每令我感动。
2011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