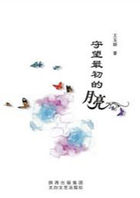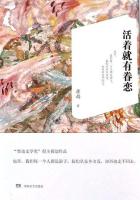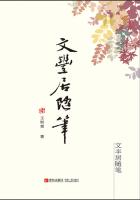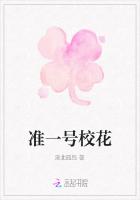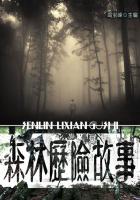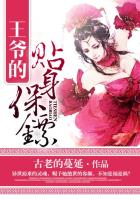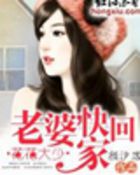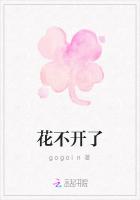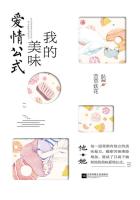1996年3月9日,西安市作家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市文联三层小楼平台上搭的木板房内召开。这情景使我想起12年前,市作协成立时,从筹备到开始折腾着干一番事业,一直都是在社会三路那个居民大杂院的平台上搭起的小棚屋里。12年,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可谓沧桑巨变,高楼大厦比肩接踵,厅堂馆舍金镶玉砌。可是,作为荟萃西安文坛风流精英的作家协会,如此庄重的换届大会却依旧在如此简陋寒碜的场地上召开,真不知是该为文人苦守清贫的气节而歌呢,还是该为经济与文化的失衡而叹?
会议的程序也大概是“因陋”而“就简”了。上届副主席、老作家景平宣布:因为条件有限,今天到会的都是作协理事,所以,当我们举手通过了理事名单后,会员代表大会就改成了理事会。
主席台是用四张办公桌拼起的。台上连一副话筒都没有。主席贾平凹坐在正中间,他要作上届作协的工作报告。平凹讲话历来“小气”,好在人不多,场不嘈杂,报告的内容我们还是听得清的。平凹在列举作家们创作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时,突然冒出一句:我们所创办的《散文报》虽然只出了一期,却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许多人还记得这份报纸……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不禁怦然而动。手中没有平凹的报告稿,可我总觉得这话是平凹的临场发挥。《散文报》在我们手里只出了一期,十余年过去了,还有谁记得它呢?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不会忘记;平凹说,“许多人还记得”,说明了平凹不曾忘记。还有谁?子雍,和谷,景平,广芩,周矢……对,平凹是对的:对于那段随风飘逝的日子,我等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我们曾用热情点亮一支火把,使那日子燃烧得闪闪烁烁!虽然,火把在转瞬间熄灭了,可我们的热情是从血脉中流出的啊!
我们能忘记么?
是夜,我从堆积如山的旧报纸中翻出了那份“独生子”(说“独生子”是指“血亲”,《散文报》后来曾转让给一家报社,他们又出了两期后方停刊)。望着这泛黄的报纸,望着那些熟悉的名字,我的思绪便回到了12年前。
我要为这段日子写一篇文章,不仅仅是为了回忆……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我想,所有的过来人都会知道:公元纪年的八十年代初,对于中国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
沉重的冰层已经打破,乍暖还寒的时节已经过去;暖融融的春阳下,人们甩脱了束缚自身的盔甲,敞开胸襟,大步流星地去追寻失落在冬季里的梦。整个中国,升腾着一股热气腾腾的浪潮。后来的人,可以对这段日子评头论足:说浮躁也罢,说狂热也罢,说盲目也罢,但中国和中国人毕竟在这段日子实现了一次跨越。“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一池水总是显出了生命的活力。
1984年初,恢复不久的西安市文联着手筹备下属各个协会的成立。我当时在《西安工人文艺》编辑部任副主编,并且早已是省作协理事,所以便被指定为市文学工作协会的常务理事,与平凹、和谷、商子雍等人一起筹备这个协会。
按照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规定,作家协会只能是省上的组织;而按市文联组织设置的惯例,市上的各个专业文学艺术团体也从不以“家”命名,大概全国都是如此。所以市上筹备的就是西安市文学工作者协会。筹务组开过几次会后,有人提出: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哪来那么多旧框框?西安是个大城市,写东西的人这么多,成就也不小,我们为什么不敢叫作家协会呢?作家有个什么尺码?
我是个喜欢幻想、容易冲动的不安分分子,我第一个响应这个倡议。而主持筹备工作的文联主席黄悌又是个极好说话的老先生。于是,我们的协会就叫西安市作家协会。而正在酝酿中的曲艺、摄影、美术等协会,听到我们称“家”了,也纷纷改名,扯起了曲艺家、摄影家、美术家、书法家协会的大旗。
那时的市文联根本没有自己的营盘,只是在社会三路一条弯曲而狭窄的小巷内租了一个大杂院里的几间平房办公。作协成立后,在平房的平台上搭了间简易小屋,副主席贾平凹、秘书长和谷都挤在这间小屋里办公。我和子雍已调到西安晚报文艺副刊部搞编辑工作。在作协跑腿的还有后来成为青年作家的张仲午(黄河浪)和“文革”后期曾在市委任过要职、又因这个“要职”而削职为民的刘大鹏。
那年,子雍和我都是四十上下;平凹与和谷都是三十刚出头,正是男儿干事业的黄金季节。国逢盛世,人到中年,我辈又皆是些热情冲动的书生,既然拉起了山头,亮出了旗号,我们总得干点什么。
于是,我们几乎是天天碰头,日日谋划,要在西安文坛上掀起几番波澜来。
我想,弟兄们至今也不会否认:我们的谋划是有些功利主义,或者说是急功近利。但我们至今仍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无论是为功还是为利,都不是为了中饱私囊。文联穷,作协更穷,我们必须靠我们的奋斗改变这种穷困的状况。全社会都在倡导广开生财之道,作家协会难道就应当永远蜷缩在这平台上的棚屋内么?
我们先办起了以平凹为院长的西安文学院,由省内知名作家轮流讲课,地点在新城剧场。文学院办了三个月,平凹、路遥、忠实等省市名作家几乎全部亮了相,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倾囊倒给近千名文学青年。每场讲座都是座无虚席。而我们对学员们交来的习作每篇都进行认真阅改。我和女作家杨小敏还为学员们作了两场学员作品点评的报告。最后将这些作品汇集成册,文后皆有作家的评注。而我们这些“教员”们得到的报酬呢?每作一场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仅领20元的讲课费。
文学院只坚持了三个月便因经济困窘而解散。但是,后来这十余年的现实却昭示了它的辉煌:许多学员都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且著作颇丰;不少学员以后成了各报刊的编辑、记者,有的甚至坐上了主编、副主编的交椅……
我们又与西安锅炉四分厂联手举办了西安首届“冲浪”文学奖。30多位作家和作品受到了奖励。此举在陕西文坛引起轰动,省市报刊均发了消息和评论。记得《西安晚报》的评论员文章是我撰写的,题为《跃上潮头干一场》。仅从这题目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我等是怎样的豪情勃发,大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势。
我们又办起了西安市作家协会作家书屋。这是我们唯一的经济实体。可是,由于我们根本不谙经营之道,不出半年,书屋就倒闭了。由平凹亲自题写的牌匾也被一层油漆涂盖了……
西安作家协会草创初期,可以说身无分文,囊中羞涩至极。可是,我们这群不甘寂寞的书生却迎着改革的大潮,为繁荣这座古文化名城的现代文学事业,风风火火地奔走着。尽管我们的各种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使沉寂了多年的西安文坛掀起了层层热浪。历史将证明,我们的努力不是徒劳!
为伊消得人憔悴
上世纪80年代初,文化市场上各类小报的走俏是那个特定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尽管良莠不齐,却挑开了封闭太久的文化市场那道厚重的幕帘。
我们也跃跃欲试,准备以市作协的名义办一份小报,让市场上有我们自己的声音。
碰过几次头,意见却统一不下来。和谷、子雍和我主张办一份好读的报。好读的必然好卖,我们必须考虑经济效益,因为我们没有钱。而平凹始终坚持要办一份《散文报》,专门刊发散文新作,并说:咱办的是全国第一家《散文报》,肯定会有读者。贾平凹是以他的小说蜚声中外文坛的。在大多数读者心目中,平凹是位小说家。然而,文化圈里的人们都知道,平凹的散文远在他的小说之上。所以,我们也完全理解平凹对散文的钟情与执著。
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南院门春发生葫芦头泡馍馆的餐桌上开的。一向柔弱温和的平凹却态度坚定地说:就办《散文报》,没错。平凹虽说年纪比我们小,但他毕竟是作协主持工作的副主席,是我们的“头儿”,并且文学上的成就也是我等不堪与之比肩的。于是我们就定下来:办《散文报》。
前期筹备由秘书长和谷负责。起草文件、跑刊号都是和谷干的。《散文报》很快得到省出版局的批准。于是我们便向朋友们约稿。约稿信反响热烈,稿件也来得很快。我们又把市作协理事、当时还在西安仪表厂当工人的周矢请来,搞文字编辑;又请著名青年画家王西京、范崇岷为文章题图插图。一切准备就绪后,稿件发往西安晚报印刷厂。我和子雍就守在排字房内,边指挥工人师傅排版边校对稿件。
一期报纸需要万把块钱,这对于市作协,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说实话,我对《散文报》的前景并没有平凹那样乐观,可这是弟兄们的事业,是市作协成立后的一次大动作,我不能不出力。在这帮弟兄们心目中,我是个最能折腾的人。“冲浪”文学奖是我牵线拉来的赞助;作家书屋是我动员一位老同学在他家的门面房里开办的。现在要为《散文报》筹集开办资金,弟兄们把目光投向我。我自己也觉得,此事舍我其谁?
我跑到在一家街道企业当头儿的哥哥那里借了一万元,拍着胸腔子对哥说:一月内一定归还!
《散文报》很快印出来了。四开大报,贾平凹题的刊头、老作家李若冰的题词“真情是散文的生命”印在头版;所发文章皆是陕西散文界的名流佳作;版面清爽高雅。平凹将新报捧在手里,浏览了一遍,手指将报纸弹得哗哗响:“啊,这有啥说的嘛!”一副顽童般的得意。
可是,报纸一次印了12万份,堆起来就是一座小山。我们是自办发行,尽管事先我曾为作家书屋拟过一份征订通知,发往各地的报贩子,各地也有信息反馈回来,但这12万张还是要通过我的手分发出去的呀!这些“宝贝儿子”该往哪放?在哪捆包?怎样邮寄?我们竟一点招儿也没有。
和谷对我说:老兄,这事还得靠你。钱是你筹集的,你手下的人又多,干脆你就跟咱把这事一揽子承包了吧?
这实在有些难为我,可我又无法推脱。都是哥儿们,我不应承下来,不是难为他们了吗!
我请子雍给他在东四路小学当教师的夫人打电话,让她在学校给租一间空教室。随后又跟我在工厂里的徒弟们打招呼,让他们到东四路小学集中。找不来汽车,便雇了几辆三轮车往返拉运。从中午到晚上十点多,12万报纸拉运完毕,堆了半间教室。
我找来的几位徒弟,苦战四天,分数,捆扎,打包,写皮,填单……终于将这12万份报纸安顿齐整。在此间,我曾与平凹、和谷找过市邮局报刊零售公司。公司的头儿出于对我们这些作家们的尊重,答应为我们包销两万份,并且提前付给我们三千元。作家书屋留了两万份,还有八万份,我们必须通过火车发往外地。
可是,我们的手续不全,西安车站不允许我们按印刷品发寄。一时情急,我从省政府一位司机朋友那里借了一辆“巡洋舰”小车,将报纸连夜拉往咸阳车站。
是夜,寒风料峭,我打发两位随我而来的徒弟找地方睡觉去了,自个裹一件旧军大衣,在空荡荡的候车大厅里守卫着一堆报纸。
小插曲:连日辛劳,后半夜我实在困得撑不住了,便靠在报纸捆上打盹。朦胧中耳边飘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这儿太冷,跟我走吧,找个暖和地方睡去……我睁开眼,瞅了一下身边的那位挺年轻挺风骚的女人,只皮笑肉不笑地“嘁”了一声,便把头缩进了大衣领内,闭上了眼睛。
在咸阳老作家峭石的帮助下,第二天下午,这批报纸终于从咸阳站先后登上了火车,飞往全国各地。
我长吁一声:天无绝人之路!身子便如泥似的瘫软下来……
道是无晴却晴
《散文报》有编者们意料之中的辉煌:全国各地文学界的朋友们收到我们寄赠的样报后,纷纷来信,称赞这全国第一份《散文报》高质量、高品位,给“文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名家们的佳作也乘飞鸿传来,全国唯一的一家《散文选刊》一次选载了《散文报》上的4篇作品。
《散文报》也有《散文报》创办者们意想不到的悲惨:发往全国各地的数万份报纸,竟然只收到了一个报贩子汇来的45元报款,汇款人附信称:报纸根本买不动,但为了我部信誉,我们还是把款汇来。今后若还是这种报,请不要给我们发寄了……有几家来信,说他们卖不出报纸,反倒占了他们的库房。不得已,他们按废纸卖到了废品站。还指责我们的征订通知欺骗了他们。而大多数的报贩子既不联系,也不寄报款,数万份报纸便“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我不信,平凹等友人更不信。于是我找到我的一个学生,她家在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骡马市口摆了一个小书摊。我让她拿些《散文报》摆到摊上卖。我自己还特意到摊上去看了几回。结果,一天卖了两份报。严格说,是卖了一份;另一份,一个人买过后,走出不过十步又折了回来:“这种报,不好看,我不要了。”扔下报就走了。
那年月,靠编小报发财的多得去了;靠贩卖小报发大财的更是数不胜数。可为什么我们编的这份小报就如此悲惨呢?
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十年浩劫”造成文艺园地万花凋零,一片萧瑟;人们的心也被冰冻得太久了,尘封得太久了,十亿人民“八台戏”看得人腻歪了。现在人们需要一点轻松的,甚至是带点刺激感官的玩意儿来调节一下自己那绷得太紧的神经。于是,小报应时而生。这些小报多是以刊登色情、凶杀、艳遇、秘闻为主的俗而又俗的地摊文学。而我们所刊载的却全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阳春白雪,和者甚寡”,可又偏偏选中了(确切地说是“被逼到了”)地摊上销售,又怎能不受尽冷落呢?
我们傻眼了……
眼看着给我哥还钱的日子到了,除了市邮局的那三千元外,我们几乎再无任何收入,何况报纸在发寄过程中还花了不少钱。
正在一筹莫展时,一个曾在文化圈里混过几天的朋友找我,想让我请一下平凹等名家,在一块聚一聚。并说,他现在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商店当经理,只要能与名家一聚,什么事都好商量。
我约好平凹、和谷、子雍。主家在曲江春酒店摆下盛宴。席间杯觥交错,主家先是抒了一番对我等的倾慕之情,随后就海吹其经营之道和雄厚财力,其中有一句话很传神:如果政策允许,我把解放路这一条街都能买下来!
平凹醉了,和谷醉了,我和子雍也晕晕乎乎的。借几分酒力,我向主家说出了我们办报遇到的困窘。主家一拍胸口:不就差七千块钱吗?小意思,包在哥哥身上了。
席散后,那人果然给我甩过七千块钱来。我声明是借,一旦倒腾过来,一定如期归还。那人江湖式地一挥手:自己弟兄,看不起我?
我将一万元还给了二哥,那是他们单位的公款。
可是,事情过了不到十天,那人却在夜色中蹲在我家的那条小巷口等我。一见面就哭丧着脸说:兄弟,哥哥栽了。那七千元是老板让我买东西的。我那天喝高了,就自己做主把钱给了你们。你知道,我是人家雇的经理。现在老板限我三天把钱找回来,不然就让我滚蛋,你看……
我这才猛然醒悟:这小子完全是个江湖上打把式卖假药的骗子!
我不想跟他多费唇舌,便说:好吧,明天上午你到市作协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了个碰头会,一致赞同:把钱还给他。此等人不可交!
可钱从哪来?
还得我去跑。会议决定由我到一家曾与我们多次协商,准备共同筹办西安文学家、企业家联谊会的企业去借。和谷给开的介绍信。会议在决议上写道:此款以作协名义借,还款由徐剑铭负责,属于徐私人借款。但如果《散文报》没有收入,作协将共同担承债务。这个决议上平凹、和谷和我都签了字。
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会看出:这是一个违背经济规律的决议。这种决议也只有我们这帮子书生气十足又以友情为重的人能作出来。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作家书屋上。平凹、和谷、子雍、大鹏、张仲午和我轮番穿梭地往作家书屋跑,但书屋依然回天乏术,只好关门大吉。
文学院也停办了。
轰轰烈烈的事业仅维持了半年多光景,便火熄烟灭了。
经和谷牵线,我们把《散文报》转给了另一家报社。
社会三路那小巷,那大杂院平台上的小阁楼一时陷入沉寂。
不久,我因一件飞来横祸遭到市检察院传讯。而三两天内,检察官的案头就多了几封匿名信,信中所列举的罪名让检察官们大吃一惊:
徐剑铭从某厂骗来五千元,以办文学奖的名义和他的几个哥们私分了;
徐剑铭承包《散文报》,净赚十几万;
……
于是,我被逮捕了;平凹、和谷也被叫到了检察院……
检察院抄了我的家。当检察官来到北城墙脚下,从结满青苔的小院走进我那间墙上裂着口子的破民房里时,一时竟怔住了:纸天棚上有老鼠在奔逐嬉闹;潮湿的砖地上摆放着一副老式的木板床,老式的书桌和一副破沙发、一副旧木板柜和一个用破木板钉的书架……存款单倒是抄出几张来,皆是三十五十的,加到一块不足五百元……
那段日子,我既要在《西安晚报》编稿,又要外出采访,又要和弟兄们一块搞作协的事,每天黎明即起,午夜始归,所有的活动都是靠骑自行车(平凹等友人也是如此)。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妻常常抱怨地说:你们这是哪服药吃错了?
是哪服药吃错了么?
我从来不想为自己的行为挂上堂皇的桂冠。我承认我自己书生气十足,又憨愚得可笑。我办事原则性极差,一切凭感情用事,意气用事,率性而为。这也是天性,大约此生难改了。我常常犯混,有时混得连自己都恨自己。可天地良心,我不是坏人!我不会算计别人更厌恶那些算计人的“人”。后人怎样评说我们在西安文坛的那阵子折腾,那是后人的事。我只能坦率地说:我在此间无愧无悔!
贾平凹曾在五年后的市作协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用一个辛酸的“调侃”概括了我们的失败,他说,这就叫,文人经商,赔个精光!
西安的文坛从此沉寂下来。
但沉寂不是颓废,而是从浮躁走向成熟。
平凹埋头静虚村,写出了震惊中外文坛的长篇巨著《浮躁》;
和谷去闯海南,一肩挑起一报一刊总编辑的两副重担,且著作颇丰;
子雍的杂文在全国遍地开花,赢得阵阵喝彩;
与上边几位比起来,我是最差劲的一个。但是,这些年来,历经风雨磨难,却还傻呵呵地活着,每天躲在这阳台改成的无梦书屋里,写些短小文章,让文坛上多一个嗓门,也算没有白活。不是说:“大狗叫,小狗也要叫”么?你不管我是“大狗”还是“小狗”,我反正是用自己的嗓子在叫!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拉拉杂杂写下这篇文章,是想对弟兄们说——
不必为我们的失败而沮丧,毕竟;
我们曾用青春的热情;
让那需要燃烧的日子;
燃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