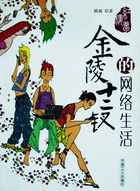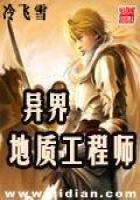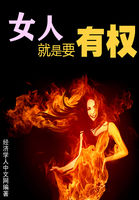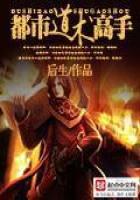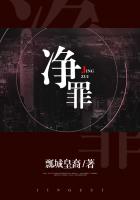前年秋天去俄罗斯,曾在彼得堡住了一星期。
觉得自己实在很没有出息的是:时过一年半,辉煌灿烂的冬宫、夏宫、普希金艺术馆,以及波罗的海海边上壮丽的阿芙乐尔巡洋舰,竟然都慢慢地淡忘了。记忆中依旧鲜活依旧生动如初的,却是城边那幢俄式大楼的一间上海厨房。
那年俄罗斯的食品依然匮乏。每一家副食店门前几乎都排着购物的长队,无非是面包奶酪香肠和土豆。俄国人民对于排队有着无比的耐心,常常等轮到自己,食物已经售完,那么他们就默默走开,寻找到另一家商店,再接着排下去,一直到买到点儿什么为止。那队伍静悄悄地缓缓移动,秩序井然,绝无人“夹塞”,也无人争吵抱怨。湿寒与萧瑟的空气中,冷冷传递着东正教文化往日的尊严;空瘪的筐篮里,装满了购物的文明,是一种度过贫困的自信。
但我们不可能去排队。作为短期访客的我们,没有时间排队。
我们沉重的步履匆匆穿过雨雪交加的莫斯科红场,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墙下久久徘徊,走过曾在书本中熟悉的阿尔巴特街,然后远远地眺望着莫斯科河两岸金色的树叶……才是九月中旬,莫斯科已露出了冬季严峻的面孔。
肚子又咕咕地叫了起来。一行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寻找合适的餐馆。餐馆本来极少,排队等候,自己端盘,食物套餐基本只有一种,并且仅相当于国内食堂的质量。如果过了开饭时间,空荡荡的大街上,就连这样的餐馆也再找不到了。曾有一位俄国作家在家里请我们晚餐,一道生拌胡萝卜丝沙拉、一道煮土豆、一道煎小泥肠再加黑面包与果酱、果汁,就是全部了。在莫斯科的几日中,我们仅在红场附近那家最大的“古姆”(即商场)内的快餐馆,饱餐过一顿美式肯德鸡,余味绕喉终日不去。街上的美元商店倒是很多,还有豪华的大宾馆,但价格令人咋舌。而我们的住处,既是购食物难也就索性不管饭了。
于是当我们坐了一夜火车在清晨到达彼得堡,被安排住进了上海一家国际贸易集团驻彼得堡的办事处,然后迫不及待地涌入宽敞明亮的餐厅,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片加炒鸡蛋时,俄罗斯顿时变得无限光明。
那家来自上海的贸易集团占据了大楼的整整一层。楼层封闭,雇有几位俄国姑娘清扫打杂服务。除去写字间业务洽谈室和工作人员宿舍,还有二十间设施齐全的客房,专供国内来办公务的人住宿。一日三餐外加房费,共二十五美金,正符合我们“公派”的费用标准。由于价格公道,来往住宿的人很多。
那天的晚餐,居然让我们大大地吃了一惊:
八人一桌的中式套餐:白切鸡冷盘、卤猪心、油炸带鱼、凉拌芹菜、炒猪肝、土豆烧牛肉、蘑菇炖红烧肉、素炒卷心菜;米饭、白菜排骨汤。
啤酒就盛在一只固定的保温筒里,打开龙头,管够。味道绝对纯正。风卷残云一般,狼吞虎咽。吃相都难看,彼此彼此。才一个星期,就已饿得透心透肝,中国人真是民以食为天。比比老毛子,好生惭愧。
暖暖地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走进餐厅,餐桌越发地神了:
油炸榛子、煎小咸鱼、荷包蛋、酱菜,稀饭加面包片、黄油、果酱。
真以为自己是在国内了。可那榛子,明明是俄国特产,还有黄油呐。
做饭的师傅亲自来餐厅上菜,用上海普通话问你是否吃好。看那师傅不过三十出头,端端壮壮的一个小伙,几个小餐厅同时开上几桌,只他一人忙里忙外。
以后的几日,早餐晚餐每天变换花样,总有几道菜,煞费苦心地与众不同。
可这不是在上海。这是在样样食物都得排队的俄罗斯呵。
终于忍不住去了厨房察看。那师傅正埋头收拾着新鲜的猪腰子和猪脚爪。锅碗瓢盆各亮晶晶各就各位,利利索索地地道道的一个上海厨房。
用生硬的上海话与他交谈,互相便亲切起来。他说他是公派来俄罗斯的,合同三年,辛苦是辛苦些,一月二百五十美金,攒上三年还值得。
那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呢?
——自家寻啊。到自由市场去,自家一样样去寻转来。他说。其实好些东西,俄国人不吃,蛮便宜的,就是要到处去兜,碰到算数。眼睛要亮,脚骨再勤快点,都有了。只要有东西,烧烧就便当了。自家再腌点咸菜,用麻油味精一拌,味道“狭气”好。从国内来办事的人,吃得好顶顶要紧,我这个厨房是不赔也不赚的。
那你每天买菜,俄语一定好啦?骑自行车去?否则那么多东西怎么背回来?
他无奈地笑笑,摇了摇头:哪里有时间学俄语呢?一天从早忙到晚。不过心里有秤,不会俄语也一样讨价还价。俄国城市里不准骑自行车的,我天天坐地铁去买菜,从一家市场跑到另一家市场,再重再多的东西,也用手拎回来……
他忙着,便不再睬我。只知道他姓赵。后来在他宿舍的桌子上,看见过一只小小的镜框,镶着他夫人和儿子的合影照片。还知道那家国际贸易集团驻俄办事处主任姓陶,“文革”中毕业于哈军工。集团目前的生意做得挺红火。
那年在彼得堡过了美好的一周,似乎多半是因为那家上海厨房。从此对上海厨房肃然起敬,对上海人也有了较为立体的认识。如若外省人都能具备上海人那样精细的管理意识,即使再艰难困苦的条件,日子也能快快地丰润起来。
彼得堡和上海厨房,本是混头混脑不搭界的事情。但上海人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总是会把自己的那个上海,一同搬了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