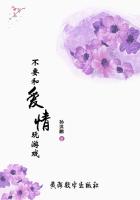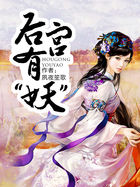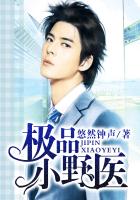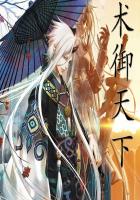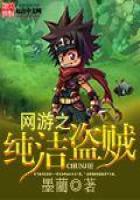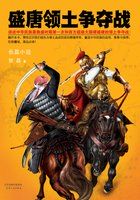渼陂
这是一方耕读文化的活化石。
这是一个能唤醒故乡情结的村庄。
渼陂古村,全然没有半星黄金周旅游的嘈杂和浮躁,披一身秋色斜阳,静静地守在公路一侧。这儿,已离了吉安市区二十余公里。
一座新落成的牌楼,矗立在村口,像庐陵文化的一个精彩序幕,后面,是厚重的历史,正在稻浪起伏的田野里发出阵阵芬芳。飞檐翘角、青砖灰瓦的“翰林第”,也即梁氏宗祠,耸峙在波光粼粼的水塘边,成为渼陂文化的排头兵。据说全村共有二十八口水塘,口口相通,如二十八位星宿忠实地护卫着村庄。雌雄两石狮把控着祠堂大门,平添了几分森严和庄重。高高的门槛内,经年的青石凹凸不平,迎面而来的亭堂上,一方“教授”牌匾格外夺目,似乎在着意提醒来客,这里是如何的重视教育,这里是如何的以儒家传道、传家。方正的天井送进丝丝缕缕阳光,送来秋天特有的芳香。祠堂共有三进,地势逐进抬高,而最恢弘的当属“永慕堂”,左右各陈设着巨鼓大钟,中央的藻井图案颜色已然漫漶,但依稀能辨出当年的盛景。两侧壁上,“忠信”、“笃敬”分列,无言地向梁家子孙也向来者训示着族规、家法,传递着中华一脉的文化源。我能深切地感受到这里的书香、这里曾经深邃的目光、这里不灭的希望。“入则孝,出则第”,多么浅显的族训,它深深地烙在每一个渼陂人的心坎。由此,也难怪文天祥亲自为梁氏家谱作序,盛赞“文献名宗”、“衣冠望族”,也难怪这里走出了一位位才子、佳丽、将军。
古村的妙趣似乎和卵石、青石板渊源极深。渼陂也不例外。马头墙比邻飞翔,形成了幽深的巷弄,踩在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上,仿佛回到童年时光。无意中一瞥,恰好见一位耄耋老太蹒跚而来,纷乱的白发在微风中拂动,让我刹那间触摸到岁月匆忙的脚步。北面长达八九百米的老街,则是由青石板路与明清建筑共同和成的一曲古乐,像久违的弹棉花的弦声,萦回在村庄的上空。可以看粮食杂货铺,可以看药材海鲜店,也可以看布匹土产人家。想象往昔的人流辐辏、熙来攘往,想象脆脆的吆喝、香甜的美食,也想象富家小姐款款地进了街边的万寿宫,向许真人许愿去。戏班子远去了,一切浮华尽消,老街上只有老人不绝的守望和富水河里不息的流水声。
站在一条流淌着阳光的老街上,我一遍遍抚摩着木门,那些粗糙的纹理,像母亲脸上的皱纹。我也来自一个村庄,那边,如今可好?
最吸引我的还是充盈村庄的耕读气息。不过一平方公里的渼陂,却曾经拥有敬德、明新、养源等诸多书院,文风之鼎盛,可窥一斑。渼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古槐第”牌楼,似乎在向后人娓娓动听地诉说着梁家先祖从陕西夏阳(韩城)迁徙的艰辛;“留有余地”墙面,似乎在阐述着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人生哲理;“求志堂”里,《百少图》、《百老图》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劳作的场面。无处不在的楹联、雕刻、香炉、太师椅、象牙床,编织出一卷内容丰富的线装书,令人阅读不尽,爱不释手。我没有一一走进书院,导游说那些建筑多已成危房。我只是在万寿宫旧址的附近,远远地仰望文昌阁直插霄汉的景象,据说那是全村的制高点,而我看来,那里系挂着渼陂千年来的希冀、理想和心结。
作为“庐陵文化第一村”的渼陂,还有一大看点便是“红色文化”。1930年2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和赣南特委及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著名的“二七会议”,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扩大红色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热烈的讨论。渼陂因此留存了大量的革命遗迹,有朱德、彭德怀、曾山、黄公略等人的旧居。我徜徉在“二七会议”会址,透过马灯、红缨枪、标语去阅读历史深处的叱咤风云、惊涛骇浪。这个当年叫“名教乐地”的书院,其厅堂里有一副对联,道是“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十分契合毛泽东的心境,备受赞赏。而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屋的寂寞,又有谁去承受?
看的古村多了,从乐安流坑、婺源乡村、瑶里、安义古村,再到眼前的渼陂,却从无审美疲惫。我乐于奔走于这些先辈们苦心经营的民间建筑中,捕捉岁月里那些细微的声息,想象一种延绵不绝的生活状态,任祖先的手掌滑过我的额头,感觉到了幸福在灵魂里拔节。渼陂再次向我展示了这种不可阻挡的美感。
我重新回到梁氏宗祠前,凝视着那飞檐翘角、青砖灰瓦,好像游子在向故园作别。一位瘦弱的老人牵着一匹披戴红花的马在兜揽生意。我听到了渼陂古老的心跳,随着水塘里的涟漪渐渐扩散,开成很美的花儿。
2007年10月4日夜于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