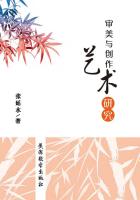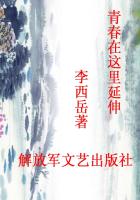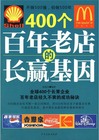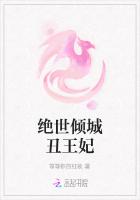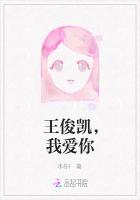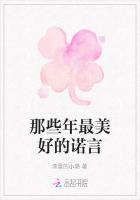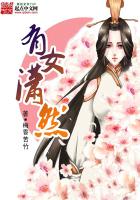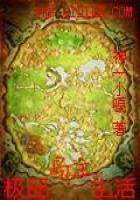在艾哈看来,推动宗教罪行成为疾病的主要是人们的社会认识,在这些认识的推动下,经历了“异常就是宗教罪”到“异常就是犯罪”,再到“异常就是疾病”的历程。[61]最初,与人们思想意识中美德相冲突的异常首先被认定为宗教罪,然后,由于原来宗教审判及惩罚的功能逐渐已被法庭和监狱所取代,原来通过忏悔或者通过宗教处罚使病人得以赎罪的方式改由法庭和监狱执行,在人们的意识中,违反宗教罪就相当于犯罪。随着现代医药科技的发展,人们发现,其实宗教罪这样的异常行为可能是由于人们的身体不正常引起的,可以在诊所通过药物进行治疗纠正,宗教罪因此又进入了疾病的范畴。基于宗教在最初划分正常与非正常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宗教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疾病,尤其是心理疾病。
人们在罪中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死。疾病是神灵所赐,不由人所主宰,而作为对于罪人的惩罚,疾病加身是理所当然,因则疾病以宗教罪的身份进入了西方人的认知思维。在品特的戏剧中,这种由宗教罪带来的苦难比比皆是,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他戏剧中的人物几乎人人都是病人,不是生理上的,就是精神上的。然而,对于这种宗教罪,品特是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他的疾病叙述是对宗教文化一种弘扬,还是一种消解?三、疾病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消解
从品特的疾病描述来看,他对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持有的是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文化,而非弘扬。
首先,在品特看来,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救赎的世界。在文明距离还远在地平线外的时刻,患病的人们通过对神或上帝的忏悔以治疗自己的疾病。在民众看来,许多神灵在具有其他法力的同时,也具有治疗疾病的法力。例如宙斯既被称为“救世主宙斯”,又在某些地方被尊崇为“医神宙斯”。雅典娜既被称为“智慧女神”,而又通常被当作“健康女神”。最为著名的西方医神则是阿斯克勒庇俄斯,传说中他是阿波罗的儿子,半人半马怪喀戎的门徒。那时的治疗几乎完全是一种信仰治疗。患者带上祭品,来到神庙,焚香祷告,祈求神灵宽恕,恢复健康。在基督教徒中,许多人也对上帝的救赎深信不疑。救赎的教义源于圣子耶稣以自身的血肉之痛,换取了上帝对于民众的拯救。于是,在疾病暴发的时候,一些基督教徒也寄希望于自身的修行以拯救苍生,据记载,在基督教早期,一旦国内危机、疾病、瘟疫爆发,人们往往聚集起来集体修炼,鞭打自己或互相鞭打以赎罪,以期神灵宽恕。[62]这似乎看来有点宗教狂热的意味,但也印证了人们对于救赎的深信不疑。然而对于上帝的这种信任,在1852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遭到了挑战。尼采更是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喊出了亵渎神灵的“上帝已死”的口号,在西方人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带来了悲观绝望的情绪。
作为荒诞派戏剧的哲学根基的存在主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宗教悲观思想,它在哲学的基本问题———判断人的生存价值上与理性思想截然对立。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来到世上纯属偶然,并且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同样,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也将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这样说来,人类和生活本身就毫无意义,或者说是荒谬的,所以人的存在是个荒诞不经的事实,他们被抛到世界上来演出了一场不幸的闹剧,既可笑,又可悲,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
在此基础上,存在主义所宣扬的种种看法,都带有否定理性观念,充满悲观绝望的情绪色彩。如人们用于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在他们看来,就是一堆杂乱的音节拼凑,除了显示这种拼凑的荒唐可笑之外,别无它义;当然,据此推论,语言所要表达的理性逻辑也是不存在的,它充其量是人们的自我欺骗而已。存在主义者又宣称: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任何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的存在毫无价值。然而怎么解决呢?加缪说过:“我们……如何自杀?”这种思想反映出对人类前途的彻底绝望。
这种宗教的绝望,在荒诞派剧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反映。例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常常被阐释为一部表达了人类对上帝深深失望的剧作。剧作中的两个流浪儿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岗彻日彻夜地等待代表着上帝的戈多,然而,戈多始终没有来,拯救他们的上帝在哪里?拯救人类的上帝又在哪里?这种深深的绝望也弥漫在品特的戏剧中。在作为西方宗教源头的《圣经》中,上帝多次对于人类施加疾病,也多次对处于病痛中的子民们伸出了援手。在《福音书》中,作为上帝的儿子与使者,耶稣救活了许多人。例如在迦百农,有一个百夫长的仆人患了瘫痪病,百夫长面求耶稣,于是耶稣治好了百夫长仆人的瘫痪。耶稣到了彼得家里,彼得的岳母害热病,于是耶稣“把她的手摸一摸,热就退了”。在加大拉,耶稣又治好了被鬼魂附体的人。在自己的城里,耶稣又治好了一个瘫痪病人,还用手按在睚鲁的女儿身上,使她复活,并使摸自己衣服的患了十二血漏病的一个女人病愈。接着,碰到两个瞎子,耶稣用手摸他们的眼睛,他们就复明了。跟着又治好了被鬼魂附体的哑巴。(《新约·路加福音》9:43 )然而,在品特的戏剧中,病人却从来没有得到拯救,他们好像已被上帝抛弃了。品特的其中一部剧作《归于尘土》,在剧目上就表明了这种意蕴。“归于尘土”最初来自于《圣经》,全句为“尘归尘,土归土,让往生者安宁,让在世者重获解脱。”(《旧约·创世纪》3:19 )最初意指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被上帝责罚,逐出伊甸园,从此需要依靠劳作得食,且生命不再无限,终有一天归于尘土。整个句子表达出一种空虚失落的哲学意蕴,读来让人有一股淡淡的忧伤:你是什么就终究是什么,生命轮回,从哪里来就会回到哪里去。品特选择《圣经》这一词条作为他这一戏剧的题名,表达了他的内心对于人类过去行为及明天前景的失望。还是在《归于尘土》中,丽贝卡与她的心理治疗师谈到了上帝:
德夫林:我在帮你摆脱困境,你注意到了吗?我在帮你脱身,也许是我想要脱身。这很威胁,你注意到了吗?我掉进流沙中了。
丽贝卡:就像上帝。
德夫林:上帝?上帝?你认为上帝掉进陷阱里了?这就是我要称之为特别讨厌的概念的东西。如果它配得上概念一词的话。小心,不要随便议论上帝。他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上帝。如果你把他赶走了,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也甚至不会再回头看一眼,到那时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会怎么样吗?这种空虚。[63]
在丽贝卡看来,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已经动摇。当德夫林说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上帝也处于同一处境。德夫林看来是上帝的虔诚追随者,他对丽贝卡对于上帝陷入困境的说法很是气愤,他的所言恰是一番宗教劝诫。然而,在他声色俱厉的口气当中,也让人感觉到他的底气不足,他已切身体会到信仰缺失带来的危险,“这种空虚”就是他自己的感受。西方世界上帝信仰的危机,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品特的戏剧中,还透露出对于基督教宣传的“仁爱宗教”的怀疑。在《摩西十诫》中,对于亲情,明确规定:“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旧约·出埃及记》20:12 )而对于爱情方面,则规定“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旧约·出埃及记》20:14 )在《利末记》中,又颁布了“有关淫乱的禁令”,其中规定“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不可与邻舍之妻行淫,玷污自己”。(《旧约·利末记》18:20 )耶和华警告说:“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了它的居民。”(《旧约·利末记》18:24 )《圣经》中的这些条例展现了基督教是仁爱宗教的依据,也奠定了西方的亲情人伦观。然而,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在品特的戏剧中是司空见惯,甚至是触目惊心的。
首先品特戏剧中多处呈现畸形的母子心理。子女在母亲的子宫中孕育,母亲对于孩子的关爱是极其理所当然的。然而,在现代医学看来,过度的关爱孩子其实是一种精神疾病,体现了父母对于孩子的焦虑。“焦虑的准备似乎为有益的成分,而焦虑的发展则为有害的成分”,[64]在品特的戏剧中,某些母亲起初对于孩子的关爱出发点是正确的,然而对于害怕失去孩子的焦虑,使得他们竭力去控制孩子,这时,这种情感就变得有害了。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有两大特点,一是焦虑中包含普遍的忧虑。第二个特点是焦虑常附着于一定的对象或情境上。[65]孩子最容易成为父母情感的附着对象,而父母担心孩子的成长,这就是一个普遍的忧虑。然而,这种畸形母爱培育出来的孩子,有可能是表现出来的是不能离开父母的恋母情结,或者刚好相反,是一种厌母情结。在《一夜外出》中的母亲与儿子之间,就展现出了这种关系。戏剧一开始,儿子阿尔伯特( Albert )正四处寻找领带,以便穿戴整齐外出。他的母亲却唠叨不休,不停地打听阿尔伯特的去处,不断嘱咐阿尔伯特要洁身自爱,不能与女孩子鬼混,并想方设法留住他在家吃晚饭。阿尔伯特为了离开家,用尽了各种办法,他一再声明是去参加一场欢送离职同事的晚会,信誓旦旦地承诺自己不会与女孩子鬼混,终于摆脱了母亲的纠缠。然而在回来后,再次遭到了母亲的盘问,阿尔伯特越来越不耐烦,终于将闹钟恶狠狠地扔向了母亲,逃离了家中,并真正地跟妓女混在了一起。阿尔伯特的父亲已经去世,他是孤寂的母亲的唯一安慰,她对儿子倾注了所有心血,也正如此,她的爱表现得有些过分了,演变成了对儿子的情感控制,这正是害怕失去儿子焦虑的表现。弗洛伊德深信,焦虑通常来源于力比多的压抑,失去了丈夫的阿尔伯特的母亲只能将力比多转换为对儿子的情感占有。然而,这种荒谬对于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妇女来说是又正常的,儿子却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剧中展现出来的亲情关系是那么的不和谐,阿尔伯特的行为不用说也不能算是“孝敬父母”。
在品特的另一部广播剧《家的声音》中,同样展现了畸形的母子心理。全剧由母亲的声音、父亲的声音、儿子的声音展开叙述。从他们的叙述中得知,儿子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离家出走了,在一个旅馆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将旅馆的男女主人当作了自己的父母,将他们的女儿当作了自己的姐妹。在儿子的声音中,仿佛也充满了对母亲的思念,但更多的却是对于逃离了父母的生活的欢乐和自由的表述。他这样对母亲说:“如果你发现我迷惑、焦虑、不确定和害怕,那么你也发现我的满足,我的生活有形有色。”[66]“啊,妈妈,我已找到了我的家,我的家庭,我以前从未梦想过竟会有如此的快乐。”[67]有一次,他的母亲和姐姐曾找到他住的地方,打听他是否住在那里。当时儿子就躺在旅馆的浴池中,清楚地听到了外面的谈话,但他却无动于衷,任凭新家的“父亲”将他真正的母亲和姐姐赶走,并庆幸父亲没有来打扰。而在母亲的声音中,当然也充满了对儿子的思念,并且从母亲的声音中得知,父亲在寻找他的过程中死亡了,母亲给儿子写了信,但却没有回音。在母亲的声音中,包含着复杂的情感,既有她凄婉的声音:“儿子,你在哪里?我很想你,是我给了你生命”,[68]又有她愤恨的声音:“如果你还活着,你就是一个怪物,你爸爸在临死的床上诅咒你……现在,我也要诅咒你,我要祈祷,愿你的生活充满痛苦。”[69]终于母亲报了案,让警察去寻找她儿子:“警察在追查你,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未满21岁……我怀疑你很有可能落入了黑帮的手里,也许是他们在强迫你做男妓……他们会找到你的。孩子,到那时,我决不会对你留任何情面。”[70]最后,父亲在坟墓中也发出了声音,看来也似充满感情,但也不乏不信任:“是你在诅咒我的死亡,我听到了你的诅咒,它们在我耳边回响。”[71]显然,离家出走的儿子也是嫌弃父母的控制,他看似思念的情感中却包含着太多的冷漠无情,而对父亲的死亡、母亲的生病也无动于衷,任由近在咫尺的母亲与姐姐擦肩而过。而母亲与父亲看似思念的情感中体现得更多的也是一种责任和控制,母亲所说的“你是我生的”“我决不会对你留任何情面”表露出她的控制心理。当久寻儿子不见后,母亲的心理也扭曲了,她给予儿子的不再是祝福,而是诅咒,将儿子交由警察寻找,公事公办,显示出她对于情感的失望与冷漠。
品特戏剧中的“家”不再是温馨的港湾,而是一具徒有其表的空壳而已。上、下两代人均表现出病态的心理,他们之间存在是的是一种畸形联系:下一代人视亲情为控制,视家为囚室,他们只想逃脱控制;上一代人显示出的更多的是责任感,是控制下一代人的愿望,他们之间存在的更多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以仁爱为核心构建的家庭纽带不再牢固,上帝提倡的亲情观被颠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