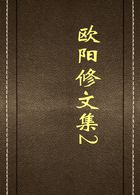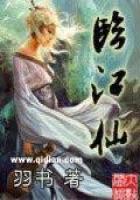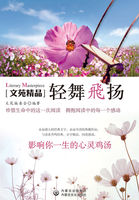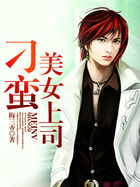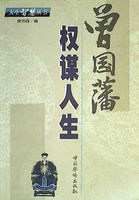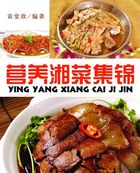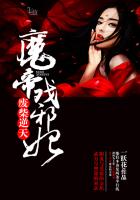舒绣文是安徽安庆人,幼年时由于其父母双双失业,家贫如洗。她捡煤渣、拾破烂、洗衣服、当小保姆,什么苦活都干过,小小年纪就负担起全家的生活,磨练出坚韧意志。
1931年春,16岁的舒绣文只身闯上海,经人介绍给“天一”影业公司的老板娘补习国文,总算有了立足之地。公司拍片时,她喜欢站在摄影棚外,欣喜地观赏那魔术般变幻的场景,津津有味地咀嚼剧中人的对话,她被这门新奇的艺术迷住了,常常错过开饭的时间。
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天一”影业公司老板邵醉翁看中,让她担当我国第一部蜡盘录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配音演员,那是因为某些演员的国语不过关,嗓音不圆润。而正值花季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配音配到忘情处,语言感情发挥极佳,往往一次就能通过拷贝。配音虽然是幕后工作,也足令她兴奋快乐,摄影棚钻得更勤,人此与银屏结缘。
舒绣文身材娇小玲珑,面容清秀,正是一棵有希望的艺术苗子。不久,邵老板又让她在故事片《芸姑娘》中扮演一个小配角,想观察她上镜的效果。可是年轻的舒绣文毕竟没有拍片的经验,开拍那天,耀眼的灯光晃得她睁不开眼,她顿时紧张得手足无措,连烂熟于心的台词也忘得一干二净。心疼胶卷的邵老板大发雷霆,当着众人的面责骂她没出息,一向自尊的舒绣文当场愤然离去,并暗下决心要做一个出色的演员。
离开“天一”公司后,舒绣文听说田汉、田洪兄弟在杭州组织“五月花剧社”,乃前往报考,经田汉面试,认定她有天赋,遂吸收这个小姑娘入社。她勤奋学习技艺,接连在话剧《名优之死》、《活路》等剧中担任角色。
1933年,上海“艺华”影业公司选中田汉编导的故事片《民族生存》投资拍摄,舒绣文随田氏弟兄返沪,在片中扮演一个被遗弃的少妇,这是她真正参加演出的第一部影片,封镜后受到好评。接着,她又在阳翰笙编剧的《中国海的怒潮》一片中,扮演奸商的妻子。这两部影片使她在影坛上崭露头角,成为观众瞩目的新秀。
1934年中,舒绣文转入“明星”影业公司任专业演员,她先后在《劫后桃花》、《热血忠魂》、《夜来香》、《清时时节》、《女儿经》、《梦里乾坤》等十多部影片中出演,名嘈全国,成为明星演员。她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但从不摆什么架子,姐妹们有事都爱找她倾谈。
抗战爆发后,不愿做亡国奴的舒绣文义无反顾离开环境优越的上海,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她与史东山、黎莉莉、魏鹤龄等人一同到武汉,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那里主演了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
武汉失守,中国电影制片厂迁移重庆,厂址设在观音岩纯阳洞,全厂员工随迁,舒绣文与王士珍在张家花园65号租房安居。日本飞机的残酷轰炸,不仅未能吓倒她,反而激发了她工作的热忱。冒着敌机的空袭,她参加了影片《好丈夫》和《塞上风云》的拍摄。
从重庆赴内蒙拍摄《塞上风云》时,“中制”剧组途经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文艺界的热情接待,这新天地里的火热生活深深感染了他们。对比重庆和延安,舒绣文觉得好似走过了两个不同中国,自称受到“莫大的教育”。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朱德接见了他们,并在他们的纪念册上题词:“抗战、团结、进步。”
这既短暂又难忘的经历,更加坚定了舒绣文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决心。回到重庆,她又结识了周恩来、邓颖超,时常聆听共产党人的教诲,对她的成长与觉悟起到很大作用。
1941年夏,由中共组织领导的“中华剧艺社”在重庆成立,舒绣文立即加入,她和张瑞芳同台主演该社的第一个话剧《棠棣之花》。1942年郭沫若创作出新编历史剧《虎苻》,她在剧中扮演如姬。随后,她又在阳翰笙创作的话剧《天国春秋》中扮演女主角洪宣娇,借剧中人之口,公开抨击国民党顽固派,备受观众推崇,但凡她出场演出,总能听到观众席上爆发的会心的掌声。
在渝期间,舒绣文还先后参加《蜕变》、《闺怨》、《为和平自由而战》、《雾重庆》、《雷雨》、《日出》、《民族万岁》、《清宫外史》等20多部话剧的演出,为宣传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四大名旦”之一。
舒绣文在艺坛享誉较早,在女明星中又属年长,被姐妹们尊称为舒大姐。抗战胜利后,她随《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组回上海,因在该片里塑造“抗战夫人”王丽珍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登上了电影表演艺术的高峰。
1969年3月,舒绣文被“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终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