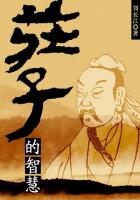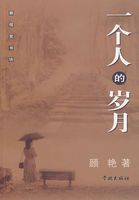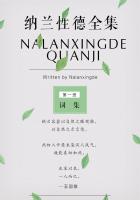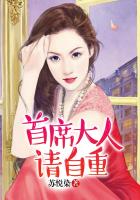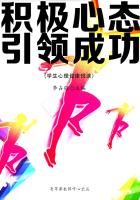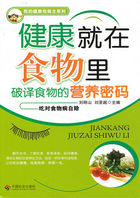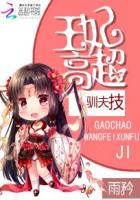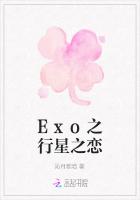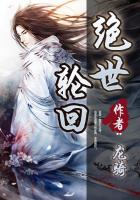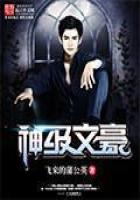于伶原名任禹成,1907年2月出生在江苏宜兴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到上海任“左翼剧联总盟”组织秘书,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从1933年到1937年,他怀着炽热的革命激情,密切联系当时的现实斗争,陆续写了《夜光杯》、《汉奸的子孙》、《腊月二十四》、《夏夜曲》、《回声》、《蹄下》、《在关内过年》、《浮尸》、《血洒晴空》、《以身许国》等40多个独幕和多幕抗日话剧。1934年至1935年,他用“尤兢”等笔名为《申报·电影专刊》每天写一篇电影评论文章,批评“软性电影”论,名噪沪上。
“七七”事变后,于伶担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部长,迅速帮助戏剧、电影界同人组织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和三个战地服务团,一个京剧界救亡协会。“八·一三”后上海沦为“孤岛”,他担任中共上海局文委委员,先后组织了青鸟剧社、上海艺术剧院、上海剧艺社,公演大量新作和世界名剧,宣扬民族气节。
于伶在“孤岛”艰苦奋斗,被赵景深喻为“最卖力气”的人。于伶自己也在《给R.S ——〈花溅泪〉代序》一文中直率地说:“自己既是爱定了演剧这迷人的武器的艺术,失败了可以重来,跌伤了我会支撑的。因为自己还年轻,自信有着充分的勇气来接受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武器只有在锻炼与使用中才能具备与发挥其战斗力的。”他在“孤岛”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长江局书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和党内表扬。
1943年元旦,辗转从香港、桂林来到重庆的于伶,到红岩村参加了新年联欢晚会,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在谈话中,周恩来详细询问了“孤岛”几年的戏剧和文艺运动状况,有不少人和事,连他这个在上海住了许多年,而且天天在文艺圈中生活的人都差点交不出答卷来。尤其令于伶惊叹的是:周恩来竟能如数家珍般地一一评说他那些作品的成就与不足,话虽不多却一针见血,又说得委婉体贴,很能体会“孤岛”作者的甘苦。周恩来甚至具体到能说出于伶在剧作中通过角色说的一句台词:要到“老远老远,很苦很冷的地方去”,是暗指的延安,并肯定说在“孤岛”那样的环境中这样写很好,观众一听就会明白。这使于伶十分感动。
此后,于伶遵照周恩来指示担任了南方局文委委员,与夏衍、章泯、宋之的、司徒慧敏、金山等组织中国艺术剧社,坚持在重庆、桂林从事进步戏剧活动。
1943年6月,周恩来要回延安参加整风,行前邀请戏剧界朋友到郭沫若家聚会,商谈下一个雾季上演哪些剧目。
当话题谈到于伶的新剧《杏花春雨江南》时,郭沫若赞赏说剧名好,有诗意。导演孙师毅兴冲冲地告诉大家,于伶还打算再写一个剧叫《骏马秋风塞北》,是以沙汀的报告文学《记贺龙》作为素材的。人们纷纷称赞于伶雄心不小。这时周恩来却亲切地看着这些活跃的艺术家们,严肃地谈起了他的反对意见:“沙汀的书,只是记下贺老总的几点印象,写书还可以,写剧本,不仅要能深刻理解和熟悉全面的贺老总,还必须深刻理解和熟悉他上下左右的人与事才行。”
于伶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毅然放弃了《骏马秋风塞北》,参加到他有生活积累的《戏剧春秋》的写作中去。年底由夏衍、宋之的、于伶合编的话剧《戏剧春秋》在渝公演,深刻反映了中国话剧工作者30余年来血泪交加、顽强奋斗的艰苦历程,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获成功。他还与夏衍、宋之的合写了《草木皆兵》,独自改编了《大马戏团》等多幕剧。
在于伶的剧作里,反映“孤岛”上海的生活的,除了《夜上海》外,还有《长夜行》等。1945年9月27日,重庆《新民晚报》曾载文评论于伶说:“试追迹于伶进步的道路,一个主要的因素,应该是他不曾自己关起房门来做一个为戏剧而戏剧的戏剧家,十四五年的战斗实践,特别‘七七’以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3年间在上海的战斗实践,确实的帮助了他。那一份艰巨的任务在于伶的肩上,并未曾使他无暇执笔,相反的,正磨炼了他的笔。”
抗战胜利后于伶重返上海,领导进步戏剧运动,写了电影剧本《无名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