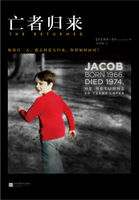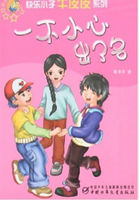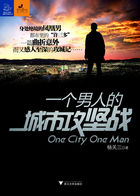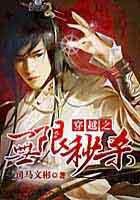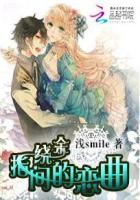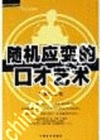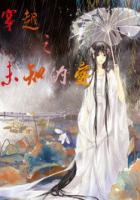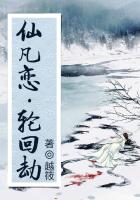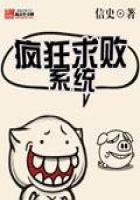没办法,我向她们问起“北阳”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这是她们高中母校的校名。不过,并不是大阪那个在甲子园声名赫赫的北阳高中,而是埼玉县的一所学校。她们上学时是垒球队的成员。
我们聊着聊着,拍摄已经开始了。过了不久,就像之前说好的那样,助理导演过来叫我们,于是我们听话地跟着他走了。“北阳”的两位牢记自己演的是智力问答节目的参加者,嘴里还一个劲地念叨着“一定要加油”、“不知道会出什么题目”之类即兴发挥的台词。真是太厉害了。
正当我以为总算完事了,刚要松口气的时候,却被告知这只是彩排。什么?这种戏也要反复拍好几遍?我有点儿不耐烦。但是转念一想,我只是个跑龙套的,不管演几遍都要拿出演技全情投入的是主演藤木先生才对。
在全体工作人员为下一次开拍做准备时,我与井坂导演聊了几句。他说虽然经常下雨拖延了拍摄进度,但是大体上进展还算顺利。
说到井坂导演的作品,以《Focus》和《Mr.Rookie》最为有名。有趣的是,这两部影片的风格迥然不同。《Focus》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实验性电影,只通过一台摄像机就展现了电视人扭曲的生活与无线电狂人的疯癫。与之相对,《Mr.Rookie》则充满娱乐性,可以被称为日本的《大联盟》①。我并非要评论哪部好哪部差,只是井坂导演对于各种电影都要拍拍看的态度让我很有共鸣。这或许是因为我一直都相信好作家应该各种作品都能写吧。
话虽如此,在导演面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于是话题很自然地从《Mr.Rookie》转到了一路过关斩将的阪神虎队。据说井坂导演在执导《Mr.Rookie》之后,也开始支持阪神队了。他本人曾经是东大棒球部的成员,现在每周都去参加草地棒球比赛。看到与我年龄相仿的井坂导演精力如此充沛,我感到很受鼓舞。
言归正传,那段戏后来又反复拍摄了好几次,我和“北阳”的两位每次都聊些不同的话题。一开始很紧张,总是想着拍摄的事,但渐渐地就能交谈自如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很了不起嘛。最后导演说“OK”的时候,我们好像正聊到我最喜欢的滑雪运动。我期待着在电影上看到自己的表现到底怎样,不过我的镜头应该也就只有几秒钟而已。
写在电影《湖边凶杀案》上映之际
(电影宣传手册 二〇〇五年)
我写小说时,首先在脑海中形成映像,就像是电影中的一幕幕场景。以我满意的形式“拍摄”完毕,再用文字把这部分表现出来。如此反复,一本小说就写成了。当然也有例外,不过《湖边凶杀案》大概也算是这种创作方法的典型了。出场人物的心理描写一概排除在外,就连主人公的思想活动也仅通过行动和对话展示。
但是,我从未想过这部作品会被改编成电影。小说中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一幢别墅中,出场人物很少,主要事件也只有一个。而我一直深信电影必须要有华丽的大场面才行。
然而,这次这部作品却被搬上了大屏幕。看到剧本时,我有些惊讶,改编水平之高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完全就是一部舞台剧。故事比原著更加精简,出场人物也更少。改编者在突出主题上煞费苦心。作为外行,我觉得这部作品成功与否将取决于演员的演技。
看了创作完成的电影,我兴奋不已。明明是自己写的故事,却猜不透结局,一直紧张到最后一秒。我的小说脱胎换骨,衍生出一部如此精彩的作品,让我这个原作者感到无上光荣。
写在电影《变身》上映之际
(电影宣传手册 二〇〇五年)
十五年前,我在住宅之外另设了一间工作室,每天早上乘公共汽车再转乘电车前往那里。某天,在公共汽车上我突然想到:“人的大脑分为左脑与右脑,如果其中一半与其他人的大脑交换会怎样呢?”当然,这个想法也不是凭空而来,当时我对人脑很感兴趣,读了好几本相关著作,所以才会产生这个疑问。而这个疑问又转化成小说的灵感,我下车的时候已经构思出大部分故事情节了。整个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左右。
本来,这种灵感突然涌现的情况在我身上很少发生,甚至可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平时我都是绞尽脑汁,想破头才想出来的。
那时,讲谈社为庆祝建社八十周年而推出特别企划,邀请我写一部新长篇,所以我就决定写写这个替换半边大脑的故事。这就是《变身》。
这是我出道六年以来写的第十四部长篇小说。当时,我的书根本卖不动。我暗暗期待《变身》这本书能卖得好一些——不求有惊人的销售量,只求能造成一点儿话题就好。
但是,《变身》依旧卖得很差。评论家对此书视而不见,文学奖也没能入围。屋漏偏逢连夜雨,讲谈社的特别企划突然中止,也就是说,连宣传的机会都没有了。
此书虽然命运多舛,但是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影视圈的人来找过我几次,希望把这本小说改编成电影。在我的印象中,这些企划到最后基本全军覆没,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有人带着同样的企划找上门来。
我一般是先在头脑中形成映像,然后再用文字表述出来。而且,比起文学性,我更注重作品的娱乐性。所以对于影视圈的人来说,也许更容易把握我作品中的意象。但从相反的角度出发,文学评论家就会觉得我的作品比较低俗吧。
在这样的背景下,《变身》终于改编成电影。看过试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竟然拍得如此出色”。电影中包含了我试图通过小说传达的所有信息。两位年轻的主演把主人公的痛苦、恋人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另外,此前所有改编企划案中认为必须改动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也几乎没有变化,我要向以导演为首的所有工作人员致以敬意。
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看这部电影。
“搞笑”的教材
(致立川志之辅先生的个人专场演出)
我出过两部短篇小说集——《怪笑小说》和《毒笑小说》,怎么好像一上来就自我宣传似的?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推理小说家,但是这两本可不是推理作品。我想很多人从书名就可以推测出两本都是以“搞笑”为主题的。
推理作家为什么要写这种书呢?首先是因为我喜欢。当然,不是喜欢写,而是喜欢读。但是近来可以写出能把人逗笑的小说的人真是越来越少,因为文学界普遍认为“搞笑小说”的地位低下;比起让人发笑的作品,那些读后让人心情灰暗的书似乎格调更高。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不少人怀疑写“搞笑小说”很轻松。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和同为“搞笑小说”支持者的京极夏彦先生都很愤慨。让人笑的表演比让人哭的表演不知要难多少倍,同理,写出让人笑的作品也非常困难。事实上,这就是我写这两本书的第二个理由。换句话说,写以“搞笑”为主题的作品对我而言,是作家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种修行。
写这类小说时,落语②是绝好的教材。分析古典落语中的段子和结尾的包袱,就会发现其实每个部分都经过精心编排,把观众瞬间引入故事世界,并精准戳中他们的笑点。我在阅读落语的时候心里一直在默念:“真是了不起!”
难道不能在小说中展示落语的世界吗?构思“搞笑”作品时,我总会这么想。我有一个短篇小说名为“要杀就趁现在”,落语爱好者肯定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向古典落语名篇《要死就趁现在》致敬。
正当我拿落语当范本创作小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立川志之辅先生提出要以我的小说为蓝本创作落语。得到他青睐的就是之前提到的《怪笑小说》中收录的《尸台社区》这个短篇。对我而言,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那种作品承蒙您不弃,尽管拿去用好了。”我怀着送笨闺女出嫁的心情再三低头行礼。
公演那天我十分紧张——要是观众觉得不好笑可怎么办?要是观众觉得无聊想要退场可怎么办?我坐在车里,一路都在忐忑不安。
但是,我的紧张完全是杞人忧天。改名为“尸体的下落”的落语极其有趣,就连我都猜不到结局。邻座的一位女观众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放心的同时也受到了强烈震撼,因为我明白让观众爆笑的不是我的故事,而是志之辅先生的表演。当然,落语的魅力也不仅仅取决于段子。
把落语的艺术通过文字展现——这正是我当前的目标。
写在电影《信》上映之际
(电影宣传手册 二〇〇六年)
每天都有恶性犯罪发生。我们看到这些报道时会感到震惊与愤慨,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渐渐淡忘。就算还记得,一旦犯人被逮捕,我们也只会感叹一句“啊,真是太好了”,然后在心里把这件事画上句号。对大多数人来说,“犯罪事件”就是这么一回事。
直到接触到与这类犯罪事件的判决相关的信息时,我才意识到事件其实尚未终结。很早之前就应该已经解决的事件,竟有许多人在多年后仍未得到解脱,认识到这一点让我非常吃惊。
我首先想到的是凶杀案中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时而要为嫌疑人在法庭上是否说实话而烦恼不已,时而又要为法官能否依据法律定刑而寝食难安。当然,失去所爱之人的痛楚更是无法摆脱。社会大众将他们视为“受害人家属”,也许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对当事人来说,“犯罪事件”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呢?不,该问的是,真的能够结束吗?
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推理小说,而且写的主要都是凶杀案,真相大白时故事也就完结了。但是偶尔我会突然产生疑问,自己真的把“案件”全貌都写出来了吗?凶手被捕,警方的搜捕活动停止之后,案件相关人士永无止境的痛苦是不是也有必要写一写呢?
于是,我决定写《信》这部小说,故事聚焦于加害人的家属。
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要如何对待他们。如果身边有类似遭遇的人,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写这部小说就是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连载期间,我一直很苦恼。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都不是用简单一句“不能差别对待”就可以应付的。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长期遭受欺凌,他从自身的经验中又会找到怎样的解答呢?我写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
然而,小说的最后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写完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道无解之题,从一开始便矛盾重重。你问是怎样的矛盾?矛盾就是无法脱离与他人联系的人类却杀害了其他人类。
不过,世间本就充满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如此痛苦。直面无解之题却只能束手无策。
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十分精彩,非常尊重原著。演员们的表演令人感动。看过的人内心大概都会受到强烈的冲击吧。
不过,我不希望大家误会,如何与加害人家属相处这一问题其实并不需要答案。不得不慨叹的是,我们竟然必须要寻求这一答案。
①一九八九年上映的美国经典棒球喜剧电影。
②日本的传统曲艺形式之一,无论是表演形式还是内容,都与中国的单口相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