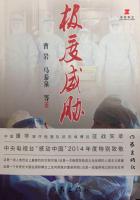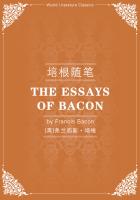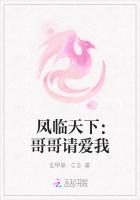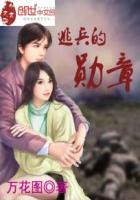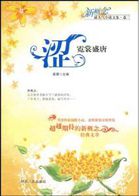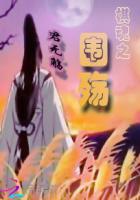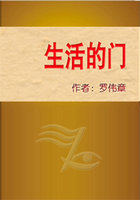一、方便面
人类记忆有一个特征,即对凡已融入日常生活的发明,往往认为是极简单之事,而对这些发明的灵感来源及最初时间不太在意,方便面的起源即是一例。
今天,人们公认方便面起源于日本。发明方便面的是一位名叫安藤百福的日本人,他是生在台湾嘉义县的一个孤儿。据说是在一九三三年,安藤回到日本,受寒风中人们早起排队等热面的情景触发,在一九五八年前后,安藤发明了方便面。办法是用油炸完的面,等着泡水。面炸过后会出现许多细孔,这些孔能吸收热水,面很快变软,物理成因相当简单。方便面的雏形是鸡汤面,安藤夫人启发了丈夫,面油炸后能贮存;儿子喜欢鸡汤面,这使安藤下决心,让方便面从鸡汤味开始。
方便面的发明史大致如此,太平淡了,但这个平淡中体现了所有古老智慧,要将这种古老智慧与现代生活适时结合起来,则需要另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可以说就是一种机遇。
人类最古老的智慧通常也是最高智慧。保存食物的动因源于防止意外灾害的生存直觉,而保存食物的原初智慧一是脱水,干;二是加盐,味。在现代防腐技术出现前,这是人类的共同智慧。方便面的存在和流行,思路建立在这两点上,食物不变坏而且还能有味道,办法是开水冲泡鸡汤。
如果就方便面的发明灵感和雏形判断,我能找出一个远早于安藤方便面的实例,这就是厦门早期的鸡蓉面。
二〇〇七年,我南来教书后,偶然在厦门旧书摊见到一册一九三一年谢云声等人合编的《厦门指南》(厦门新民书社发行,民国二十年)。我在这本书后看到一幅广告。由这则广告知道,这种鸡蓉面的牌子是“冠德”。它的广告词是“鸡蓉面,旅行第一,滚水泡下,甘芳适口”,这个广告放在今天推广方便,也无不可。由同书另一广告可知,当时厦门有一家陶园商店,在它推销自制的食品名单中,我看见排在第一的即是“始创鸡蓉面”。其他地方有无类似的食品,我没有查考,但以中国人的聪明推断,想来不会是只有厦门一家吧?
一九三〇年代的厦门生活,想来今天还有健在的人可以忆及,我没有去访问那些吃过鸡蓉面的老者,也想象不出那面的味道,但我感觉与今天的方便面是一种灵感的结果。厦门离台湾最近,而当时来往频繁,说不定在台湾嘉义出生长大的安藤,儿时即有食鸡蓉面的经验,成年后这个记忆诱发了他的灵感。
方便面的发明权是确定的,这是安藤的幸运。我想说的是古老智慧,一定要与现代生活适时配合起来,才能产生另一种智慧。方便面的流行建立在社会成员生活节奏普遍加快和工业化技术的普遍应用上,舍此,则古老智慧不能发生作用。从技术发明的灵感来源观察,我们可以将方便面发明的灵感和时间推前,甚至可以将这个灵感移到厦门来,但在缺乏快节奏生活和工业技术化的前提下,再超前的智慧,至多也只能产生一种类似点心那样的食物,而不可能产生一种广泛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食品。
鸡蓉面的出现,可以说已具备了后来方便面的所有发明灵感——干,宜于保存;泡,吃起来是热的;鸡汤,有味道——但方便面还是没有在中国诞生,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现代节奏的职场生活,自然也就没有这个巨大需求。没有相当的技术条件,即令有需求,也不可能大量生产来满足。在日本,也只是到了一九六〇年前后,需求和生产技术才适时配合起来。
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但我们总是错过那个最佳时机,我们今天还在重复这种命运,但愿下一次伟大的发明是源于我们的智慧,而上天又给了我们最佳时机。
二、洋装书
二〇一二年三月间,我寄了一本《常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给深圳的胡洪侠,书是毛边的,估计他会有点兴趣,我知道他喜欢书。
隔日就在书店看到洪侠兄的新书《微书话》,非常精致,令人爱不释手。其中有一则提到,陆灏曾问过他,中国第一本洋装书是何时出现的,是什么书?他说一时还没有查清楚。我对这件事稍有兴趣。
中国书籍的装订工艺,经过筒策、卷轴、旋风、经折、蝴蝶等装订形式的演变,最后稳定在线装上。它的特点是在整合的书页上右边打眼,明线装订。好处是简洁、美观、方便,短处是单册书页不能太厚,线的寿命有限。装订技术是由印刷工艺决定的,中国雕版印刷的特点是单页单面刷印,对折整合,所以线装是这种工艺的最佳选择,显示最高智慧,手工时代,找不出更好的方式了。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讲过一个道理,社会事物由繁向简。在书籍的装订上也能体现。
洋装书有精平装两种,工艺原理大体相同。早期以锁线加外封面为主要形式,后来以胶装为流行工艺。洋装书的好处是体积小容量大,单页双面多版印刷,是典型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世界图书的最终形式稳定在洋装形式上,肯定是它的优点明显。世间事物,一定是优点多的取代优点少的。
严格说出中国洋装书出现的精确时间和具体书目,可能不是很容易。实藤惠秀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断定的时间是一九〇〇年,举出的实物是一本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教科书《东语正规》(唐定锷、蕺翼翚著),这本书虽由中国人编写,但却在日本印刷完成。作为一种新的书籍装订形式,在一般流行意义上,洋装用了约五年时间,完成了取代线装的过程,时在一九〇五年,这个时间很有意味,中国的科举制度恰好也是这一年废除的。
如果界定中国洋装书的出现,除印刷技术条件外,至少还应考虑四个因素:(一)汉字;(二)中国人著译;(三)中国本土印刷;(四)洋装。
实藤惠秀注意到一个特点,中国早期洋装书版权页上,一般都是清朝纪年和“明治”年号共用,所以他判断这些书都是在日本印刷完成的。考虑这个特点,同时满足上面四个条件的洋装书,一时还不好确定。
实藤惠秀还提到一本成濑仁藏的《女子教育论》(杨廷栋、周祖培译),一九〇二年由上海作新社出版,这是一家设在上海的出版社,由蕺翼翚和一个日本人合作创立,专门出版洋装书。我手边恰好有这本书,但它的版权页上,没有清朝的纪年,只有“明治”年号,虽然标明出版地设在“上海大马路泥城桥”,但印刷是在“东京并木活版所”完成,所以,也还不能认为是纯粹的“中国洋装书”。这本书虽用了洋装工艺,但装订还是用了纸捻取代丝线,可见洋装工艺也有一个过渡阶段。
洋装书和其他器物的出现不完全相同,它是工业时代的产物,量大且标准化。非要固定某本书为中国洋装书第一标志,恐怕不好确定。我们大体可以实藤惠秀的研究为依据,把一九〇五年前出现的洋装书,都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洋装书,至于哪本第一就要比较大量的印刷实物了。
三、录音机
录音机是人类重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今天,录音机具体形式随电脑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可以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录音机。
录音机的前身是留声机,为爱迪生发明,时在一八七七年。一八八八年一位美国人发表了利用剩磁录音的论文,奠定了录音机的理论基础。一八九八年,一位丹麦人发明了钢丝录音机。录音机的早期历史经历不同阶段后,开始进入人类日常生活。中国人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自己生产的录音机。
作为一种具体知识,录音机何时传入中国呢?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还没有人具体指出。这个时间应当说相当早,可以判断在它刚产生不久,中国人就知道了这种东西。所谓中国传播,专指中国人、中国文字中最早记载了它的出现,而这种文献在中国本土刊行。
张荫桓(一八三七—一九〇〇)是广东佛山人,清末曾任中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著有《三洲日记》,是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至光绪十五年出使上述三国的日记。此日记清末曾在北京刊行,后编入《张荫桓日记》。
在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甲寅(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三洲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鸟约富人阿边好博,其子好冶游,另赁华庑以居,忽一夕,阿边与阿洛对局而胜,得采二十万元,阿洛无现资,书券限三日交银。翌日阿边寻其子新居,阿洛尾之,阿边父子诟詈甚激,其子贸贸焉迳附火车赴费城去。阿洛突入,索阿边还其债券,阿边愤甚,诋之不虞,阿洛手刃相从也。阿边被刺,阿洛即从阿边夹衣内检债券裂之,自掩房门而去。房主人妇闻诟詈,知其父子不能相能,晡时无动静,乃推门入,见阿边被刺于榻,仓卒报官。差拘其子,人证凿凿,其子遂抵罪。
这个案子本已了结,但忽然节外生枝。它的被推翻则是早期美国录音机出现后,成为重要举证手段一例,而中国人有意识记录了这种新事物。
张荫桓在日记中接着记述道:
忽有人名多士,手携一机器至公堂,一触而动,当日阿边父子相詈之声、其子出门步行之声、阿洛开门与阿边诋讪之声、阿边被刺呼痛之声,阿洛将刀拔出用纸抹刀之声,一一传出,于是问官,乃知杀人者阿洛也,乃宥其子,别执阿洛。此种冤狱,赖此机器平反,异矣。盖多士本与阿边之子隔壁住,是日正将传话机器试用,适阿边来寻其子,喧嚷不堪,多士虽遂扃钥房门,信步他往,欲俟声息稍静乃返,忘却窒止机轮,乃回房而机动如故,所传悉阿边父子相詈、阿洛行凶之声情,及闻阿边之子定狱,因携此机器至公堂为之昭雪。(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三十一页,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毫无疑问,张荫桓日记中记载的“传话机器”即是今天的录音机,一八八六年六月,这个时间距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的时间只有九年,中国人不但知道了一种西方科技产品,更知道了它在刑事案件中可以承担重要证据作用,作为一种西方新知识,应当说它已进入了中国的知识系统。
四、A片
中国人什么时候知道世界上有A片这回事,我们在一般的史料中还不好确定。A片的产生与现代摄影技术出现相关,中国有春宫画传统,但没有A片传统,因为中国没有先产生它所依赖的技术。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知道有A片,应当是改革开放后的事,当时称为“黄色录像”,后来又有一个说法是“毛片”。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器物,一为观念。所谓中国传播的意思是中国知识中有了关于这种知识的记载,通常是有了汉语译名或者中国人知道了这件事并以汉语记载了这种知识。最近储安平《欧行杂记》出版,我看到其中有一则A片史料。
一九三六年,储安平乘船到欧洲去,过苏伊士运河时,经过一个叫坡赛的地方。这个地名今天叫什么?我没有查到。储安平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很不好,储安平说:“还有一件事我要特别写下来,就是在坡赛,居然公开的沿街兜售春画,一张一张给你看,开价还价,一如普通的交易。还有些人跟在你后面叫你去看活动的性交影片和裸体跳舞。我简直不明白坡赛这地方是什么一个世界,看来这地方的淫风一定很盛。”(韩戍编、储安平著:《欧行杂记》,第四十九页,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活动的性交影片”即是今天的A片。储安平当时是一个有知识的青年记者,尚没有用出A片的固定称谓,而只称“活动的性交影片”,可以判断它还没有进入汉语的知识系统。此前中国人的著作中,有无关于此种知识的记载,我还没有看到过。如果将来写A片中国传播史,储安平的这条记载应当是个时间判断节点,只有在中国文献中发现比它早的记载,才更有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