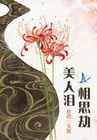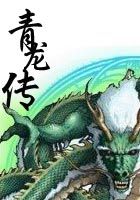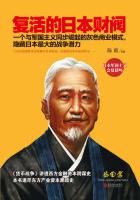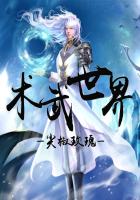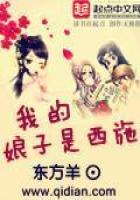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达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60岁,然而,在他的眼中,他的新生活才刚刚铺展开。回到祖国后,李四光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定期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积极输入新鲜的思想血液,以便更适应新中国新时期的工作、时代特点。同时,他也忘我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地质工作中,发现油田就是其中一件不可不提的大成绩。最终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百废待兴,亟待石油
“中国是个缺乏石油资源的国家。”
“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矿产资源急缺,放眼中国,你看到的不是机动车而是冒着浓浓青烟的公共汽车,那是因为中国缺少石油,公共汽车的燃料只能够以煤炭代替;人均拥有的钢材连打一把菜刀都不够;连小小的图钉都得依赖进口;街上跑着的汽车没有一辆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1949年,全中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钢产量仅仅15万吨,这与亟待发展的新中国格格不入。
方兴未艾、内忧外患,这一切都因为中国经济建设遭遇困难,这些困难也都指向一点——中国石油匮乏。是真的匮乏吗?早在1915年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花巨资也没有在中国收获多少石油,而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在对中国地质进行调查后也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而且还有外国专家断定中国缺乏石油,扬言说:只有西部有,其他地方绝对没有;此外,中国人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石油真实的状况,就连毛主席和周总理也不能够确定。
当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到祖国后,他断然否定了这个“事实”。面对毛主席对中国贫油的担忧,李四光只微笑着摇了摇头,他对毛主席说:“没有那个必要,咱们国家的石油产量是非常丰富的。”
李四光这样坚定的回答,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而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在他眼中,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外国人的结论也并不能够绝对说明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凭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对中国地质的研究,已经预感到中国底下滚滚石油的存在。经过他的研究,很快就发现了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石油)”。接着,他就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为新中国找寻石油的大业中去了,不辞劳苦地工作着。
致力石油,不辞劳苦
“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道两湖地区……都可以做工作。”
李四光夫妇不辞辛苦、秘密回到北京以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郭沫若来不及吃早饭就赶到火车站迎接了他们;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总理也亲自到他们所住宿的饭店与之进行了长谈。李四光倍感激动,希望赶快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此时他已经60岁,但是面对新中国,他依然显得神采奕奕。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但更多的还是战斗在寻找石油的第一线上,因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亟待他找到宝贵、丰富的石油资源。
担起了这个任务后,李四光就立马投入了工作,他对中国地质矿产资源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更加肯定了中国的地表下一定藏有丰富的石油。他分析、解说了中国油气形成和移聚的基本地质条件和情况,并用科学的论据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这次发言鼓励了中国地质学界的信心,全国科学家、地质工作者都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认真分析、找寻。1955年,他们开往第一线,从东北平原开始普查,仅仅几年内,勘探大队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
终于,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1959年9月25日,从东北传出佳绩——中国石油勘探队在松辽盆地找到了石油。时值新中国十周岁生日,这一喜讯无不鼓舞人心、增添喜庆。
这个油田就是“大庆油田”,一个在当时为新中国带来无比欣喜的希望油田。接着,李四光又领导勘探队相继找到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辽河油田、华北油田、中原油田等等几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大油田。
这些油田的开发,使中国原油产量大量增加,而且彻底粉碎了外国人认为中国缺乏石油的错误论断。
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欣喜而庄严地宣告:中国石油可以基本自给。
走过斗争、战争,经历千辛万苦,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然而面前却横出一个“中国缺少石油、外国对中国油禁”的大难题。内忧外患,幸好中国的李四光回来了,他就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新中国的光明大道。
为了救中国,为了使祖国的建设事业快速、有序、持续、健康地进行下去,年过六旬的李四光仍不辞辛苦,领导、指挥中国勘探大队进行中国石油找寻工作。他们走遍中国的东北、渤海湾、华北、两湖地区,逐步发现储油构造,探明大型油田,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这一切令人动容的事迹,都与李四光的爱国红心紧紧相连,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要把所学的东西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