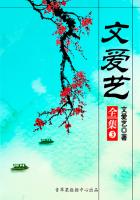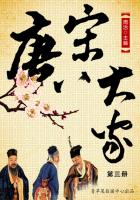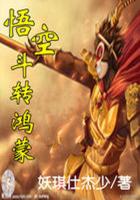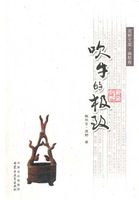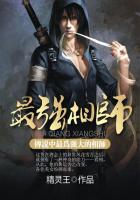钰报道:先生说妙玉其实就是曹頓的出家以后的形象,不知在文本之中怎可以看出来。目前多数读者都认为妙玉是个奇怪的人,你这样说恐怕没有人会信服吧!
先生道:要正确认识妙玉,还是要到文本中看的。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文本之中关于妙玉的叙述吧!
一、妙玉生于仕宦之家,而且是富贵之家,随身带出来的器具都比贾家的更珍贵些。苏州人氏,早年多病,落人空门,却是僧不僧,俗不俗,男不男,女不女,带发修行,号称“槛外人”。父母亡故以后,随师傅人都,住着牟尼院,爱读庄子文。自称“畸零人”。师傅圆寂时,谆谆告诫,不可回乡。
二、妙玉爱洁成癖。文中层层铺陈,自刘姥姥吃了贾母剩的半盏茶开始,一直到宝玉要小斯打水给妙玉洗院子。
三、妙玉吃茶很讲究。她竟能知道贾母不喝刘安茶,茶具、泡茶的水都很讲究。特别是,吃茶时把贾母撂一边,单单和宝钗、黛玉和宝玉去吃梯己茶。她很孤傲。
四、但是,她可以给宝玉用她自己用过的茶杯吃茶,刘姥姥用过的杯子宝玉可以要去送给刘姥姥。宝玉可以到栊翠庵要红梅花,别人就不行;哪怕宝玉去,带了小厮去就不行了。她会给宝玉祝寿,寄贴自称槛外人;而宝玉则选择了槛内人。
五、妙玉会作诗,被黛玉称作诗仙。
解读来看,第一个特点,妙玉出身富贵之家,书中夸张的说比贾家还要富贵。然而妙玉自称“畸零人”,这是很奇怪的。其实就这是夸张的警示读者要注意这儿。目的就是告诉你,妙玉就是曹頓一样从富贵家逃出来的人。苏州人氏,这和甄家是同乡的提示,目的还是暗示妙玉的真实身份。不僧不俗、带发修行、不可回乡,目的就是告诉读者,妙玉出家其实是藏匿,是逃难,本可以回乡但是怕家乡熟人。妙玉隐居的地方,其实并不遥远,只是不可与父老相见,是咫尺千里罢了,是真正的“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第二方面,文中正文和脂批都提出或者暗示,贾宝玉是情毒之人,最后悬崖撒手,悟道出家了。贾宝玉多次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最是清洁;女人就是被污染的俗物了。贾宝玉听说谁提仕途经济的事,就极其厌恶。这就是贾宝玉的“洁癖”。不知大家还记得宝玉有一句话不?宝玉对黛玉说:“我和你都没有亲兄弟姐妹,我想我的心和你是一样的”,这正是“畸零人”。对于贾宝玉说“我和你都没有亲兄弟姐妹”,好多人都会认为我写错了,贾宝玉,明明有元春、探春、贾环等兄弟姐妹嘛!其实,这看似错误的地方正是文眼呢!这儿要揭示的就是曹頓过继曹寅之后,算作无“亲兄弟姐妹”的。你比较一下妙玉和贾宝玉的特点看看,会得出什么结论?答案也许就这么简单,贾宝玉与妙玉其实就是一个人。贾宝玉与妙玉的槛内人与槛外人对称,其实就是说明贾宝玉和妙玉是作者曹頓的为官和出家两个方面的存在形态。妙玉是槛外的贾宝玉,贾宝玉就是槛内的妙玉。妙玉之洁癖,就是宝玉之情毒。对谁都不待见的妙玉,独对贾宝玉梯己;那不是大家看出的妙玉爱上贾宝玉,凡心不泯。妙玉和贾宝玉都是“畸零人”,都出家“不僧、不俗、不道”,亦僧、亦俗、亦道。特别是,关于妙玉“男不男、女不女”的说法,更具有巨大的指向作用。妙玉和贾宝玉就是一体两面。妙玉和宝琴都是红梅花,宝玉也是红梅花。贾宝玉对仕途经济看着、听着都无比厌烦;妙玉对世俗之脏极其敏感。但是,妙玉独独可以把自己用过的杯子给宝玉用。谁也并不可能要来妙玉的梅花,贾宝玉可以。大家要注意的是“人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这两句其实就是贾宝玉生命的写照,“人世冷”与“离尘香”而已。
大家应该注意的还有,关于贾宝玉乞红梅的描写,主要目的就是引出四首诗来。这四首诗,道出了作者的本来意图。邢岫烟的诗中的诗眼是“看来岂是寻常色,浓淡由他冰雪中”,她告诉我们梦中江南的红梅是不寻常的,是南明朱红。李玟的诗的诗眼就是为了追梦“误吞丹药移真骨,偷下瑶池脱旧胎”,她告诉我们曹頓假死出家投奔南明重新做人的故事。薛宝琴的诗中要告诉的就是,“乘槎访帝孙”,不过她访的是南明“帝孙”,而不是刘心武说的弘皙一类。最后贾宝玉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为了访帝孙瑶台种一红梅花,他“槎竍谁惜诗肩痩,衣上犹沾佛院苔”,千辛万苦做了和尚。这首诗结合妙玉的故事,作者告诉大家的是,曹頓向往南明故国,为了寻找复国的希望一瑶台之种红梅花,甘愿做了槛外人,出家做了和尚,哪怕痩骨嶙峋也在所不惜。作者曹頓就是借助妙玉的故事,表达了妙玉与贾宝玉的同体,说明了自己离家出走并不是消极遁世,而是为了坚定的政治理想,抒发了自己鲜明的政治抱负。妙玉“欲洁何曾洁”不是前文大家所认为的被人肉体玷污,而是所谓名义上出世做洁净之人,其实还是时时关心这个污俗的世界,希望拯救这个坍塌的世界。是表达我曹頓离家出走做了和尚,离开了这个污浊的世界;但是我还心系故国,并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界,写下《风月宝鉴》警示后人。妙玉之洁是精神之洁,而非肉体之洁。不要低俗的看待作者的写作意图。关于“欲洁何曾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介绍了妙玉的前身曾经是不想人浊世,抱定木石前盟做平民的决心;但是,没有办法,被康熙和家人赐予金玉良缘,从而流人浊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屈辱的服从了老迈的康熙。这就是,脂批“故不能不屈从枯骨”的本意。不是象说笑话一般认为妙玉“被某王爷强奸”。
妙玉所揭示的是,我一曹頓,离家出走以后的形象。曹頓具有一颗洁净的心,不愿意与浊世朽物为伍;把出世隐居民间视为洁净之行。妙玉之洁癖,不是简单的物的洁净,而是心灵的洁净。她的出家,不仅仅是为尼为道,而是离开污浊的世俗,她不僧,不道,也不俗,因为曹頓仅仅是一个隐者。她不是一个女人而已,她“女不女”,因为她是曹頓。妙玉居住十年的玄墓蟠香寺,实在就是康熙朝廷,玄烨的朝廷实在就是“玄墓蟠香寺”,我把康熙统治的官场比喻成黑色的墓穴,我真的不想做什么织造,我只想做一个清白人,但是“枯骨”康熙的命令不能违抗,欲洁何曾洁,终于陷人清统治集团这个污泥之中。这正是判词“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并不是续书所说的被歹人奸污。那是肤浅的、机械主义写实论者的误读。玄墓蟠香寺这段日子,我看到的都是腐朽和糜烂。感觉到的都是惶恐和不安,盼念的都是隐居。大家应该都知道欧阳询的故事,欧阳询父亲起兵失败,全家罹祸,年幼的欧阳询隐居欧阳父亲的朋友江总家二十年。我最初的离家出走,也是如欧阳询隐居一样,人间蒸发的。也是如妙玉一样,藏匿的,也是不能回乡的。我所期待的,就是象欧阳洵一样等着朝代更替,南明复国。在这二十年的隐居之中,写下了风月宝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凹晶馆联诗我在以前的文章已经讲过了,整个过程就是揭示曹寅家的经历过程。林黛玉和史湘云写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就是从曹家的烈火烹油之盛,写到了花落水流红的衰败阶段。这时曹家已经是,寒塘逃走了仙鹤,冷月埋葬了花魂。一派破败景象,这两句不是周汝昌先生讲的仅仅实写史湘云与林黛玉两个人的,是写整个曹家,写整个女儿的。曹家破败以后,各路子孙他们的生活,就是妙玉所写的“香篆销金鼎,脂冰腻玉盆。箫增嫠妇泣,衾倩侍儿温”及其后文。这个令人悲愤的场面,这个令人悔恨的结局就是作者和贾宝玉关注的结局,就是作者和贾宝玉痛苦流泪、流血珠的结局。这儿让妙玉写出来,和史湘云写出来是一样的,他们就是经历人。妙玉就是离家出走的人曹頓,就是书中的贾宝玉。还有很多文本证据,在此不再多说了,我相信读者自会悟得。
有先生认为妙玉就是作家本人,并且说有林黛玉的影子。那是敏锐的认识。黛玉就是作者本人的木石之志的物象,也正是妙玉隐居生活的前提。作者、黛玉、妙玉,三者实在是一体的。这说明还有知心之人的。现存120回本《红楼梦》后面“续书”之中,瞎猜妙玉的结局,真正成为了反证续书为假的绝好例子。这也会为那些认为“续书”为真的人提供一些研究思路和方法。醒醒吧,高鹗控。自称“证”字辈传人的刘心武先生,认为妙玉以身相许搭救贾宝玉。他的那一套是在哪儿看到的?那么活灵活现?是怎么“证”得的呢?好像忠顺王正在欢媾妙玉,有人正在床前似的?如果没有看见,没有证,不要附会《红楼梦》“证”字一门好不?
几个问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中有句脂批,成了“续书者”和认为妙玉被强奸者(包括刘心武)曼妙瞎猜的直接原因之一。其实,今天所看到的各版本的批语是这样的。原靖眉批:妙玉偏辟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瓜州渡口劝惩不哀哉屈从红颜固能不枯骨各示囗。周汝昌先生校为:妙玉偏辟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现渡口,各示劝惩,红颜固[不]能不屈从枯骨,[岂]不哀哉。戴不凡校为:[乃]妙玉偏僻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瓜州渡口屈从,各示劝惩,[岂]不哀哉。红颜固[不]能不[化为]枯骨[也],[叹叹]!
其实这是谜一样的批语,各人只是从自己的角度理解而已。首先,不论是周先生还是戴先生都没有给出“各示劝惩”的意思,也不会给出为什么会在瓜州渡口的原因。只会猜想出妙玉回乡,在瓜州渡口被枯骨强奸。那么,妙玉被强奸,劝惩了谁?谁又会来实施劝惩呢?因为继抄书者不明白,所以抄成这个样子。
真正的批语是:妙玉偏辟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红颜固不能不屈从枯骨,不哀哉!他日瓜州渡口各示劝惩。周汝昌先生的校勘较为合理些。
意思就是,这是妙玉偏辟生涩的地方。正如俗语说的:太过于高洁,人们反而不容易理解你,讨厌你。你不想屈从康熙去做污浊的官僚,但是,你不能不屈从这个老家伙。到了时候,南汉队伍打到瓜州渡口,光复中原,将会对他们给予惩罚和劝勉。
这些都是自然主义写实论和不懂瓜州渡口含义造成的。读《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能用自然主义写实论。
瓜州渡口自宋以后都是战斗复国的象征:王安石《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陆游《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宋·张缉《月上瓜洲·南徐多景楼作》:
“江头又见新秋,几多愁,塞草连天何处是神州。英雄恨,古今泪,水东流。惟有渔竿明月上瓜洲。”
明·郑成功:“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信朱。”
仅仅把瓜州渡口看成普通渡船之地,那哪儿是《石头记》呢?那哪儿是甄士隐呢?瓜洲渡口的劝惩是政治的劝惩,世事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