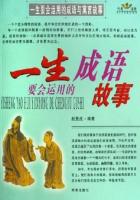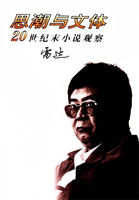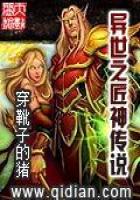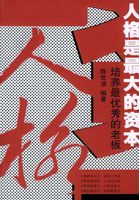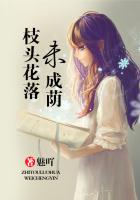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首先选择的却是大山深处的龙胜——这是一个在决定出行前从未听说过的瑶族自治县。翻看随身携带的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其中《瑶人》条下记有:“瑶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年丰则安居巢穴,一或饥馑,则四出扰攘。”
“耕山为生”——这四字应是南方瑶壮等民族梯田形成的历史渊源,当地关于龙胜龙脊梯田有这样一段文字:“龙脊梯田始建于元朝,完工于清初,占地面积四平方公里,分布在海拔三百至一千一百米之间,坡度大多在二十六至三十五度之间,最大坡度达五十度,垂直落差五百多米,梯田如练似带,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小山如螺,大山似塔,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春如层层银带,夏滚道道绿波,秋叠座座金塔,冬似群龙戏水,集壮丽与秀美于一体。”
看图片中青白相间的曲折线条(春天梯田刚放水后,反光所形成的层层银带),感觉这些描述并非虚言,那种光与影,那样的行云流水,如天地间一抽象立体巨画,浩浩莽莽,心胸为之一阔。
桂林汽车站每隔数十分钟便有一班去龙胜的汽车,出桂林城后,风景依然绝美,悬泉飞瀑时时可见,茂竹绿萝深处,往往掩映着二三吊脚楼,一如让人神往的湘西风光,只是少了沅江的悠远与伤感。
抵龙胜后,车站有直达龙脊金坑梯田的车,上车,一脸形尖而瘦的男子塞给自己一张名片,说如果去那里可以到他家的家庭旅馆,又拿出地图热情地比画他家的所在位置,聊了聊,兴趣不大,男子下车继续揽客,车不久摇摇晃晃也开出了,一路逶迤向北行去。路很窄,车窗外可见深谷峭壁,几不见底,心为之一惊。到和平乡后,换车,上车坐定后,身边一戴草帽的壮汉衣襟开着,露出蒲扇似的结实胸脯,他憨厚地朝自己点点头,便也朝他点点头,那人欲言又止的样子,仿佛终于鼓足勇气,有些羞涩地笑着,问自己住不住宿“我家地点很高的,靠近观景台,视野也好。”
这人的样子让人看着有些踏实,便和他说,上山后再看看,若旅馆条件都差不多时一定先选他家的。这样的回答似乎让他很满意,便盘弄着手中的一大把香蕉,告诉我他家里常年住着一个老外,老外早上喜欢吃香蕉烙饼,所以吃完了香蕉就得下山给他买来。
车进深山后,路右一直是条清澈如镜的溪流,陆续有瑶家女人背篓上车下车,清一色头盘如锥巨髻、戴大耳环、着黑色土布短裙,下车后不久即消失在大山深处。溪流尽头,是处小小村镇,可见捧碗在街边屋檐下说话的三五闲人,大概不久前刚下过雨,地上泥泞得很,几个孩子哄笑着上车,脚上是清一色粘满泥土的粗大套靴。
两山之间又是一段碎石子路,歪歪斜斜,但不到一小时便到终点了——是一个寨子,下车后,顿时拥上不少衣着艳丽的瑶家女人。草帽汉有些温厚地看我——自然推辞了那些瑶人的邀请,和同时下车的三个游人一起跟草帽汉拐过寨子,向山上行去。
无意中接到这么多客人,且全跟定了自己,草帽汉眼睛里全是笑意,他主动将另一位旅伴的背包拿来,挂在扁担上,边走边开始介绍起当地民风来。
这才知道他姓刘,妻子也是瑶族。他说这里开发不过两三年,简易公路也是这两年才修建的,过去,这里的人要走半天多时间才能出山。
山路几近“羊肠”,由一块块石板散乱铺就,曲折而舒缓地摇曳而上,直伸展到无尽的曲线里,人行其中,飘飘忽忽,云里雾中一般,全无方向感,身边可见的只是层层叠叠的梯田,形状不一,共有的却是一种灵动的妩媚。
秧苗刚插不久,窄而亮的水中才见一片浅绿,偶尔传来几声蛙鸣,叮叮咚咚的清音却一直响在耳畔,可见或架空或埋于田埂间的竹管,是输水管道,引出山泉后,由上到下逐级灌注于梯田,再沿着缺口汩汩地流至低处——龙脊梯田有着完备的水系,在海拔最高达一千多米的山顶梯田上,南方民族千百年来与自然共舞的才智与毅力不能不让人惊叹。
走了不过十多分钟,旅伴中便有人大声叫累,问草帽汉还有多久才能到。
“快了快了!”他指着云雾里隐约可见的几丛黑瓦走木楼说“再拐三个弯就到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句话进并不实在,他说的弯差不多是一座山的弯道,而不是山路的小弯,他所说的“快了”——我们至少走了近一个小线时。
然而这真是一个考验意志与充满壮美的行程:一边是劳累疲惫,但依然坚持着走下去,因为那些无法形容的梯田曲线,简直魔幻一般——每走一步就会变幻,伸展、收缩、放大,弯曲、舒展……说是百变视觉惊艳并不为过,而这一切的组成元素竟然只是稻田——零零碎碎、大大小小的狭长田块,在我这个见惯水乡稻田的人看来,不到此处,真不知世间之奇。
偶尔田间可见数丛翠竹子,或是一个牛棚——朝里面看,居然有牛在缓慢地咀嚼。
拐过两山相连的弯道,进入一个小小的林子,似置身于鸟的世界——耳中全是各类鸟鸣,或啾啾啁啁,或婉转有致,或音韵悠长,这边叫几声,停一下,那边又接着响起。山道上不时有水漫出,什么地方一眼清泉,用手掬一捧,清凉凉的,索性把鞋脱了,赤脚行在石板路上。
走过一段路,草帽汉忽然很快乐地叫道:“杨梅!”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果然上面山路一侧的杂树丛中,一棵满树点点微红的杨梅,刚下过雨,树叶全湿湿的,翠生生的好看得很。
草帽汉放下行李,说:“我来摘吧,多摘些回去给你们吃。”他的身手真是敏捷,分开杂树杂草,几步就窜到树旁,累累垂下的杨梅鲜红鲜红的,很养眼,看他摘那点点的红,让人感到一种生的欣悦。袋子里很快就满了,紫红紫红的颜色全浸出来了。
杨梅被雨水洗过,从大枝上折下一个小枝,边走边尝,比江南所卖杨梅小些,新鲜劲却过之——还带着树枝嘛,入口微微的甜,随即便漾来微酸,忍不住抿住嘴,酸味渐浓,一阵激灵,酸得几乎吐去,然而就在此时,一股甜鲜又隐约而至,且余韵极长,忍不住又摘一颗入口……一路吃着杨梅,酸得想吐,又甜得又不想吐,时间很快,再拐过一个弯,进入一个小小的寨子,草帽汉便说:
“到了。”
——他家就在寨子后面,一座三层的新木楼,前对无尽的梯田,后面是处山坡——当然,再往上,还是梯田。
这木楼真大,一楼除了两侧的厨房与卫生间外便都是厅堂,偌大地方只放了些桌椅,一台电视,二楼、三楼全是客房,正是旅游淡季,除了我们几个人,再没有别的人住这里,女主人带我们到三楼,房间布置简朴干净,推窗所见即是梯田与重峦叠嶂的远山。
很满意,去浴室洗去浮尘后,出外时看到厅堂里冒出了一位老外,约五十岁,看到我立刻微笑着点头说:“你好!”女主人介绍说这就是常住她家的老外让·克罗德,法国人,前年曾在她家住过半年时间,这次是一个多月前来的,准备至少住三四个月时间,他每天一大早就出门拍图片。女主人居然会一些简单的法语,她指着克罗德告诉我,他和这寨子里的不少人都熟悉,克罗德看出女主人指他,便问说什么,这女主人和克罗德说一通后,得意的克罗德立刻指着坐在门口绣花的一位瑶族老妇人对我说:“这是我老——婆!”我大笑,那瑶族老妇人放下针,也笑着佯骂克罗德。
玩笑过后,女主人抓一把米到外面唤鸡——在几只鸡鸭来吃的当儿,果断地抓住了一只母鸡——她向我推荐了煨土鸡“味道好,到这里的客人都吃的。”克罗德看他们抓鸡,却又指着一只黑白相间的雄鸭和女主人说话,女主人咯拉咯拉很快乐地笑起来,又点点头——原来克罗德请求她千万不要杀那只鸭子,理由是——“那走只鸭子太漂亮了”。然而因为杀鸡,鸭子显然受了些小进惊吓,跑到远远的坡上东张西望着,心神不宁。
晚饭除了煨土鸡,又点了炒白菜、腊肉、青椒炒蛋,外加啤酒一瓶,邀克罗德共餐,克罗德欣然受邀,席间不停地把鸡骨与腊肉扔给一只闻香而来的狗,边喂边温柔地说:“布卢苏,布卢苏!”他告诉我这是汉语“慢慢吃”的意思,他担心狗吃噎着。
饭后已是薄暮,天渐渐黑了,克罗德回房休息,自己便从所来的路上顺着走下去。远山只是一抹淡影。层层梯田间笼着似有若无的烟岚,飘飘忽忽地又不见了,那么多条曲线婉转交错,依山连绵不绝地盘旋而下,远远近近的田间一圈圈反着白光——原先青白相间的曲线不知什么时候已转为黑白相间,附近寨子里不时升起两三缕炊烟,可以听到什么人在大声地叫着谁的名字——不知是不是唤孩子回家吃饭,石径深处隐约可见一两名着瑶家服装的女子,背篓默然行走。
什么地方有狗吠,轻轻的一两声,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一般,再无声息——才发现坡上人家高台一直蹲着条灰白的狗,一动不动地凝视远方,我来时它是这样的姿态,走时,它仍是这样的姿态,它的目光一直是远方,仿佛若有所思,如哲人。
回程时在草丛间居然发现几只萤火虫,满心的欢喜,捉了一只,到底还是放了,目送这儿时熟悉的生灵一闪一闪地消失在水田间,一时竟想不起它到底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
就像我在这巨大的层层叠叠的稻田里,记不清它们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夜幕终于将壮观无比的梯田群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