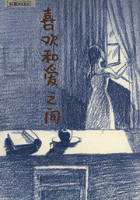她常常跟他玩纸牌,总故意输给他。他们看见一些肥胖的中年女人和一些风湿病的老头子在井边喝水,回家后她就在他面前模仿起他们的样子来,引得他哈哈大笑一阵。她尽量地纵容他,奉承他,戏弄他,一直当他一个年轻小伙子看待,同时却又服侍得他舒舒服服,竟把他当做一个行动不便的龙钟老人一般。有一天她猜他的年纪只有四十五,他说他的大儿子也有三十五了,她就说她无法相信这种话。总之,她故意装出那种心醉神迷的样子,已经演得无衣无缝了。
直等三个星期过去了,他丝毫没有显出引诱她的意思,她就有些觉得焦躁。
有一天晚上,他走了之后,她独自站在一扇玻璃窗面前,用手指甲在玻璃窗的凝汽上胡乱画着。她撅着嘴,眉心深锁着。
拿尔正拿着一双火筷从火炉里将赤红的炭火夹进一个银火盆,瞅见了琥珀这种神情。“出了什么问题,夫人?”
琥珀惊得一个转身,差点连裙子也扭坏了。“可不是吗!哦,拿尔,我快要发疯了!这只兔子我已经追了他三个星期,可是仍抓不住呢!”
拿尔盖好了火盆,正将它拿进卧室去。“可是他已经上钩了,夫人。这是我看得出来的。”
琥珀跟着她走进卧室,开始脱起衣服来。她脸色阴沉,连连地唉声叹气,仿佛她为引诱老头向她求婚,已经花了一辈子功夫了。拿尔过来帮她脱衣服,站在她的背后头,替她解开软骨带。
“哦,夫人!”她开口反对起来,“你何必唉声叹气呢!这一班保守的老清教徒的脾气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在他们家里做过活的。他们都把通奸看做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可以发誓,这位老先生除了自己的老婆之外,一定是二十年来没有碰过一个女人!他现在很害臊,你得容他一点时间克服啊!而且你费了这许多心机,原是要他把你当做一个正经女人。可是我的眼睛同巫婆一般,看得出他已很动心了——譬如麻包里边埋着火,总要将它烧起来的。”她又仿佛看得很透彻地般点了点头补充道,“你只要给他一个适当的机会,将来一定能一把牢牢擒住他,如同把野鸡套进了圈子似的。”说着她把双手比做一个陷阱,在自己的脖颈上箍了起来。
事实上琥珀心里非常清楚,这一次是她制服世人的最后一个机会了。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她不敢再失败了。她曾眼见过不少女人,也同她这样靠着一点心机和相貌谋得暂时的活路,可是不久就色衰宠失,根基未固而又身世飘零了。于是她心里很着急地想到,不管怎样,我是非干不可的。我是非要使他跟我结婚不可的!但是后来她想啊想,忽然想出一点新鲜主意来,觉得自己这种要先引诱他落水而后再谈结婚的手段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他的结婚就是由于亏心,迫不得已的了。是啊,她恍然大悟,这种苟且行为是他决不肯干的。那么他当然不会来勾引我了!他当我是一个贞洁的女人而且尊重我的呀!他除了自己意愿,决然不会来跟我结婚。那么我非使他正式向我求婚不可了!这是摆着的道理,我为什么没早点想到呢?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夜她跟拿尔将这问题商量了许久,终于被她们想出一条计策来。
大约一礼拜之后,琥珀和温先生就坐了他的马车回伦敦去了。这之前的几日,温先生曾告诉她,说他必须回伦敦了,琥珀说她不久也要走,不如提早几日跟他一起走。她觉得跟他在一起,路上能放心些。她自己的马车让给拿尔和考居尔坐,跟随在他们后边。那天早晨他们在琥珀的房里一同吃早饭,吃得非常丰富,因为有一天的路要跑。她原本兴高采烈,现在却陷入一种期盼和忧虑的沉默状态了。她不时轻轻叹一口气。
那天天色暗沉沉,雨点不住从树林的枯枝里筛下。
空气潮湿而刺骨地冷,但是他们身上穿着翻毛皮大衣,腿上盖着翻毛皮厚毯,御寒准备得充分。各人脚下又有一个脚炉,里面旺旺生着炭火。因有了这种设备,那个颠簸的大车厢里面是温暖而潮湿的,而这种温暖就造成了一种亲切的气氛,使得那辆马车仿佛是一块与世隔绝的秘密孤岛了。
也许就因为这种孤寂无人的情境,使得他的胆子大起来,竟敢在那车毯底下摸住了她的手说道:“你在想什么心事啊,孙太太?”
琥珀一时不开口,过了一会才带着一个最妩媚迷人的微笑瞧了他一眼。“哦,”她说,“我正在想,我们不久就要分开了,想起在东桥井和你一起玩牌,一起吃饭,一起到井边去逛,多么有趣,今后都要向往不到了。”说着她又轻轻叹了一口气,“我因和你相聚这几天,今后怕要非常孤独了。原来她曾对他说过,她在伦敦的生活非常孤单,既无亲戚,又无朋友,又不敢结识新交。”
“哦,可是孙太太,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们的友谊当做从此断绝吧。我——嗯,老实对你说吧,我希望我们在伦敦仍时常能见面。”
“那好极了。”琥珀黯然说道,“不过我知道你一定很忙——你的家庭又非常热闹。”原来她早已知道,他家在黑衣僧有一所大厦,他那大大小小的许多儿女都仍旧住在一起。
“不,我不会忙的,我的医生原叫我少做事,我也乐得悠闲了——只要有你这样一位美人替我做伴。”琥珀听见这句恭维就向他嫣然一笑,又装做羞答答的样子将头低下了。“而且我很高兴让你会会我的家人。我们一家人团聚一定是很开心的,我想你一定喜欢他们——并且他们也一定喜欢你。”
“你真太好了,温先生,竟会顾到——哦!怎么啦?”因为她发现他脸上突然起了一阵痛苦的痉挛,不禁喊起来道。
他一时没有说话,显然觉得自己在这非常浪漫的顷刻,忽然害起病来是怪尴尬的。但他终于摇摇他的头。“不——”他说,“不,没有什么的。”
可是一会儿之后,他又出现痛苦的神情来了,竟把一张脸涨得发紫。琥珀不由得大惊失色,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哦,温先生!你说呀!千万别瞒我——究竟怎么了啊?”
这时他神色大变,显然难过万分了,终于只得承认,说他肚里不知什么缘故一时痛得厉害。“可是你不必替我操心,孙太太。”他恳求道,“我一会儿就会好的,这不过是——哦!”他突然发出一声不可控制的呻吟。
琥珀看着他,脸上反映出同情的苦痛。可是她马上就来着手应付这个局势了。“这里前去不远就有一个小客店——我记得我们来的时候经过它的。我们到那里去停下来,你得立刻就上床去躺着,我知道我一定有——哦,你不要反对啊,先生!”她见他开口要抗议的时候就抢先说道,那语气不容分辩,却又温存得跟一个母亲对她的病孩子说话一般。“我一定会有办法的,这里——我有一些止疼药草和甘菊花放在这个小提包里,这是我向来都随身带的。你且等我把水烧开,好让你将药服下去——”
说话之间他们已到那小客店门前,琥珀就将马车喊停了。温先生的跟班华大个儿约罕本想把他背进里面去,这原是他可以为之的,但是温先生坚持不肯让他驮,并且骂他太多事,于是只得将他搀扶进去了。那时琥珀忙得跟一只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一般,先跑进里面去吩咐客店老板娘把房间预备好,又叫暴风和显芝把该搬的箱子搬到里边,又出来看看温先生好不好,如是一进一出地奔了不下五六回。最后大家好不容易把温先生搀扶上楼,逼着他在一张挂着帐幕的大床上躺下。
“现在,”琥珀对老板娘说道,“你得生起一个旺火来,拿给我一把水壶和一个铁架,让我来烧点开水。把你所有的热水瓶都拿给我,还要再添几条被头来。拿尔,你打开那只箱子,取出那一盒药草来——显芝,你去找我的历书来——我想在那绿皮箱的箱底吧。现在你们都走开去,好让温先生安静一会儿——”
于是琥珀解开了他的衣服,拿掉他的大衣和帽子、领结和紧身,将许多热水瓶在他身边围起来,又把被头严严地盖着。她的动作既敏捷而又温柔,兴冲冲而又一本正经,若有旁人看见,总当她已经是他的妻子。他恳求她不要为他这样烦神,只要她派人到伦敦去请医生,他又仿佛以为这场病竟要不起似的,要她派人去通知他的家里人。可是琥珀统统拒绝了。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温先生,”她坚持道,“我知道你只要几天时间就会好起来。你不应该吓坏家里人的——何况伦迪很快就要做产了。”伦迪就是温先生的大女儿。
“哦,是了,”温先生柔顺地表示同意,“我不应该去吓坏他们的,是不是?”
这时他虽觉得身体难受,却因此病而得到这样周到的服侍,倒觉幸而有此了。平常他的为人抱着一种冷漠的态度,想不到他现在虽远离家属,举目无亲,却有这样一个美人专心致志不辞烦劳在这里照料自己呢。她怕他的病随时要发作,甚至连夜里也不肯离开,定要在几步外的一张春凳上陪他歇宿。
只要他稍微有点儿响动,她就马上从春凳上爬起来赶到他床前,扑着身子去看他,以致她那一头浓艳的头发不由落到他脸上,同时那微弱的烛光穿过她的腋下照出她的胸房来。她那低沉问讯的声音不亚于给他一种抚摸。她的肌肉偶尔触在他身上,热乎乎的,加上房间里热气腾腾,以致她身上的茉莉花香和龙涎香气一阵阵地扑进他的鼻孔而使他沉醉。人世间的害病没有比这再快乐的了。又加上她极力说他脸色苍白,不能起床,所以他至病愈之后也还赖在床上好多日。
“哦,我的天!”有一天琥珀在隔壁房间里梳妆的时候,对拿尔说道,“我想我将来嫁给这个老头的时候,总已经是个看护妇,不是一个妻子了!”
“哦,天,夫人,原是你硬让他不起床的呀!而且原先拿那野菌给他吃,也是你自己的主意——”
“嘘!”琥珀警告她道,“这种事情不必劳你费心记着。”说着她从梳妆台上站了起来,又给自己的倩影最后一个顾盼,这才走到隔壁老头的房间门口,脸上先舒展一个非常妩媚的表情,然后推门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