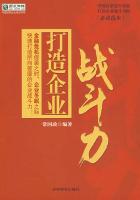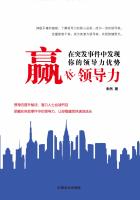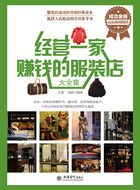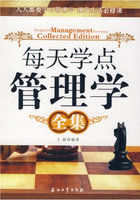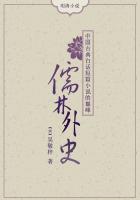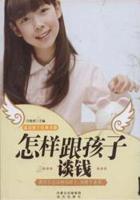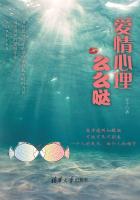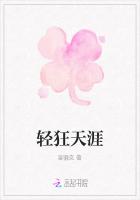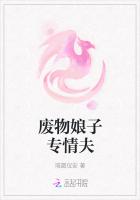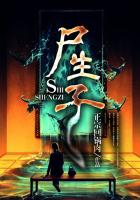我如何成长为中国外企第一经理人
在我被任命为微软中国总裁后的2002年4月,微创软件公司也正式挂牌成立。我现在拥有3个头衔: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总经理、微创软件公司CEO和微软中国区总裁。3个职务在身,压力不可谓不大。但是,人只有在压力之下,才可能成功。每做一件事,都必须成功,不许言败,这就是我的性格。
杜家滨的笑,吴士宏的泪,高群耀的邮件:
我与前三任微软中国掌门人
2002年3月15日,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我像往常一样查看电子邮箱。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微软中国公司总裁高群耀的邮件,奇怪的是,邮件地址显示为高群耀私人邮箱,却不是以microsoft.com结尾。
信中说:“我将辞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兼总经理职务,去追求在业界更富于挑战和对中国发展有更多贡献的职业生涯。”
我立即拨打高群耀手机,他的手机已经关机。我又即刻给高群耀回了一封电子邮件,我对他说,自己很不希望他离开微软,希望他能否重新考虑一下这个决定。我劝说高群耀的理由是:“第一,你对公司很好;第二,公司需要你。”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复。
对高群耀的离开,我既觉突兀,又很伤感。当然,此前也不是没有一点迹象。2月中旬,从亚太区发来的一份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计划的名单上,就没有高群耀的名字。3月初,高群耀来上海,我和他一起参加2002财年的年中报告。那天,我还和他一起吃早餐,我们所谈都是报告中工作的事情。临别时,高群耀对我说要去东京面见亚太区总裁罗麦克,我还鼓励他和罗麦克好好谈,公司还是需要他的,不要做冲动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点头称是,表情看上去十分平静。
在我任上海微软总经理的四年多时间里,微软中国公司竟已三易其主。从杜家滨,到吴士宏,再到高群耀。这其中真有媒体所说的“魔咒”在作祟吗?
我与这三任微软中国掌门人交往的种种片段,此刻想来,总有种近乎诡异般的奇妙之感。
1997年7月,我第一次见到杜家滨。他是台湾人,1995年从惠普跳槽至微软,一手将微软北京办事处转变为独资公司,成为微软中国公司第一任掌门人。作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的候选人,我的职位和他是平级关系,我们均向微软大中华区总裁汇报工作。虽然我已经通过了总部的面试,但微软中国公司毕竟是微软在中国所设机构的老大,为了表示尊重,我专程从美国飞去北京和家滨见了一面。
在美国时,我就听说了家滨在中国“奢华”的工作情形。据说他平时总住在五星级酒店的套间,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梦一般的生活。一见之下,传闻果然不假。那是个周末的早晨8点,我们的“早餐面试”就安排在他居住的中国大酒店进行。虽然名为“面试”,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实质内容。我想他就是想通过交流来感受一下,是否喜欢和我这样的人一起工作。第一次见面,他的那种踌躇满志的自信神态,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优越感,让我颇为羡慕。我用一种发自内心的谦虚和诚恳的态度对他说:“今后在工作上请家滨多多地关照……”
第二次见到他是当年年底,地点在泰国度假胜地普吉岛。微软大中华区1998年度的kick-off(开工)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出席者都是大中华区总监以上的高管。那时我刚正式就任上海微软总经理。对于一个总部技术工作部门出身的人来说,我当时只觉得一个Kick-off会议要来普吉岛开,实在是奢侈啊。不过也打心眼里喜欢这样潇洒的工作方式。那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打高尔夫,记得普吉岛上那个Banyan Tree(印度榕树)高尔夫球场山海一色,景色极美。杜家滨作为微软中国总经理,在会上发表了对微软中国1998年度的展望演讲,感觉他的演讲功力蛮不错。
此后因为工作关系,和家滨见面的机会变得相当频繁。每次见面,他总面带笑容,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我们的部门之间也只有协作关系,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一切都风平浪静。
但我很快就知道了,平静水面下涌动的是暗潮。1998年2月初的一天,我的直接上司布莱恩·尼尔森从香港来北京,我去北京向他汇报工作。他当时任微软大中华区总裁,一直是我最好的后盾,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老板。那天晚上,他邀请我去香格里拉酒店的酒吧里喝酒,然后用很神秘的语调告诉我:微软中国公司正寻找一个新的总经理。布莱恩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他突然就和我说:“Jun,你要不现在就和她聊聊吧。”我正在迷惑之际,布莱恩已经把接通的手机递给了我。
“Jun,你好,我是Juliet。布莱恩和我提起过你。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回到中国来,中国多好啊。我是一直待在国内的,对微软什么都不懂,你一定要帮我。希望我们今后有机会见面,好好合作……”
Juliet就是吴士宏的英文名字,当时她是IBM中国公司南方区的总经理。对方说话的感觉,仿佛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直觉告诉我这个女人很阳光,很亲切,也很不寻常。
我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做。布莱恩很喜欢你,我们也很期盼你的到来。你来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理念……”
就这样客客气气地讲了五六分钟。
挂掉电话,布莱恩问我认为吴士宏这个人怎么样。我根本没有把刚才的谈话当成一次面试,但他却当成是电话面试正经对待的。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挑别人优点的人。我说:“我很喜欢Juliet。她很阳光,说话富有感染力。虽然不知道她的能力如何,但我愿意和容易相处的人一起工作。”
自始至终,我对这次电话面试感到颇有些惊讶。
随之而来的就是杜家滨的离去和吴士宏的上任。之后家滨加盟了思科(中国)公司,而且做得很不错。吴士宏初接手微软中国,意气风发,媒体也对这位护士出身的传奇女经理人十分关注。但新的矛盾很快就出现了。
1998年6月,布莱恩·尼尔森被调离大中华区,罗麦克成为了新的大中华区总裁。之前布莱恩把大中华区的总部设在香港,吴士宏主管下的中国公司在北京,两人很难有业务上的冲突。她又是布莱恩亲自招来的人,布莱恩自然也会对她爱护有加。罗麦克上任后,为了加强对内地业务的管理力度,将大中华区总部的办公地点迁到北京。罗麦克和吴士宏两个人都很有能力,又都想做出成绩,可是蛋糕只有一个,摩擦和冲突便步步升级。
在吴士宏任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期间,我和她的关系倒是非常好。我负责技术中心,和她主管的业务毫无交叉,所以没有矛盾也属正常。我们各自的部门在工作上也有合作,过程都相当愉快。我很喜欢她的直率性格。她来上海时,我们也常会一起吃饭交流,彼此一直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当时微软在中国设有四大机构,分别是北京的微软中国公司、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中国研发中心,以及上海的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按她的说法,微软在中国所设机构的领导人中,我是她唯一喜欢并且可以愉快合作的人。
1999年6月,吴士宏“因事业和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从微软辞职,在IT界引起震动。
吴士宏为什么要感激我
1999年10月,吴士宏在正式加盟大型国有企业TCL公司的同时,出版了新书《逆风飞飏》。此书因为其中大量对微软的批评性言辞而引起轰动。她出这本书的时候,微软中国公司曾通过关系找到TCL董事长李东生,企图向吴士宏施压,让她放弃出书,但被吴士宏拒绝了。
当时微软在中国所设机构的所有高层领导,几乎都被吴士宏在书中点名批评,唯独我是个例外。书出版后,她打电话告诉我说:书里她用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印有“98GCRSC”标志的微软T恤,以表达她对我特殊的感激之情。这张照片里的T恤是我送她的,GCRSC就是大中国区技术支持中心的英文缩写。她说本想过用一张我和她的合影放进书中,但考虑到我还要继续在微软工作,所以选了这张照片。
6月份她离开微软时,我专门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了她的告别晚会。晚会的气氛甚是悲伤,她当场哭了。很多她希望来的人都没来,只有她的一些铁杆部下参加,和她平级的微软高层就我一个人。有人说我和吴士宏走得太近,她和微软的关系如此糟糕会不会影响我的前途。但我并不畏惧这些,心怀坦荡,简单做人,这就是我为人处世的方式。
职业生涯的时机:
我为什么拒绝接替吴士宏
罗麦克变成我的顶头上司后,我和他的关系也很好。吴士宏提出辞职后,罗麦克第一时间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Juliet今天向我提出辞职,这对外界来说会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公司要迅速找到她的继任者,我认为你是唯一可以胜任这个职位并且我也信任的人。”
因为几点原因,我拒绝了这个提议:第一,我领导的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已被确定升级为亚洲技术中心,正争取进一步向全球技术中心发展,这一直是我的职业目标。第二,我回到中国不到两年,对中国市场等各方面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第三,我看出,罗麦克本人非常想自己来做微软中国的业务。
我回绝他的提议后第三天,罗麦克从北京专门飞到上海来劝说我。他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是希望我考虑一下接受这份工作,并允诺一定会支持我。我还是拒绝了。并且向他建议:未来的三到六个月,你谁也不要去找,自己来试做一下,做了之后你对这个业务才有真正的了解,任何需要我的时候我会来帮助你。
罗麦克让我再考虑一下。一周后,微软中国公司在昆明召开高管会议,罗麦克专门把我邀请去。当时微软中国的五位副总经理谭智、鲁众等人,我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不错。他们已经知道罗麦克想让我去做微软中国总经理,在这次会上都表示支持我,希望我来带领他们,不要再从微软之外找人接手。我还是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在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心中抵御“高官厚禄”诱惑的心思都很坚定。在我看来,职业生涯中选择时机非常重要,各种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因为诱惑而贸然行事,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
1999年12月,罗麦克从Autodesk公司挖来高群耀,让他出任微软中国公司总裁。Jack(高群耀的英文名字)是留美的工程学博士,是个非常书生气的人。他戴一副眼镜,说话中规中矩,做事不愠不火,和吴士宏的江湖气相比完全是两种风格。吴士宏的离职让微软中国成为一时的舆论焦点,温文尔雅的高群耀一来,和媒体也就渐行渐远了。不过,这也正是微软所希望看到的。他在任的两年,微软中国给外界的总体印象是无功无过、平平淡淡。
和杜家滨、吴士宏时代一样,我和高群耀的微软中国公司之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我领导的亚洲技术中心正式升级为全球技术中心,我汇报工作的上级变成微软亚太区。在微软的管理架构里,我变成和罗麦克平级的关系,但微软中国每年的年度大会还是会邀请我去参加。
在2000年的微软中国公司青岛年会上,高群耀提出上任后的新财年计划,销售增长率要达到50%。那时微软中国刚经历管理层的剧烈变动,吴士宏时代的大部分副总经理级别的高管纷纷辞职,市场和销售部门的员工也大量离去。公司上下气氛沉闷,年会也开得有几分叫人昏昏欲睡。要改变微软中国的内外环境,当然不是我分内之事,可我希望至少可以活跃一下会议的现场气氛。那天,我用幽默的语气在会上做了个15分钟的演讲,从自己作为一个微软老员工的角度,和他们讲了一下该怎么做技术、管理、销售,居然大受欢迎。后来微软中国的员工告诉我,年会上别的领导都在讲业绩要如何如何,条条框框得令人乏味,只有我的发言才贴近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感受到愉悦和激情。
演讲时,我也善意地调侃了高群耀一把:“Jack你太可爱了,可爱得太不了解微软了,所以才给自己定了一个这么庞大宏伟的目标。可是你知道吗,说增长30%,做到50%,领导会认为你有能力。定80%,哪怕做到70%,你也是失败者。明年这个时候你绝对不敢说增长50%,后年这个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下面的微软中国员工自然是乐成一团,高群耀自己也不禁露出他招牌似的憨厚笑容。
我本是无心之言,谁知竟一语成谶。
从回绝到接受:入主微软中国内幕
我收到高群耀电子邮件的那天,媒体开始报道“高群耀辞职”一事。两天后,微软对外证实高群耀离职。
三天后,3月18日,星期一。我刚走进办公室,秘书就很紧张地对我说:“老板,刚才接到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的电话,让你一个小时内回到座位,他要和你进行一次重要的电话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