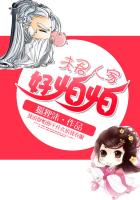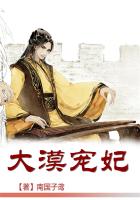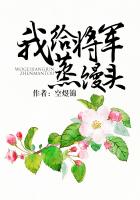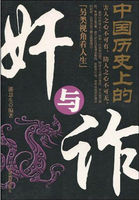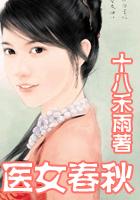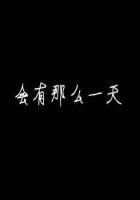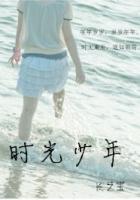虽然出身青楼,但是与生俱来的娴雅从容,竟然让她在冒家这个诗书之家受到青睐。这实在是极其了不起的一件事,那个礼教森严的年代,烟花女子只是零落的草叶,怎能登大雅之堂?可她走进去了,仿佛她从未走过青楼的路。很显然,是董小宛身上的温婉气质让人折服,不论走到哪里,她如幽兰般静静地站着,就能让人心旷神怡。于是,冒家接受了她,像是接受一朵走出泥沼却鲜妍如初的清荷。
她从来都是一朵清荷,人世再纷乱,再繁杂,她永不褪色。
由于冒辟疆的原配妻子秦氏体弱多病,董小宛便理所当然地承担了打理家事的责任。很难想象,一个从青楼走出的女子,竟然能把冒家上下里外照料得妥妥当当,俨然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其实她本来就可以这样,她只是在青楼的喧闹中走了一回,回到真实的生活,她可以无比贤淑。当冒家一切的事务被她理得井井有条,她也就彻底击碎了人们对于青楼女子的刻薄看法。虽然不是所有的青楼女子都可以这样贤淑,但是像董小宛这样原本就娴静却无奈进入那片天地的女子,是可以过平淡日子的。只是他们面前经常横亘着一样东西:冷酷的偏见。人们不让她们走向真正的生活,只把青楼惨淡的日月给她们,让她们孤寂、凄凉。
日子渐渐静下来以后,董小宛便将一段唯美的生活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只知道才子佳人相互掩映,而她将这两个词用诗意的方式,刻画成一帧一帧的画面。画面清新而生动,主角是她和他。只有走向那样的画面,才会明白什么叫做才子佳人。
“碧纱待月春调瑟 红袖添香夜读书。”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场景,就在冒家的书房,静静地呈现着,如轻烟一般,让人难以触及。尘世太过喧嚣,人们已经难以回归那样的情怀,但那时候,他们真的有过这样唯美的时光。冒辟疆考证古籍、着书立说,董小宛在旁边燃香递茶。偶尔她也帮着查考资料、抄写文稿。当然董小宛自己也练字读书,她还曾将古今女性的轶闻奇事编成一本书《奁艳》,可惜未能传世。她练习书法,每天几千字,从不懈怠。
闲暇时他们品茗赋诗、弹琴作画。在琴诗书画里的似水流年,竟是那样柔软明丽。他们也会在月下相依着,喁喁私语。世间所有的情话恐怕也抵不上月下相依的片刻。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情怀,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享受这样的悠然时光。
一段月光,几丝清风,两个诗性的人,就构成了那样婉约的画面,人们只知道日光的温暖,却不知道月光的清凉,更让人惬意。虽然月光在古人的诗句里经常被盖上惆怅和落寞的印章,但是两个人的月光却全然不同。偶尔董小宛也会与冒辟疆的两个孩子一起在月下背诵唐诗,又是另一番情趣。
日子,原本可以过得这样诗意,只是一些小情怀,就可以刻画那样的柔美情节,可人们却总把自己搞得七零八落,难以收拾。当然,他们这样的诗意生活,在一些人看来未免太梦幻,太甜腻。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倒是大刀阔斧、风生水起的好。喜好不同,性情不同,便会给生活不同的色彩和旋律。月光虽美,对于某些人不过就是一片惨白;夕阳虽好,对于这些人也不过就是一滩蚊子血。如此而已。
可这样的幽雅时光,却被那场浩劫给撕破了。李自成攻占了北京,清兵入关南下,江南很快就被清军的马蹄踩得支离破碎。所有的温柔和清朗、细腻和悠然,都在马蹄下颤抖。
冒家虽然从战火和死亡的缝隙中逃了过去,却丧失了几乎全部的家产。于是,董小宛面临着一个缺米少柴的烂摊子。她努力精打细算,才勉强维持着生活。战争只属于那些野心勃勃的人,而战火却经常烧得整个世界通红。战争中的生灵只如蝼蚁尘埃,似乎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他们何辜啊?
日子稍有起色的时候,冒辟疆却病倒了,下痢兼疟疾,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疟疾发作寒热交作,再加上下痢腹痛,冒辟疆几乎没有一刻能得安宁。为照顾他,董小宛把一张破草席摊在床榻边作为自己的卧床,只要丈夫一有响动,马上起身察看,恶寒发颤时,她把丈夫紧紧抱在怀里;发热烦躁时,她又为他揭被擦澡;腹痛则为他揉摩;下痢就为他端盆解带。经过五个多月的折腾,冒辟疆的病情终于好转,而董小宛已是骨瘦如柴,仿佛也曾大病了一场。
很难想象,董小宛心中那份爱到底有多深沉,让她在丈夫生病的时候能够释放出那样大的能量。可是一个妻子应尽的所有责任她都做到了,而她只是一个侍妾。从她遇见他的第一面,她就决定为他付出一切。此时她当真付出了一切,一切的爱,一切的力量。
但是命运给她的磨折还没有结束。日子刚刚安稳不久,冒辟疆又病了两次。一次是胃病下血,水米不进,董小宛在酷暑中熬药煎汤,紧伴枕边伺候了六十个昼夜;第二次是背上生疽,疼痛难忍,不能仰卧,董小宛就夜夜抱着丈夫,让他靠在自己身上安寝,自己则坐着睡了整整一百天。
而这次,董小宛耗尽了最后的力量。这个清荷般的女子,经历了长期的劳累以后终于病倒了,这一病就没有好起来。顺治八年,她安详地离开了人世。那么温柔、婉约的女子,却只有二十七年的时光。而这短暂的时光,竟然那样凄凉,无论在苏州、南京还是如皋,她总是在人生的路上轻轻柔柔地行走着,如云彩般,而生命却给了她太多悲伤和苦痛。可是她走的时候却又那样安详,只因她以柔弱身体做到了最大的坚强。她离去的时候,所有人都为她落泪,所有的记忆都归结为一份美好,二百多年后仍有人拾起,赞叹。
董小宛离去后的日子,冒辟疆悲伤至极,想起在病中时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心痛如刀绞,可是又能如何?斯人已逝,只留给他满满的回忆,一次次走进去,一次次黯然神伤。月如初、琴如初、窗如初、字如初,人却不在了。只好把悲伤攒成诗行,寄给远方的她:
饮离杯,歌离愁,诉离情。是谁谱掠水鸿惊。
秋娘金缕,曲终人散数峰青。悠悠不向谢桥去,梦绕燕京。
春空近,杯空满,琴空妙,月空明。怕兰苑,人去尘生。
寒北冬暮,怅年年雪冷风清。故人天际,问谁来同慰飘零?
董小宛离去了,但是她已把一个鲜活而丰满的形象放置在山水和田园之中。我们都记得,她曾经行走在山水间,衣袂飘飘;她曾经闲坐在田园里,情思绵绵。她永远是那个清丽脱俗的女子,在三百多年前的人间,以静雅的姿态,倚着月光和琴声,看风烟散漫在流年之上,在时光深处种花种草,种满地的精致情怀。
她只是个烟花女子,在青楼的黯淡流年里弹琴陪笑,可她心中却永远留着一块芳草地,那里有云和月,琴和诗。她为烟花女子的形象添上了平静的色调,为那个冰冷坚硬的时代添上了悠然的气息。从青山到绿水,从夕阳到白雪,从云霞到月色,在江南的角落里,柔和着整个人间。她放下一切,从青楼走出,便像是从未走进去一样。那样孤傲的女子,本来就与青楼的纵情声色格格不入,她是清荷一朵,从繁华和泥淖里走出,仍不改傲然本色。
借着月光去寻觅她,却又遍寻不着,只看见几首诗,影影绰绰,横在山水田园之间:
幽草凄凄绿上柔,桂花狼藉闭深楼。银光不足供吟赏,书破芭蕉几叶秋。
修竹青青乱草枯,留连西日影相扶。短墙微露高城色,远处疏烟入画图。
小庭如水月明秋,天远窗虚人自愁。多少深思书不尽,要知都在我心头。
无事无情亦未闲,孤心常寄水云边。今宵有月无人处,高讽南华秋水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