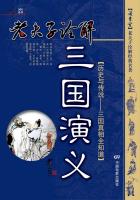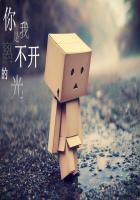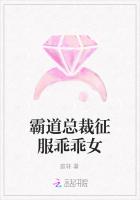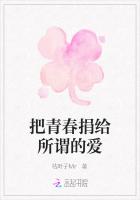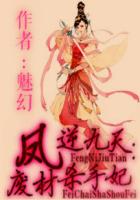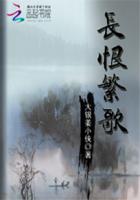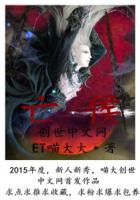西湖边的帅哥
汪精卫第一次与胡适相会是在桂花盛开的9月的西子湖畔。胡适第一眼看到汪精卫就暗自吃惊,都说汪精卫是美男子,他一直以为那是人们的溢美之词,一个男人即便漂亮,又能漂亮到哪里去?待到亲眼目睹,一时眼前放光:世上真有如此漂亮的美男子,健美的身材、深邃的目光、希腊雕塑般的面孔,把胡适看痴了。随后几天,徐志摩、汪精卫、胡适、曹诚英几人结伴去海宁看潮,那里是徐志摩的老家,秋高气爽,潮涨潮落,湖光山色间,胡适与汪精卫一见如故。后来胡适在日记中曾记载道:“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徐志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llery、汪精卫……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
徐志摩本是风流才子,笔下不免诙谐,但胡适对汪精卫的钦慕之情跃然纸上。如果大家都是单纯的文人,也就是文坛的一段佳话而已。但汪、胡都有政治背景,二人又意气相投,很快发展成紧密的政治关系。
胡适和汪精卫分别之后,常常书信来往,谈政治,也谈谈诗文意趣。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原,汪精卫在宦海中忽左忽右,联共反共,排蒋拥蒋,几经折腾,几经沉浮。1932年初,汪精卫正式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掌握相对实权。汪精卫上台后,是很有政治抱负的,鉴于中国多年武人强权,他期望建立一个以“文治”为主的“文人政府”。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很快对此给予积极回应,他说:“我们觉得这个方案是值得认真地考虑与试行的。”汪精卫则心领神会,亲自写信邀请胡适入阁出任教育部长,虽然胡适没有从命,但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几年里,两人鸿雁传书,推心置腹,成了一对铁杆兄弟。
鸿雁传书的“蜜月”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的侵略威胁成为压倒一切的时局焦点。
胡适与汪精卫在通信中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过分贫弱,经不起对日本一战,如果全面开战,中国必败,于是两个人都力主对外妥协。汪精卫显得更加悲观,主张“一边抵抗,一边交涉”。上海沦陷后,国联调解“伪满洲国”外交又失利,双重打击让汪精卫抬不起头来,据说那一阶段他日日借酒浇愁。从前汪精卫十分听妻子陈璧君的话,但那段日子陈璧君的话他充耳不闻。有一则轶闻说,某日汪精卫又喝得酩酊大醉,醉就醉了,可是偏偏汪精卫出洋相,跑到餐馆后堂炒菜间小便,硬是将人家的炒菜间当成了洗手间。炒菜的大师傅听得水声哗哗,还以为打杂的没有关好水龙头,转身想顺手关了。回头一看,却是大官汪精卫在方便,吓得大师傅差点将手中的炒锅扔了,也不敢上前制止。当天下午陈璧君听到这则传闻,当即大怒,冲到汪精卫办公室,一手关门,一手就在汪精卫后脑勺上拍了一下,大骂他太不像话,不但丢了党国的脸,也丢了她陈璧君的脸。汪精卫也知道,自己的女人为何一怒成了母老虎,吓得大气不敢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几口猫尿就让堂堂男人变成了鬼。幸亏只是在餐馆后堂,要是在总统府里出乖露丑,估计不断送政治前途,也会给对手授之以柄,够他喝一壶的。
虽说汪精卫一直与胡适鸿雁传书,被外界称为二人处于“蜜月期”,可胡适的无政府主义并没有解开汪精卫心中的“惑”。由于过度悲观绝望,汪精卫先设下亡国结局,而自觉身负重任的他,异想天开地想学赵氏孤儿的程婴、甲午战争的李鸿章。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中全会,在和与会者合影时,汪精卫被人行刺,连中三枪,幸好没中要害。当时很多人怀疑蒋介石是幕后黑手,因为正好在集体照相前,蒋介石突然临时缺席。蒋介石为避嫌疑,积极督促破案,凶手很快被抓获,原来刺客的目标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不在场,而改刺汪精卫。
汪精卫被刺后,胡适亲自登门慰问,关心备至。听说胡适来看望自己,汪精卫快活得手舞足蹈,陈璧君亲手下厨做菜,将警卫、门卫一大帮都叫来吃饭。席间看着胡适头上冒出的白发,汪精卫忽然心酸地说:“适之,你有白发了,我帮你拔掉。”胡适哈哈一笑,推开汪精卫的手:“白发早就有了,和你一样,国忧民忧,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次相聚两人分外开心。七七事变后,正如汪精卫和胡适预料的那样,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大批人马一窝蜂逃到重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主和妥协派人士组织了一个泛政治团体,称为“低调俱乐部”,希望能通过谈判找到一条停止战争的和平之路。这个俱乐部里除了后来跟汪精卫出走的陈公博、周佛海、曾希圣等人,也有很多各界名人参加,比如何应钦、胡适……
事变后汪精卫曾给胡适写过这样一封信:“适之先生,我十分感谢先生的指示,我的意见,昨天已对先生说过了。我现在尽我的努力,我只有一句话对先生说,今日之事,最好是国民党以全党殉此最后关头,而将未了之事,留之后人……明日下午四时陶希圣先生约同先生来谈,我现在不写下去了。(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四日。)”
在这种危急时刻,发誓不从政的胡适,很快答应出任驻美大使一职,他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当时代表日本舆论界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说:“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1938年初,汪精卫和胡适在重庆分别,这一别就是阴阳永隔。几年后汪精卫死在日本,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要回中国……”得知汪精卫的死讯,并且他的死在中国得不到别人的同情,胡适的心情格外沉重,他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一直到死,胡适仍是很欣赏汪精卫,一如他当年一见汪精卫,就这样说过:“如果我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爱你。”